传记文学理论
2003-8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白生
272
无
《传记文学理论》主要讲述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等,精彩内容。
赵白生,1964年生,江苏省溧水人。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任职有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此外,还担任《跨文化对话》执行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曾获哈佛燕京博士论文奖学金(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赵光潜美文学奖(1997)、北京大学英语系优秀教学奖(1996)等。主要编著包括《肖像》(2000)、《传记文学研究》(1997)、《元首传》(1995)、《走向后现代主义》(合译,1991)等。主编有《独角兽英语阅读文库》(96册、1998)、《布老虎传记文库》(96册,1998)、《传记文学通讯》(4册,1996-2003)等。目前正致力于《世界文学理论》和《生态主义》的研究。
引言“吾丧我”:传记记传第一章 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 第一节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第二节 自传事实:“我与我周旋” 第三节 历史事实:“真相与想像” 第四节 三维事实:“自传是别传”第二章 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 第一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本质 第二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成因 第三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形态第三章 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 第一节 身份的寓言 第二节 影响的谱系 第三节 整体性原则第四章 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 第一节 使命书:制度性自我 第二节 非我篇:否定的隐喻 第三节 心理说:理念幻想曲 第四节 时势论:英雄无心影第五章 传记文学的经典诉求 第一节 新传记的三板斧 第二节 文学史的忏悔录结语参考书目大事年表后记
书摘 在谈唯物论时,瞿秋白对“互辩律”(瞿秋白对辩证法的翻译)十分看重,而对“历史意识”落墨较少。《多余的话》则正好相反,历史意识跳跃到前台,“互辩律”反而屈居暗线。“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历史的偶然”、“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1]等等自始至终,通贯全传。浓郁的历史意识弥漫着《多余的话》的每一个章节,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瞿耿白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却是非历史的。 首先,他切断历史,给非历史性阐释提供了契机。《多余的话》省略了在瞿秋白短暂的一生里掀起涟漪的重大历史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时,瞿秋白只有十三岁,但这场革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国丧”的故事是瞿秋白早年生活的一个里程碑。杨之华和羊牧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这个故事。瞿秋白的妹妹是当事人,她给我们提供的亲历记无疑更为详实可靠: 哥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最年长的。我比他小两岁。他在幼年时期一些不同凡响的言谈举动,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在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云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剪掉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但到了第二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这一年,哥哥也只不过十二岁(下注:应为十四岁),却怀着这样深沉的忧国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现在想来真令人惊讶!实际上,他在这时候,已经树立起革命的志向了。[1]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2]或者十四岁的瞿秋白就“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略去“国丧”这个故事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七会议是主流历史的一条干线,同时又是瞿秋白一生的三段生命线,那么截去“国丧”的故事,一方面割断了历史和个人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切掉了个人发展史的源头。历史纵向发展的来龙去脉切断了,瞿秋白的三段生命线自然衔接不上。所以,他说参加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误会”,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把参加五四运动解释为“历史的误会”,这是瞿秋白非历史性阐释的范例。他这样叙述那段如火如荼的经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3]两个“得”字,一副无奈的神情跃然纸上。那么,瞿秋白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被动和无奈呢?事实上,瞿秋白对这一运动“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1]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忘我的投入:“因为疲劳过度,他回校以后,当天即肺病发作,口吐鲜血,但仍奋不顾身,第二天又积极响应全市专科学校总罢课的号召,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俄专学生进行罢课斗争。”[2]对于他在五四的表现,瞿秋白的好友郑振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回忆资料,其中有一句话正好回应了瞿秋白怎样当上“政治领袖”的:“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3]也许,瞿秋白说的“谁也不愿意干”是事实,但瞿秋白在解释这一事实时,却省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郑振铎所提供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做上“政治领袖”,并不是完全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内在的品质——“出众的辩才”和“领导的天才”——脱颖而出,更不用说他长期的精神准备。在俄文专修馆时,他“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4] 五四运动是一件大事,需要全景式的透视,可是瞿秋白却大事化小,拈出一点事实,从一个角度人手,轻描淡写两笔,就把它打发掉了。他不想内外结合,多方位地解释这段历史。这样非历史处理的结果,瞿秋白模糊了个人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完完全全掩盖了他那颗“浪漫派”(下面加点为原作者原强调点,下同)的心。这颗心“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5]“‘我’无限”[6]是瞿秋白“无涯”诗的基调。可是省略了辛亥革命,淡化了五四运动,没有了永恒的历史,怎么能体现“无限”的“我”? 非社会之我 关键性传记事实的缺席是《多余的话》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瞿秋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当过驻外记者,执教过上海大学,后又身居党内要职,交游可谓遍及海内外。跟他有过交往或交锋的主要人物包括:斯大林、布哈林、鲍罗亭、米夫、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戴季陶、汪精卫、蒋介石、王明、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等。这些人构成了瞿秋白自传里不可或缺的传记事实。可是《多余的话》只偶尔提及一两个人,造成了传记事实的大片空白。 对瞿秋白的传记作家来说,核心的传记事实是鲁迅。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1931年夏初到1933年底,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战斗的生活,一个字也未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1] 瞿秋白只字不提鲁迅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当然不能写他“和鲁迅特别致力于当时文化战线上政治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对标榜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进行了密切的协同作战”。[2]他更不能叙述他在鲁迅家三次难忘的避难生活,特别是“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
引言传记文学,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她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认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1]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他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2]大诗人叶芝(w.B.Yeats))l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3]在中国,《史记》的影响个案不胜枚举。传记文学的重要性早已被文化转型期的先驱人物所认识。梁启超对传记文学可谓一往情深,他的大量传记影响巨大。郭沫若在自传里写道: 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I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4] 胡适是另一位不遗余力地为传记文学鸣锣开道者。他除了自己动手写传记之外还不断劝别人写自传,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传记文学的价值——“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尽管传记文学如此重要,可是传记文学的研究却严重滞后。从国外情况来看,传记文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传记文学的写作。20世纪初,卡尔.范.道伦(Crl Van Doren)指出:“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2]半个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改观。詹姆斯.克理伏(James L Caifford)在《作为艺术的传记》一书的序言里写道:“跟诗歌、小说和戏剧不同,传记从来没有成为精深的批评研究专题。”(3]直到80年代,伊拉‘布鲁斯’奈达尔(Ira Bruce Nadel)仍然面对着同样的事实:“批评……对传记的风格、结构或语言鲜有论述。”[4]不过,对于这三位研究者所描述的现状,有两点需要补充。首先,在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里,对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出过一些专著。有的研究成果,如乔治·密硕(Georg Mih)的自传史研究,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记创作谈纷纷发表。但正如范·道伦、克理伏、奈达尔所说,学术意义上的批评研究几乎是空白。最近二十年,国外传记文学研究异常活跃,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传记文学的研究严重失衡。研究专著基本上一边倒,自传研究空前劲猛,而传记研究却门庭冷落。此外,日记、书信、年谱、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肖像、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依然少人问津。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如此庞大,不全面研究这个谱系,我们的理论就难臻完善。所以,传记文学仍然在召唤它的“亚里士多德”。[1] 我国的传记文学研究目前处于草创阶段。尽管胡适、梁启超和朱东润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开设过传记文学的课程,但遗憾的是,凭他们的影响,却没有能够造就出一批传记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80年代初,唐搜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匆匆逝去,传记文学依旧是学术方面薄弱的一环。”[2]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填补了一项空白,结束了我国到1992年“还没有一部传记文学史”的历史。[3]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在写《传记通论》时,朱文华说,他“每每苦于找不到集中和系统的论述传记理论和写作问题的参考书”。[4] 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里写道:“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当时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5]在总结近十年来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时,俞樟华和邱江宁指出:“在创作繁荣的背后,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冷落,严重滞后。”[6]如果总结一下我国目前的传记文学研究的话,我们看到,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相继出版的专著有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1994)、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1995)、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1999)和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7]但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还需要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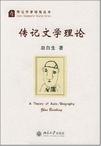
无
很好的一本书,对传记文学的特点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传记文学领域的必读书,基础书。
书很系统,脉络清晰,容易掌握,理论书籍也很生动
朋友说便宜又实用!
书的印刷质量不错,但书所阐述的理论觉得没有深入。
好,完好无损。质量还行
读高三的亲戚的孩子要用,应该不错吧。
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要支持!!
指定教材,不解释
希望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