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1998-08
外国文学出版社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295
219000
黄雨石
无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爱尔兰著名意识流作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运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意识流小说之一。本书情节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反映出来的。书中的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他对祖国、家庭和恋爱等都有源于而又反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作者青年时期的自我写照,困此本书对研究作者及其意识流写作有很大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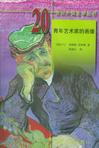
无
这套丛书是国内一流的外国文学丛书,我买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超过一半来自当当网,很高兴,哈哈!但还有几本如《沉船》、《人的境遇》、《鲵鱼之乱》、《老妇还乡》···要么断货,要么当当网没进过,能否设法配货呢?爱好文学的人都不会错过的,呵呵
翻译的家伙很有名的。
这本书值得一买 对于喜欢乔伊斯的人来说。
经典的文本,经典的译文!唯一感觉的就是出版年限有点久了!
书中有一页太脏了
或许是对当代文学艺术的认知偏颇,另我难以静下心来看这本书。再加上抽象派的作风,就更难懂了。
还没看完内容不说纸张太薄了拈起一页来像透明的一样
名著名译,版本好,线装50折,有必要购置。
可能是太深奥,我没看懂
读乔伊斯读得太晚,一如我的冗杂浑沌的人生,早早蜷于幻想,耽于审美。
一面如此渴求着真实,一面却缘木求鱼般久久踯躅在封闭、自溺的体系。 执着于愿望,却忽视了能力;逃避丑恶,却也逃避了责任;厌弃功利,却甚或因此早早迷失自我的方向。
乔伊斯的身上有如此深厚、宽广的关切与承担。 艺术家的命运,因此,
首先,意味着对更广阔意义上人类命运的体认与承当,毫不含糊,从不畏缩,勇于承受 注定的孤独和 接连不断的错误。
"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种艺术形式中 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 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 沉默、流亡和机智。"
曾经充满豪情壮志地取下书架上的《尤利西斯》,但最终还是灰溜溜的还回去了。乔伊斯在我的心中一直是那么生涩、孤独、狂妄,然后还有一些些失落,至少我不敢那么轻易地靠近他。冲着“艺术家”的名目,花了两天的时间看了这本《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看着一个颖悟的男孩子对自己毫不客气的批判,在挣扎中坚定自己的认同,带着从青春期过渡到成人世界的苦涩和洞彻尘世的眼光仰望虚无,不由得让我心生慈悲和怜悯。不过,也许这样对异性的同情和怜悯恰恰是倔强的斯蒂芬所不屑的,哪怕是故作不屑。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吧。
这部小说越往后越显得清冽而张狂,坚毅而充满灵性,思路灵动,仿佛冲洗着亘古存在的岩石的激流,晶莹的水花打湿人性中发霉的苦涩。小说中斯蒂芬对欲望既规避又渴望,对信仰、祖国、家庭也有类似的心理纠缠,但他最终他背向它们选择拥抱自己,因为“我不想伺候我不再信仰的东西”,最终肯定的还是遵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有勇气面对孤独和错误,我想这最终所战胜的只是恐惧吧!
灵魂能够战胜恐惧就已经足够了。有多少时候,生活的各种条律如噩梦一般诅咒我们,连同命运也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命令我们顺从和屈服,哄骗我们假装快乐和幸福。如果不这样就只能像流浪狗一样被抛弃到孤独的脚下。孤独的高贵和慈悲之处在于沉默地接纳一切不被理解和认同的事物,这些事物却互不兼容,好在这仍不失为一个保全灵魂自由的容身之处。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就是如此步入孤独之境的一个人的路线图,不管在什么样的季候下,一直保持着雨后的清新特质,好像一觉醒来,生命又变纯净了。
“具有戏剧形式的美的形象,是在人的想象中加以净化后再次投射出来的一种生命。美学的神秘,和物质的创造的神秘性一样,是逐渐形成的。”
引言出自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身为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现代主义文学巨匠,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以其隐喻之晦涩艰深、结构之复杂奇诡而闻名于世。通过外部心理描摹、叙事视角转换、内部心理独白等捕捉意识流动过程的文学技法,荷马史诗中沉眠已久的奥林匹斯诸神,一夜间从二十世纪都柏林的天空下复活,参与了爱尔兰文学史上一场神秘莫测的心灵狂欢。
正像伏尔泰对但丁的揶揄:“他的声誉将会继续上升,因为人们拒绝阅读他的作品。”对个人美学理念的执着,对小说文本实验的坚守,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精神体验的深度探寻,注定了乔伊斯的名字将被少数评论家奉上神坛,而被绝大多数读者敬而远之。无人理解的写作者是孤独的,亦如无人吟诵的诗篇是无言的。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不但像千年前漫步在希腊城邦的盲诗人那样,预见了命运加诸自身的孤独与无言,更将这种属于创作者个体的痛苦,上升到为审美独立性辩护的高度——“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之内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可被看作是一把通往乔伊斯世界的钥匙,一曲剖析艺术创作者心路历程的无声之诗。
在小说开篇,乔伊斯通过冷静的第三人称视角,将读者带回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都柏林。斯蒂芬•迪达勒斯是个敏感细腻、热爱审美多过政治的少年诗人,出生在一个具有严格天主教传统的刻板家庭。斯蒂芬八岁那年,也就是1890年,是爱尔兰历史上风云动荡的一年。那一年,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查尔斯•帕内尔被曝光同有夫之妇的不伦恋,遭到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倒戈,同时面临着他自己所在的天主教会的谴责。在爱尔兰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天主教信仰与爱尔兰人的国族身份认同,常被混为一谈,而与之对立的则是象征着英国统治的新教。因此,这场发生在议会和教堂中的政治风暴,一夜间席卷了无数个普通爱尔兰家庭的生活。斯蒂芬恐惧地看着他的家庭教师丹特,一位狂热的天主教修女,为了表示对帕内尔玷污自身理想的愤恨,用剪刀撕碎了为帕内尔预备的刷子上的绿绒背——在她心目中,绿色是属于爱尔兰的神圣颜色。习惯了审美判断而非政治判断的斯蒂芬对此非常困惑,“他拿不准怎么才是对的,应该赞成绿色的还是赞成绛紫色的”。激烈的争论不仅发生在每天的报纸上,也发生在迪达勒斯一家的圣诞餐桌上。斯蒂芬那同情帕内尔的父亲,同丹特小姐展开了歇斯底里的争吵,互相斥责对方为“叛徒”“受诅咒的”。家人因为政治观点相左而对立冲突的场景,在斯蒂芬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他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也不知道宇宙在什么地方完结,这使他感到很痛苦,感到自己非常弱小。”
进入青春期后,随着心智的成熟,斯蒂芬日趋感到自己周围政治气氛的紧张压抑、学校生活的枯燥沉闷。这一切“常给他带来极大的苦恼,令他心中时刻充满不安和痛苦的思想。”为了逃避灵魂的不安与痛苦,斯蒂芬利用一切课余闲暇,沉浸在那些充满反叛精神的诗篇中,将拜伦奉为“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对拜伦的迷恋,并不能帮助斯蒂芬摆脱教会学校施加于他的思想钳制。在英文课的课堂上,老师公然指着斯蒂芬,毫不避讳地对其他同学声称,斯蒂芬在自己的作文中宣扬了“异端邪说”;性情独断粗暴的教导主任,在不容斯蒂芬申辩的情形下,将他认作说谎话偷懒的坏学生,当众用尺子狠狠地打了他的手掌心;粗鄙的男同学们,高喊着“拜伦是个异端分子”,将斯蒂芬逼到水沟边的角落里,逼他承认拜伦不是好人……
“他现在已经明白,他的灵魂所热烈追求的是自身的毁灭,那么祷告还会有什么用呢?”在斯蒂芬广阔的内心世界,至暗的深渊与至亮的星空同时显现。对灵魂毁灭的渴望,与对获得救赎的期盼,时刻撕裂着少年的心。好友达文劝告斯蒂芬说,一个人首先考虑的应是他的祖国爱尔兰,然后才是自己的诗人身份。但斯蒂芬早已明白,一名艺术家对“美”的认识,与他声称自己信仰何种宗教无关,与他表面上拥护何种政治观点也无关,而关乎于他对内在“自我”的认知程度。蓬勃丰富的艺术张力,往往起源于人性中本质的自我矛盾——那是人类的悲悯之心与暴戾肉欲之间无尽的交锋。然而,并非每位投身艺术的青年都有足够勇气,为内心感受到的真实人性而创作。一颗敏感的创作者心灵,对自认为善和美的那一部分天性愈是爱恋,对自认为丑与恶的那一部分便愈是恐惧与羞耻,并往往因此从一神论宗教、政治乌托邦中寻求慰藉,通过赞颂幻想中的天堂,来逃避内心存在的地狱,就像斯蒂芬听完神父布道后,感受到的那样:“他的灵魂是躺在自己罪孽的深坑里,但是天使的号角声却把它从那罪孽的黑暗中驱赶到光明中来。他的罪孽在世界末日的风暴中拼命逃跑,像带着无限恐惧的老鼠一样吱吱叫着,在一撮鬓毛下面缩成一团。”
斯蒂芬深知,这种将个人道德偏见置于艺术真实之上的创作方式是怯懦又狂妄的。在斯蒂芬看来,一个艺术家应是美的孕育者、承载者,而非置身事外的审判者。艺术家首先应该承认,是他的国家、他的时代和他的生活塑造了他,因此,他心底一切真诚的声音,都应被视作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得到诚恳的倾听。唯有当艺术家勇于直面自我,不再一味自我审查、自我压抑,他的作品才能拥有超越时代的独立美学价值,而非沦为社会伦理斗争的牺牲品,抑或个人虚荣心的残渣。
乔伊斯认为,最大程度的艺术真实存在于创作者的自我之美中。这个“自我”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艺术家本身,也并非社会伦理、他人意识的投影(super-ego),而是创作者通过文字这种媒介,想象出的一重全新自我,全新生命,即创作人格的美学自我。因为这个“自我”只生活在虚构与创作中,不需要忌惮现实中的群体关系、道德伦理,所以也就没有欺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突破虚荣心束缚,孕育出这一重新生。因此,所谓的“直面自我”指的是在创作中排除他人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把最个人化、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作品中,而不因为忌惮社会规范、世俗偏见而有所保留。
也正因此,当达文试图说服斯蒂芬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表明他的爱国立场时,斯蒂芬没有直接作出反驳,而是对达文讲述了一段晦涩难懂的“灵魂论”:“就在我刚说到的那个时代,灵魂首先诞生了。它的诞生缓慢而阴森,比肉体的诞生更为神秘。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马上就有许多网在他的周围张开,防止他飞掉。你和我谈什么民族、语言、宗教。我准备要冲破那些罗网高飞远扬。”
青年诗人斯蒂芬•迪达勒斯成长历程中体现出的个人与时代之争、艺术与信仰之争,可看作是乔伊斯自身的一面镜子,映射了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经历的漫长心灵挣扎。1903年1月,21岁的乔伊斯对祖国发生的一系列宗教、政治斗争心灰意冷,拒绝了前途大好的神职工作,独自远走巴黎学医。然而,仅三个月后,这位文学天才的巴黎梦便宣告休止——母亲的骤然病逝,使乔伊斯不得不暂时结束他的流亡生涯,重新坐上了返乡的航船。令乔伊斯始料未及的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尔兰天主教会,早已为乔伊斯与他虔信天主教的母亲之间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得知自己的长子坚持不肯皈依后,乔伊斯的母亲抱憾而逝。怀着对幻灭的哀恸,对童年的追忆,以及对双亲与故土那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乔伊斯开始动笔创作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斯蒂芬》。虽然手稿在他生前从未发表,但其中的男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形象,却反复出现在乔伊斯文学生涯的多部重要作品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乔伊斯式美学英雄”。
“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这是斯蒂芬离开家乡追求艺术理想之前,在内心深处对自己发出的呐喊。作为一位“不存在的艺术家”,乔伊斯逃出了历史瞬间的虚无存在,永远生活在他自己建造的文字迷宫中,无人得以直视他那谜一般的眼眸,正如后世永无人知晓,那曾经目睹了人神交战的盲诗人荷马最终归去何方。
刊于《云爆弹》第六期
If you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you should escape from the boundary. But is there anything called "freedom"? Once Stephan said that everything is bounded and restricted, including the free art, i.e. there is no such a concept named 'freedom'. Even if the art is emotional and sensational, it is still constrained under the sphere of the artist's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is a typical modernism novel, so, Joyce forces on the characters' inner thoughts and struggles. It is a novel of 'emotional' religion and politics. Stephan, from the right beginning to the very end, is thinking about whether he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it sensible to follow the god's guidance as other Irish Catholics do?i.e. under the god's lead, people will live happily and walk on the right life path. Or, is it more sensible to listen to its one's heart?--an individual's will is his try faith. Stephan knows that he should treat his heart as his true faith, however, he has to exile himself from his family, friend and homeland. Finally, he follows his emotion and artistic ambitions to achieve the dread of being a poet like his idol Bryan.
In this novel, women are also a noticeable subject (or rather, an object). Women is the emblem of sexual concept and inferior.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Ireland situation--England tried to colonise Ireland and 'seduce' it.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sounds like lyrics. Joyce used many repetitions to reflect our hero's struggle.
书的第一章有如下一段文字:
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哞哞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哞哞奶牛遇见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蛙蛙······
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看着他: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
这样开头的文章总是让人忍不住去爱的,因为在这样的文字里读者足够有能力预见此书必将是作者用比医生手术刀更锋利的语言去解剖人生和灵魂,或是像一位执着的画家一样,小心仔细不无带着狂热的激情在画布上留下一幅肖像。让肖像的脸孔留下历史,让深沉的双眼洞察沧桑。
无疑,乔伊斯是一个爱审视自己的人。他如同那些同样处于变换的时代,对自己民族和国家拥有抱负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先进分子,对自己的灵魂有着洁癖者般的高要求,严标准。不管这样的一个他,是处于童年或者是青年时期。那种综合的自我同一性认同过程能包含的痛苦和矛盾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人,不得不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爱尔兰生活中的肮脏、麻痹和奴性,对自己所属社群的病态状况失望、反感。内心怎能不似火海般翻滚,对生命的信仰和对宗教的怀疑怎能不在一点一滴的观察中产生动摇,瓦解过去的自我,重新认识世界。
总有些人,出生在不属于他的年代,但他却成为为那个年代画上浓厚色彩的画笔。
It is a pity that I was not introduced to Stephen Dedalus earlier in my life. If I were able to converse with this sensitive yet insightful man at a younger age, I may have been able to examine my own spiritual adventure from a dramatica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Nonetheless, I feel fortunate to have finally found the motivations to bravely step forward into the world of James Joyce, and take my first of many journeys in this amazing world.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s a book worth spending a whole life to reflect on.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attempted to flip through the first few pages of Ulysses while lying on my bed after a long day in high school. It was a version translated to Chinese – I thought I would be able to grasp the flows of consciousness if they were written in a language that I was more familiar with. Unfortunately, I never figured out what Joyce was trying to express. Maybe I was just too young to approach his ideas. Maybe consciousness cannot flow in the mind of sleepy boy. Maybe the translator didn’t even quite understand all the messages hidden in Ulysses, so it may not have been my fault after all.
Now I somehow realized that jumping directly into the world of Ulysses was too ambitious a task to accomplish. James Joyce did not even create his landmark work directly – he transcended his styles gradually by working through what is now commonly considered as the alpha version of Ulyss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t seems that Joyce was able to let his modernist writing technique mature along with his alter ego, and therefore Portrait basically serves as a stairway to the temples of Ulysses and Finnegan’s Wake.
Since the narrator avoided weaving connections between each scene, I was given the freedom to slowly reflect on what I’ve read and eventually figure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tle details. Difficult as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was, it actually turned the story alive. I was forced to read Stephen Dedalus’ life in the same way I read my own life. Our life is supposed to be 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e do not have narrators to explain the meanings of our daily events and help us construct connections between everything. Joyce pulled me into the portraits, and I become Stephen Dedalus. I saw things. I heard things. I felt things. I was living a life.
Stephen was destined to be an artist, not a priest. After all, the book is called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Stephen Dedalus’s fate was actually written from the beginning – the book did not begin with a series of religious verse, but instead with a poetic tone sang by Stephen’s father. Long before Stephen interacted with the Catholic religion, he was surrounded by fabulous artistic elements. “Once upon a time and a very good time it was, there was a moocow coming down along the road, and this moocow that was coming down along the road met a nicens little boy named baby tuckoo …” “O, the wild rose blossoms. On the little green place.” What I found amusing was how Stephen even transformed Dante’s words to songs: “Pull out his eyes. Apologize. Apologize. Pull out his eyes.” In a way, art offers Stephen a place to retrieve from the crude life filled with conflicts named religion, family, school, and nationality. It seems that he was always able to naturally accept ar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is identity, without feeling any sort of struggles or constraints. Although Stephen imposed various forms of restraints on himself while examining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his identity, never had he doubt that the importance of art. Deep inside his heart, Stephen realized that he was an artist, so he enjoyed using art to hide himself from the painful reality.
The additional elements in life somehow contradicted with Stephen’s inner identity as artist. He eventually had no choice but to abandon the constraints, and courageously fly away. “When the soul of man is born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nets flung at it to hold I back from flight. You talk to me of nationality, language, religion. I shall try to fly by those nets.”
After interacting with a series of extremely patriotic figures in the works of Yeats, Lady Gregory, and O'Casey, I was intrigued by Stephen's conflicted relationship with his nationality. In a way, the states of his family member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erception towards Irish nationality. At his first Christmas dinner, young Stephen witnessed an argument between his father and uncle. Dante’s tumultuous departure from the table somehow resembled an action that Stephen later imitated. Dante broke away from others to declare his ideological independence. Similarly, Stephen broke away from others to declare his spiritual independence. At a very young age, Stephen was taught not to accept anything as infallible law. Political stance can be disposed for the sake of art. Religious commitment can be disposed for the sake of art. Family and nation can also be disposed for the sake of ar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artist, at first a cry or a cadence or a mood and then a fluid, and lambent narrative, finally refines itself out of existence, impersonalizes itself, so to speak. The esthetic image in the dramatic form is life purified in and reprojected from the human imagination. The mystery of esthetic like that of material creation is accomplished. The artist, like the God of the creation, remains within, or behind or beyond or above his handiwork, invisible, refined out of existence, indifferent, paring his fingernails.” I’m not sure if Stephen eventually considered himself as a figure equivalent to God, but James Joyce is definitely a God-like artist who is brave enough to withdraw himself from the complexity of life and purify his pursuit of art. Maybe God is also an artist, and Joyce is just worshipping him in a more appropriate way. After spending decades exploring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rt, Joyce finally presents his answer in the form of a young man called Stephen Dedalus.
Without doubt, Stephen is a very ordinary character. He is not Sherlock Holmes, Jay Gatsby, nor even Humbert Humbert.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alter ego of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tephen is as ordinary as a person can be. Even though Dedalus showed potentials of developing into a great artist, Joyce decided to end the story at a point where the readers can still completely relate themselves to this young man. Just like every one of us, Stephen is still confused even though he has already found deeper meanings in his life.
“Welcome, O life! I go to encounter for the millionth time the reality of experience and to forge in the smithy of my soul the uncreated conscience of my race.... Old father, old artificer, stand me now and ever in good stead.” Although the character has clearly matured through painful processes of self-reflection, he still was not able to form a conclusive system of philosophy on aesthetics, religion, love, and identity. It seems that James Joyce decided to leave Stephen undeveloped and let the readers imagine where this young man ends up in the future. Maybe he evolved into James Joyce. Maybe he did not. Maybe he became me. Maybe he became you. Because of all the different options offered, A Portrait is a masterpiece that contains much more contents than what we think it does.
“我将去面对无数的现实经历,将在我那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的民族所不曾有的良心。”
读到这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结束了。当我怀着难以平复的激动心情合上书页,这本薄薄的小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起层层的涟漪,我的视线不禁长久的停留在封面上方小说题目里的这几个字上,更准确地说是那一串压在中文翻译下方的英文单词上——《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它仿佛闪电一样打穿了无尽的时空,一只鸟儿翻动起巨大的金色羽翼从迷宫里腾空而起,我看到了詹姆斯•乔伊斯那撒旦一般的面庞上浮现出的微笑,静默在我的脑海里轰鸣。
A Portrait——
“画像”两个字暗示了小说的写法。阅读小说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走在一幅幅画像面前,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色调、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笔触,这样的感觉让我想起俄国著名的民族乐派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为纪念亡友而创作的印象风格作品《图画展览会》。
如果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仿佛一段又一段的夜曲,或者幻想曲,或者音乐小品:唯美,浪漫,精致,好像美轮美奂的宫殿,美的让人遗忘在记忆中,让人来不及动用理性去思索这背后的建筑结构。仿佛浸泡在醇厚的葡萄酒中一般,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呼吸。
那么,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则好像交响乐,开始就是结尾,运用简单的动机发展出主题,在旋律的进行当中那些原始的动机时常像蛙跳一样闪现,折射着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当我们打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读上几页时,就会被这种写作手法而深深的吸引。小说中处处穿插着诗歌一般的意象,交响乐一般的动机。比如第一章中的牛、老鼠、家长的教导、记忆的重现、板球、学校建筑等等,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心理的变化而不断重复着出现,仿佛漫不经心的排列组合。同时语言的风格也随之改变就像音乐中的转调一样,给人以线索去探究小说家心目中的情感变化和艺术构思。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去观察这部作品的建构模式时,我们会不禁惊讶,詹姆斯•乔伊斯就用这样一些日常的不能再日常、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材料、意象或者动机而发展出了这样意蕴深刻的长篇小说,反映出了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他堪称小说家中的贝多芬。
说起这幅宏大的历史图景,一般的读者(尤其对于本文作者这样被打上“不解风情”标签的与自然科学的形上学打交道的人),如果仅仅凭借没有注释的小说文本,恐怕很难理解小说中或者顺便一提的人名地名,或者精心描写的心理活动,因为乔伊斯写的非常含蓄。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乔伊斯的创作生平,体会一下爱尔兰特殊的历史,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和艺术构思就会像两个高速相向运动的粒子一样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发生对撞,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乔伊斯写的非常入骨。甚至如果我们有在爱尔兰生活的经历的话,那种特殊的文化背景,那种浸透着爱尔兰长达八个世纪被不落的太阳灼烧的殖民历史的自然地理和城市建筑,会在我们理解小说的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张力。
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和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的反映,这似乎是两个极端,一个通向无穷小,一个通向无穷大。可是因为乔伊斯深刻的洞察力,他完美的将这两个极端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从之前的作家所不曾涉足的道路走向了罗马。又好像带着所有的读者绕着地球一圈一圈的走着,让我们感受到那些想象中头脚倒置的对立的极点,原来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The Artist——
定冠词the的使用意味深长。Stephen Daedalus,正因为他出现在小说里,所以他不是任何人;但也正因为是在小说里,他又是所有人。当然,前提是,作者是乔伊斯一样的小说大师。
漫步在小说里,浏览着一幅又一幅的画像,我时常感到眼前摆着一面镜子,这边是被遗忘了的现实的我,那边是越来越清晰的被照亮的我的回忆。这样的感觉好像一朵刚刚绽开的水仙花,又好像一只亲吻着湖面中的倒影的天鹅。
这不是我吗?!
我也在学校里踢过球,打过架,被推进水沟,被老师冤枉,也曾关于世界关于宇宙产生过幼稚的思考(真的幼稚?),也曾在一旁默默的眼巴巴的看着家长们在饭桌上争论政治讨论我的前途。Stephen Daedalus听到过对于政治与宗教的争吵,我听到的是共产党与马克思罢了;他听到过对于天主教与新教的异见,我听到的是左派与右派罢了。
我敢说,小说中除了主人公在妓院的性经历的描写之外(偷笑,这一点毫不讳言),其余的一切我都感同身受。甚至Stephen Daedalus在忏悔室门口对着自己将信将疑的上帝发出对于自己的性罪孽的忏悔段落,我也能身临其境。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自己,童年甚至是现在不也偶尔会下意识的对着上帝表白一下以“自我与命运”为主题的感慨吗?然而上帝在信仰者的心目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个人的这种下意识行为很可能发源于对好莱坞大片中的情节的模仿。同样的将信将疑,或者无所谓信与不信。
定冠词the在这里的使用既传达出一种普遍性,又具有主人公的独特性。在欣赏的过程中即使因为一万个相似而忽略了一个不同,也是非常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带着一阵又一阵的惊异去阅读这部仿佛自己的自传体小说的时候,在心中仍然要努力排除这种很可能扭曲而造成自恋的想法,要时刻提醒自己相同的表象之下所涌动着的不同的血脉,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原因——乔伊斯的写作有着爱尔兰特殊的历史背景。
这种定冠词所传达出来的独一无二,又与小说结尾处主人公的流亡宣言里呐喊出的“将在我那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的民族所不曾有的良心”遥相呼应。Stephen Daedalus,他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如何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艺术家?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乔伊斯花了大量的笔墨通过Stephen Daedalus与林奇的对话表现了主人公的美学观。令人信服,拍案叫绝,在历史进程中犹如迷宫一样的美学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居然深刻而条理的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一段在小说中显得格外耀眼,又似乎有些毫无征兆。可是当我们重新捡起刚才的问题,会发现这一段的出现是不可或缺的。主人公在整部小说里一直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沉思者的形象出现,也正是在他讲述自己的美学思考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思考着自我、认识了自我,更加清楚的看到了未来的方向,而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了。虽然在小说当中他还没有创作出什么举世公认的作品,可是当我们看到他的美学观之后,我们坚信这只是小说叙述之外的必然。
当我跳出文本,试着用同样的手法想象着去为自己写一部《一个青年科学家的画像》时,我发现,对于科学,自己尚不能拿出一套如此完整而深刻的体系。
As a Young Man!!!
Young这个词点明了小说主人公的年龄段,正在青年和曾经青年的人们通过乔伊斯的笔触都能对这个年龄段中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活动产生共鸣,这也是这部小说的普适性的一个主要方面。
然而这个介宾短语更加深刻的内涵是中文所无法传递出来的,从中文翻译回英文,我们可以这样更加简洁的表达:A Portrait of the Young Artist。但是回想整部小说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这样简洁的翻译欠缺了很多的分量。原因就在于Man这个沉甸甸的词在西方文明史上有着深沉的文化意蕴,它的第一次被叫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在宗教的阴影下人们高喊出“以人(Man)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浪潮里。上帝被放在一边,人文主义者们的追求就是要活出一种很Man的感觉。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一次对于宗教传统的打击,后来的尼采是第二个喊出“上帝死了”的人(需要点明,内涵有所不同)。
在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第一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特征就是对现实的知性的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文艺复兴通过遥远的历史的走廊,在今天仍然发出回响的另一点就是艺术家的概念,从那时开始,艺术家的形象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奔放不羁、天马行空、生活浪荡、衣冠不整、鹤立鸡群、傲视天下,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当我们想到这一层历史背景时,再去看Stephen Daedalus这个角色,在第三章重点描写宗教的部分,连篇累牍的文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引力将读者囚禁在令人瘫痪的精神迷宫里,不知所措,仿佛是被束缚在两面相对摆放的镜子之间,在现实与意识无穷无尽的相互映照里看着无数个越来越模糊的自己。他最后对于宗教与现实的反叛是多么的震撼人心,与这种内容的震撼相对应的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这时也从第三人称突然转变成第一人称。在爱尔兰那块受着殖民和宗教双重迫害的土地上,人们已经变成了乔伊斯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牛——驯服,一盘散沙,不能抱起团来将犄角一起朝外对准来犯的狮子。
再去想乔伊斯的流亡之旅,一生穷困潦倒但却酷爱奢侈,在创作的道路上坎坷多难但却一刻也不曾妥协。他为什么要流亡意大利呢?也许,主要是因为那里更便于生活,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但是意大利这块土地上,既有着文艺复兴的历史传统,在残酷的宗教迫害里仍然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为后世的所有知识分子提供着精神的源泉;但同时又有着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传统,在爱尔兰长达八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中始终作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摧残和麻痹着爱尔兰人的精神意志。也许这个巧合也是成立的,詹姆斯•乔伊斯是像荆轲一样勇敢的人,他完成了一次孤独的流亡,一场燃烧的远征。
再去品味乔伊斯的语言风格,不妨和普鲁斯特做一个对比。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绝不可能出现一个“屁”字(未读完《追忆似水年华》而做的猜测),然而在乔伊斯的小说里,一切都很现实,毫不遮掩,我们已经习惯了他这种将崇高与卑鄙、美丽与丑陋并置时的冷幽默与冲击力。曾经两位大师历史性的见面时,他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这就好像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会面,他们对彼此能讲些什么呢?两位从各自的人生旅程出发在小说的世界里探索人类心灵哲学的大师,在这一刻还有什么比静默更好的表达惺惺相惜的方式呢?
为什么会惺惺相惜?詹姆斯•乔伊斯在我们脑海里的那张画像不停地慢慢旋转着,背面就是翻动起巨大的金色羽翼从迷宫里腾空而起的Daedalus。然而我们再去想一想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位短命而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哮喘症囚禁在室内的人,却在他那不朽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找到了永恒的存在,他不也是一位Daedalus似的人物吗?
对于Stephen Daedalus,对于詹姆斯•乔伊斯,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句台词:“Some birds are never meant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世上总有这么一种人,宁可粉身碎骨、流落天涯,也绝不相信“存在即合理”所带来的奴役与囚禁。对于这些人,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让他们从心底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在打破丑陋的现实、追求更好的未来的道路上,你——永不独行。
乔伊斯,爱尔兰的鲁迅,小说界的尼采。他好像一只风筝,张开他天才的羽翼飞翔在自由的蓝天白云之间,折射着金色的阳光,然而线的那一端始终紧紧的绑在自己民族的心结上,正是这颗不屈的心脏的跳动,为远走高飞的乔伊斯送去继续前进的动力与信心。当一个人一遍遍的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是因为超越时代、超越人群时,继续坚持自我需要多么强大的勇气!他的作品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小说无国界,但是小说家有国籍,爱尔兰这个国家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肃然起敬。
乔伊斯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背井离乡过着流亡四方的生活但是却对人讲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爱尔兰。正是因为他流亡了,他的作品才得以创作与发表;正是因为他从未离开,他才没有再沦落到新的命运的罗网与生活的迷宫之中。
历史已成绝唱,时光流逝,沉淀下这些不朽的文字与思想默默地散发着夺目的光辉,启迪着今天的我们做一个知性、勇敢的人。在倡导着民主与多元化的今天,现实的困境却从来没有被打破,后殖民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在孕育着更大的罪恶,眼花缭乱的谎言之下仍然充斥着物质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泥淖与渊薮,让世人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自己。当我们想要像小说中的Stephen Daedalus,历史中的詹姆斯•乔伊斯,一样去流亡,去寻找,去打造,去战斗,只是今天除了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在“灵魂的作坊”里,我们还能去哪里呢?
“勇敢的鸟儿成群结队,飞向远方,飞向遥远和最遥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最终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不再能够继续飞翔,而栖身于某根桅杆或某个陡峭的崖壁上——他们现在甚至感谢如此凄凉的落脚的地方!
然而,谁能够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已经飞到了天的尽头,已经飞过了鸟儿的极限?我们的所有伟大的导师和祖先最终都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精疲力竭,姿势可能既无威严也不优雅:这也将是你我之辈的下场!
但是你或者我又算得了什么!其他的鸟儿将展翅飞向更远的地方!我们的这种信念和希望随着它们的翅膀上下翻飞,飞上了云端,飞向了远方;它超越了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无力之上,从云端上举目仰望,看见了一群又一群比我们更有力量的鸟儿仍然在不懈地向着我们曾经飞向的地方飞翔,向着大海,向着无边无际的大海飞翔!——那么,我们的目的何在?
我们是否想要飞过海洋?这种不可抗拒的向往,这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我们快乐的向往,究竟要把我们带向何方?为什么我们飞行恰恰是这个方向,这个迄今为止所有人类的太阳陨落下去的方向?人们有一天也许会这样说我们:我们取道西行,希望到达某个印度——但却命中注定要葬身茫茫的大海上?或者这样说我的兄弟?或者——?”(引自尼采 《曙光•精神的飞行者》 )
"JOYCE AND HIS TIME":
http://www.clas.ufl.edu/users/kershner/bioa.html
这个网页足以解答小说中各种与爱尔兰命运、爱尔兰的青年的命运纠缠不休的细节,以及扰攘不宁的大学时代,陪他左右的那些朋友,都曾是谁,后来因何而死。
这是值得读一辈子的小说,每次读后都觉得已经读懂了,可下一次看,却发现,其实依然不太懂。
本书是《尤利西斯》前传,但形式没那么叛逆,所以有点闷,与中国读者在情感上,多少有些隔阂,我们不太能和主人公同悲同喜。
因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确定性”的,我们先天就承认它的合理性,当个体遭遇挫折时,东方人会更多检讨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奸商必备的计算能力: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么就改变自己。
但,这和欧洲文化格格不入,现代化曾让一代欧洲人的精神走向幻灭,经济迅猛提高,却没能造福人类,国与国之间毫不掩饰着彼此的敌意,战争与屠杀站在走廊里,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在恐慌的压迫之外,复有人世间赤裸裸的竞争,我们因此而冷漠、疏离且虚伪,那么,我和他真的是共同体?我们真的有共同利益?当战争来临时,我为什么要为抢走我工作的那个人而战斗呢?
这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再也无法圆谎的世界,詹姆斯•乔伊斯选择了彻底的堕落,这不是玩世,而是放弃,因为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这世界的荒谬,只好用自己的态度,来寻找同伴。
越个性,越孤独,越受伤。主人公脱离于生命之外,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荒唐,这个视角的出现,堪称是詹姆斯•乔伊斯对现代文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他笔下,我和自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在批判着自己,自己在背叛着我。如何才能解脱呢?他不知道,但他固执地认为,凡是试图将我和自己合而为一的人,都是傻瓜。
沿着这个进路,现代文学越走越宽,其实《麦田的守望者》中的惆怅,与本书完全相同,只是前者更时尚一点,詹姆斯•乔伊斯依然坚持着老英国文学的叙事传统,缓慢,优雅,古板,以及灵光一闪的幽默。
这世界是我的枷锁,但我不能挣脱,因为一旦挣脱,我将无法再依赖于它。这种逻辑的困境,构成了这本里程碑式小说的紧张感,然而,这种紧张感是不太容易被察觉的,如果只看故事的话,它似乎平淡了一些,而这份平淡,也许就是作者正在诅咒的世界的本来面貌。
所谓经典,是永远不会老的,当我们老去,它依然年轻。
乔伊斯不愧是意识流的大师。在这本20余万字的书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主人公斯蒂芬的内心独白。书的最后,斯蒂芬的思绪像流水一般漫无目的的发散。他想到夜幕降临,想到”黑暗从天而降“,而后又发现自己其实记错了台词,应是”光明从天而降“。
从天真的幼年时代不情愿的进入青春期,对斯蒂芬来说正如”黑暗从天而降“。
在这被黑暗笼罩的青春岁月中,斯蒂芬感受到了一个与幼年”奶牛哞哞、宝贝咕咕“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感受到了世界的虚伪肮脏,经历了萌动的性,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深深的负罪感;他不断的挣扎着,与家庭、与宗教、与这个本不属于英国的爱尔兰。这时的斯蒂芬,面对身处的青年时期感到的只是困惑、恐惧,他用力的思考却无法得到解脱。
跟着时间的步伐,斯蒂芬终于穿过了这幽暗的时光:
”我不会为我不再崇信的东西去卖力,不管它自诩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将会竭力以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或艺术形式来尽可能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只会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就是沉默、背井离乡和机智应对。“
斯蒂芬最终抛开了那些强加于他身上的束缚,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路,即使以孤独为代价,他也并不在乎。
文章最后由第三人称转变为斯蒂芬第一人称的日记。在那些支离破碎的文字与思绪之中,我依然能看见斯蒂芬的挣扎与痛苦。但那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的挣扎了。因为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他将坚定的走下去。
”欢迎,啊,生活!我将去面对无数的现实经历,将在我那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的民族所不曾有的良心“
”老父亲,老发明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永远给予我帮助吧。“
我相信,在这一刻,对斯蒂芬来说,光明从天而降。
视剧中表现内心挣扎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脑袋左边一个圈冒出一位穿白衣服长翅膀很清新的鸟人,像天使,代表好的自己。脑袋右边一个圈冒出一位穿黑风衣戴墨镜很酷的帅哥,像魔鬼,代表坏的自己。天使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的话,你就堕落了,大家会嘲笑你看不起你的,你对得起你家人亲戚朋友吗?”魔鬼说:“服从心灵的召唤,JUST DO IT!这才是真正的你,你不这样做,你就对不起你自己,你要给自己自由,让世俗的眼光见鬼去吧!”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选择做天使,让自己痛苦让亲人朋友高兴,看到大家高兴后,自己也觉得开心,最后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曲折点的是先选择魔鬼,在受到惩罚后浪子回头,凤凰涅磐,魔鬼变天使,大家还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种非A即B的一元论表现手法属于老套路,不新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就不一样了,斯蒂芬(主人公)选择了C。小说的歌词大意是:斯蒂芬从小生活在很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母亲笃信天主教,希望儿子和她有同样的信仰。他虽然早就对宗教心存怀疑,但是还是装着信着。步入青春期后,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开始背离教义,哥们很痛苦啊,就去寻找知心哥哥姐姐妈妈叔叔的寻找慰藉,希望他们给自己心灵鸡汤一把,让自己从此走上“正道”。可事与愿违,他根本按奈自己的欲望和艺术家的本性,于是就“堕落”了——开始嫖娼。但童年时期宗教对他的影响,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作用,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都很肮脏,每次“作孽”完,都会陷入无尽的悔恨和失望之中。即使这样还是阻挡不住他下次去爬妓女的床。从小说中看到他并没有把责任推到妓女身上,他就是过不了自己这关,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只是在不断地忏悔。后来遇到了一位神父,像成功学大师一样,神神叨叨地给他们讲了地狱如何如何可怕,地狱之火这般那般的厉害,每个下地狱的都要经书这火的煎熬。唯有信仰上帝爱上帝,真心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死后才不会承受地狱之火的惩罚,才能进入天堂。斯蒂芬听过这些之后,非常害怕下地狱受罚,他也迫切需要抓住一根稻草来把自己从罪恶的泥潭中拉出来,所以他开始真心忏悔,向神父讲出自己所有的“罪孽”,开始变成一位虔诚的教徒,每天都在认真祈祷,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他想相信自己的信仰就在这里。可想归想,真正的相信确是另一回事,他比一般的人都要了解宗教。但是不管如何努力,他就是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宗教。虽然他在那里获得了短暂的快乐,那种不孤独的快乐。
最后斯蒂芬背叛了宗教,但没有继续”作孽”,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一条属于自己和适合自己的路,他“……要去发掘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和艺
术形式,这样我的心灵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
要不说人家乔伊斯牛逼呢,之前我还没看过一本小说对主人公这么狠的,他像是发现了一座用不完的富矿,在不遗余力地挖掘斯蒂芬的内心,从里面开采出无数宝藏,他用了整整21万字的篇幅来表现斯蒂芬对信仰的追寻,而《译后记》提到乔伊斯原本是计划要写一千多页的。
我们没有信仰,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其实你只要把这个信仰换成你的某个人生重要抉择就行了。如果你跟我一样记不住外国名字,觉得看起来会比较费劲,也不要紧,只要您记一个就行,就是斯蒂芬,看和他相关的心理刻画,景物描写和对话。如果你连书都不想看,又想让人觉得你比较有文化看过这本意识流小说,你把上面的歌词大意记住。如果你连歌词大意都不愿意记,那就记住这个抽象出来提纲:斯蒂芬怀疑宗教——寻找他人帮助——“堕落作孽”——回归宗教——踏上朱军的艺术人生之路。如果你连这个都懒得知道,那当别人谈起这部小说的时候,你就说“斯蒂芬很纠结,不过还好,最后他找到自己想要的了”,然后直接闭嘴,剩下的让对方猜去吧。即使这样您也没说错,这部小说就说了一个事,斯蒂芬的纠结。
一些其他的感想
1.很惊叹斯蒂芬的早慧,一个16岁的少年,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思考的不是怎么泡妞,怎么玩,怎么考试考个好成绩,怎么穿衣打扮,而是怎么直面自己的欲望,寻找心灵的归宿。
2.丢失信仰比没有信仰更痛苦。
3.一个人向内到底能走多远?以字数衡量,乔伊斯给了21万。应该可以更多,甚至是无限多。
4.孤独这玩意是艺术家自找的,这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时候用这个来顾影自怜,就太矫情了。
5.我们有没有小说只描写80后的青春期欲望和对欲望的挣扎的?
6.这小说不适合拍电影,大部分是心理和对话,而且是讨论宗教、信仰、艺术和美的,要拍出来,应该属于科教片。
when the soul of a man is born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nets fung at it to hold it back from flight.You talk to me of nationality,language,religion,I shall try to fly by those nets. ----by《In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原文Stephen went on:
——Pity is the feeling which arrests the mind in the presence of whatsoever is grave and constant in human sufferings and unites it with the human sufferer. Terror is the feeling which arrests the mind in the presence of whatsoever is grave and constant in human sufferings and unites it with the secret cause.
黄雨石译文:
——怜悯是使人的头脑停留于任何一种人所遭受的严肃而经常的痛苦之中,并使它和受苦的人相联系的一种感情。恐惧是使人的头脑停留于任何一种人所遭受的严肃而经常的痛苦之中,而使它和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相联的感情。
徐晓雯译文:
——在人类阴郁而连续的苦难面前,占据了人类心灵并与受苦难的那个人连接起来的感情,叫做怜悯。在人类阴郁而连续的苦难面前,占据了人类的心灵并把这苦难与那神秘的原因连接起来的情感,叫做恐惧。
李靖民译文:
——怜悯是一种控制人的精神的情感,当人类遭受的任何一种长期深重的苦难与具体的受难人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这种情感。恐惧也是一种控制人的精神的情感,当人类遭受的任何一种长期深重的苦难与某种神秘的诱因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这种情感。
grave的翻译不同,原文中and unites it with中的it,几位翻译家也没能统一。
谢谢一楼的同学,我觉得他的不错。
1904年1月,22岁的爱尔兰青年詹姆斯·乔伊斯应都柏林一个新杂志《达纳》之约,写了一篇叙事体散文题为《艺术家的画像》。但是这篇短文最终并未得以发表,编辑以内容难以理解为由,拒绝予以刊登。在这篇文章里,乔伊斯展现出强大的企图心,运用他的"心灵顿悟速写",将往事像流水般一幕幕展现出来,流畅得足以随着思绪起伏跌宕。10年后的1914年,乔伊斯几经改写,彻底摒弃了原作品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描述,最终定稿名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随后在众多朋友的不懈努力下,付梓出版,这部作品首印仅750册。
100年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界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名列第三。这足以证明这位意识流小说的开山大师在20世纪小说写作领域中占有的至尊地位,也悄悄暗示文学新千年的开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为乔伊斯的早年之作,没有捉弄人的文字游戏,没有故作高深的哲学探讨,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也没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讥嘲,语言纯净而饱含诗意和激情。他忠实记录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孩子的残酷青春物语。这部书既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们可以窥到乔伊斯的影子,它又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场景大多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又不是完全纯粹的自传,无论是人物、时间还是情节的处理都与现实生活存在着距离。
这本书,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所以他改了又改,尽可能地在作品中复活以前的自己。乔伊斯写出了所有对生命敏感的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幼年的懵懂和恐惧,少年的狂躁和不安,青年的困惑和清醒。这是一个灵魂企图摆脱束缚的奋斗过程。那么,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防波堤旁的大宅,翱翔的飞鸟,犹太人贫民区,天使般的生活,酒吧,咖啡店,妓院,教堂,大学,瘦弱的学童,攻读文学艺术的大学生……种种不断累加,乔伊斯用这些素材构筑了语言的海市蜃楼,想象、记叙、描摹、议论,如梦似幻云烟一般,时而清晰逼真,犹如尽在咫尺,时而朦朦胧胧,宛如隔着一层薄纱。
就仿佛一场关于青春的梦魇。
这场梦的主人公,就是所有的读者,你。本书最伟大之处,在于那永不消弭的青春活力,毫无遮掩地展现出一个从幼年到青年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慢慢成长,一步步走向成熟。乔伊斯按照精神世界的规律或者说回忆的经纬来编织小说,赋予时间以具体的形式,描绘了生命的机理和每一处皱折。他借助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不时交叉地重现已逝去的岁月,从中抒发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派遣的惆怅。一切都在时光的流失中瓦解变质,乔伊斯用语辞把这个时刻固定下来,失去的青春就是这样找回的。次第更迭的人物,让我们挽紧时间的缰绳。
伍尔芙说,乔伊斯先生不顾一切专注于表现内心深处的火花掠过大脑时隐约间传递出无数信息。他仿佛炫技般地展现着自己出神入化的文学天赋,无论是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第三人称的叙述与第一人称的视角交替,还是自由间接引语,内心独白,破折号代替引号等等特殊表达,都不言而喻作者的伟大。乔伊斯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生活在别处是他命运的常态。从本书问世开始,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要驾驭自己命运的青年艺术家,他已经做好了彻底背叛的准备。甚至他已经不屑于鹦鹉学舌,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来书写命运。那么,这部作品就是乔伊斯对自己青春的一场薄奠。我们放佛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有点单薄,有点脆弱,又执着地往前走。而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
《中华读书报》20091118
说实话,这本书给我的触动并不是很大。但是在阅读的时候,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股“意识之流”,一种形式之美。
书中主人公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过程倒给我不少启发:
艺术家的眼光:家庭,宗教(在中国,则为官方说教),性爱都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平庸。惟有获得一种获取美感的能力“把普通的生活经历变成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光辉的杰作”(P256)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
艺术家的故乡:惟有逃离故乡才能真正返回故乡。从奥德赛返乡开始,回归永远是文学的中心。
艺术家的冒险:必须长出翅膀,必须往更高的天空飞去,但是飞得太高,翅膀很有可能会被灼热的光芒融化掉,代价便是坠地而亡。
艺术家的武器:“我只会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就是沉默,背井离乡和机智应对。”(P298)
艺术家的父亲:必须杀死自己的生父,找到自己的养父。(P1,P298)
艺术家的狂妄:谦虚永远是艺术家的第二美德。
Cranly pointed his long forefinger at him.
“Look at him!” he said with scorn to the others. “Look at Ireland's hope!”
They laughed at his words and gesture. Temple turned on him bravely, saying:
“Cranly, you're always sneering at me. I can see that. But I am as good as you any day.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about you now as compared with myself?”
“My dear man,” said Cranly urbanely, “you are incapable, do you know,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thinking.”
黄雨石译:克兰利一边用他那长长的食指点着他,一边对着大伙刻薄地说道:
“看他,看这爱尔兰的希望!”
他的话和他的动作引得他们大笑。坦普尔勇敢地对他攻击,说道:
“克兰利,你总是嘲笑我,这一点我可以看出来。不过,我怎么说也和你一样好。你知道我这会儿在心里拿你和我相比,我怎样看你吗?”
“亲爱的伙计。”克兰利有礼貌地说道。“你没有能力,知道吗,绝对没有能力思考问题。”
徐晓雯译:克兰利用长长的食指指着他。
“瞧瞧他!”他语带嘲讽地对其他人说。“瞧瞧这爱尔兰的希望。”
他们对着他的话语和手势哄堂大笑。坦普尔勇敢地朝他转过身,说:
“克兰利,你总是在嘲弄我。我看得出来。可是在任何时候我都比得上你。把你跟我自己做个比较,我眼下对你是怎么个看法,你知道吗?”
“我亲爱的人儿,” 克兰利礼貌周全地说,“你知道吗,你没有能力,根本没有能力产生什么想法。”
李靖民译:
克兰利一边用他那长长的食指点着他,一边对着大伙刻薄地说道:
“你们看看这小子,看看这爱尔兰的希望!”
他的话和他的动作引得大伙一阵哄笑。坦普尔挺起了腰杆儿冲他说道:
“克兰利,你小子总想拿我开涮,别以为我不知道。不过,我怎么说也不比你差。你知道我这会儿在心里怎么拿你和我相比吗?”
“喔,我的好小子。”克兰利用戏弄人的口气说道。“你是个笨蛋呀,知道吗,一个没有脑子的大笨蛋嘛。”
乔伊斯对语言很敏感,所以他的文字很妙,《尤利西斯》里有部分章节写的也很妙,但自从三年前我硬着头皮读完它以后,我就再没有摸过它了,我一个哥们说《尤利西斯》写的很狂放,简直是语言的狂欢。我承认他说的没错,但这不代表它是个无懈可击的精品。《尤利西斯》太花哨了,所以我不喜欢。相反,《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为乔伊斯的早年之作,没有捉弄人的文字游戏,没有故作高深的哲学探讨,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也没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讥嘲。《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纯以文字取胜,语言纯净而饱含诗意和激情。这就是年轻的乔伊斯啊,而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太老了,太老了。老得连作品中也充满了世故、圆滑和老年人常有的自大。也许等我老了,我会喜欢。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我在一年前才看到,一看之下就欲罢不能,连读了两遍还意犹未尽,又在卓越网买了青岛出版社的英文版。为了看这本书,活活的把我的电子辞典给摁坏了,不好意思,我的英语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我看书不喜欢写长篇大论的评论文章,我总是尽量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本书,其实我自己也明白,如果一句话可以说清楚,作者就不会呕心沥血的弄一大堆出来了。但文学虚构的魅力就在于此,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无趣的东西丰富化,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这在文艺学里称为蕴藉。咱不说那高深的玩意,单单为了稿费,有时候作家也会努力的添加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但是乔伊斯不是这样,作为草稿的《斯蒂芬英雄》可比《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厚多了。乔伊斯创作心态很好,不光是为了稿费,其实他要是靠稿费活着,早就饿死了。特别是这本书,他写的就是他自己,所以他改了又改,尽可能地在作品中复活以前的自己。于是乎这就给我的概括提供了方便,乔伊斯写出了所有对生命敏感的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幼年的懵懂和恐惧,少年的狂躁和不安,青年的困惑和清醒。这是一个灵魂企图摆脱束缚的奋斗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但这一代价有时候还需要别人替他付的,这就有点不地道了。也就是说他要伤害一些人,甚至最亲的人。斯蒂芬伤害了母亲和自己的好哥们。乔伊斯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他的弟弟。个中细节,不提也罢!
Statement
What I present is inevitably fallible since it is authentically original.
The Ecstasy of an Exile--an essay on "A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
... "the Epiphany: a sudden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whether in the vulgarity of speech or of gesture or in a memorable phase of the mind itself."
---Stephen Daedalus
Will I be considered haughty or hypocritical if I were to declare that I empathize with Stephen Daedalus (or James Joyce)? Will I be labelled as a freak if I admit that I am so constantly deluged by those streams of conciousness in me that I am endlessly combating the urge of utter withdrawal?
Like Stephen I once attempted to sought comfort in secular entertainment, in his age it was periodic prose and in my case it was rock-n-roll or pops; I once sought for comfort in religion, in Gods, drawning myself in the lyrics of "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 reading Bible, getting to know Jesus, talking to god; I also was driven by antiJesus movements, nodding in full agreement when reading aloud that "those judgements and redemption things are sheer nonsense"; I found difficulty in communicating with my parents and my family, who have driven me to learn English and adapt myself to that related culture at my very early age and made me feel unsatisfied with and ashamed for my native culture and impart an alienated feature in myself so that certain type of uniqueness is partaken by me and Stephen is the rebellion son who tried but failed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ather; then we(Stephen and I) both made Godess/God out of ordinary woman/man to fill ourselves with amazement and awe, we share the same aesthetic suspectibility --we loved him/her at the first sight, perfectified that special somebody then witness our dreams shattered; Stephen was a pseudonym used by Joyce and Joyce expressed his unothordoxical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tuality, and thanks god I have been a girlschool student as long as seven years and I simply cannot think that lesbian are all amoral and I certainly have formed my own criterion of femininity. Yet we are not just filthy sextuality-addict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our nation, Ireland or China, we cannot feel blissful since our motherlands are not what we dream of and are facing fundamental problems that beckon satisfactory solutions. And ultimately, when all resort to invite that epiphany he discribed failed, he packed his luggage and bid his hometown farewell. Fare thee well he might have said, before he trod new ground and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art, and left me staying up till 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 contemplating over a solution for myself.
What do we remember as an infant, a child, and a curious youth? The knowledge we conceive affects our conciousness, in which lies the individual approach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unique perspective by which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in soundry fields, art, philosophy, sociology, science, are observed and understood. Stephen's reminiscence of his life experience shows his attempt to self-analyze. He believes, I reckon, that every single person has his/her own way of taking cognizance, that his own streams of conciousness is unparalleled. Nobody is being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his. Nobody could be the guidance, the messenjah. Nobody could guide him along the path, and there is even no path. He realizes that he is treading new ground. He despises the Irish system, political, educational, religious, that have laid intertwin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nation. He wants to turn to his parents for a solution. But that is not possible. Stephen has to justify his wild existance and his vivacious independence by believing in theories created by himself. These theories will neither be acknowledged by the Irish nor by the Britons. They perch on the hyphen traversing them. And Stephen perch on them. And he is permanently trapped in an emotion of embarassment, agony, ambiguity and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Stephen retains his ecstacy in the idealization of a neighbouring girl he barely knows, Eileen Vance. He has been an rebellion in so many aspects that he constantly feels the inner weakness. He wants a woman who is transcendent and superior to curb his wretch feelings, and without her, life would be too hard. Virgin Mary is his spiritual goddess, yet when she becomes elusive and impalpable, he turns to the ecstacy for Eileen.
After a real conversation with Eileen, however, Stephen's ecstacy collapses. Eileen is no longer the holy female he pays homage to. Previously, Stephen polarizes all female. Women are either unapproachable virgins like Eileen with totally satisfying femininity, or slutty whores with whom only sinful lust will be associated. Yet after that conversation, Eileen's image deteriorate to an average human being, neither holy, nor sinful. Stephen realizes that mortals cannot be his god.
The darkest period in Stephen's life, in which seemingly all things turn against him,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his family declines enormously.
His father is so nostalgic of the glorious days of the past and so afraid of shatter the illusion that he often gets drunk to shun the throes.
Stephen feels that religious redemption is intangible.
The perfect image of Eileen is broken.
Constraints and lack of freedom in the Irish system constantly bothers Stephen.
It is in the gloom of hopelessness that Stephen seeks for new way out. It is in his childhood days that he conceives that he is aiming for the lofty goal that will satisfy his inarticulate pleasure his life. And finally he resorts to art. Art could be the only thing that relates to his life. Stephen eventually envision himself as an artist in pure pursuit of art and aesthetics.
As I am reading the book, I am frequently disturbed by my own expedition to identify with Stephen and my stunning success of finding some resemblance between me and Stephen.
I started English learning when I was three thanks to the influence of my family members. English and the culture it is based on has always been an inseperable part of my life and indeed, my consciousness. My life so far seems like an attempt to strike the inner balance of Chinese elements and American elements in my mind, since I am the only Chinese kid of my maternal cousins. The influnce of American culture on me has arrived so early a time that I was by that time even unaware of the actual meaning of culture for its sake. I funtioned all along. I triumphed in thinking in English since English is a part of my stream of conciousness. I share lots of characteristics of my Chinese peers. But when it comes to some of the basic practice of cognition, I oftenly shift into the American way. As I have stat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s, early experience contributes to form our conciousness, our exact unique way of understanding of world, and different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way of approaching to the problems continue to result in diversed stream of conciousness. I am finding myself being different from my peers in a few fields, which leads me to the mire of agony of self-analysis. From when does I start being different? Can I justify the discrepancy? Will I be understood? Am I being differnet simply because I am a rebellion? Or am I being different as a result of failure to cope with the hitting of both cultures in my early age?
My failure to get a help from my parents or my uncles is reasonable. My parents want me to learn English well so they let me learn it early. But they do not have fluency in English. My uncles are American citizens but they didn't learn English in such an early age. My cousins are Americans who definitely ar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but are illiterate in Chinese. My family has turned me into a blend, a weird blend seeking for an identity without forfeiting any alienated part as they have been in me all along. I suffer to some extent the difficul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my parents and family, which gives me the woeful feeling of expatriation. Thus result in my endeavor to find anybody out there who could understand me, which then leads to my idealization of a boy, which has been proven as an utter failure and has add to my inarticulate pain. The feeling of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concern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etc and inclination of way of entertainment are also huge and inappropriate to elaborate on. These make me empathize with Stephen's pursuit and conviction on perhaps a very superficial level.
As I get to know Joyce's repudiation of catholic ireland and his countering declaration of artistic independence and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writing, I sense that I can feel his longing for achieving the independence from both the old Irish way and the liberating ways he has oftenly been immitating. He wants to expel himself to a safe distance to both ways so that he can by himself cling to the good elements and deter bad elements in both ways. And his resort is in art only.
That artistic freedom both Joyce and Stephen are struggling for is also exactly the freedom I long for since I contend only in freedom and through freedom can I work out my own solution.
是啊,为了我的这个爱/我已付出所有的一切;/因为她越变越好看,/而我越变越疯邪。
——乔伊斯[1]
一、乔伊斯讲述自己的故事
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上半叶英语国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1902年赴欧洲,开始侨居生涯。他的几部重要作品讲述的都是发生在都柏林的事情。而他的早期作品之一《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是他对于意识流创作的试验。同时也证明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们的苏醒》中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的意识流技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艺术实验,而是在早期创作中已经开始酝酿的了。[2]
《画像》是乔伊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书中卷首语引用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八卷中的:“他用他出众的才思开拓出新的艺术领域。”而书中讲的就是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童年、少年以及青年的心理成长过程,和他的艺术觉醒。也许书卷首的“他”与其说是斯蒂芬,不如说是作者自己,是作者创造出了意识流写作手法。
二、讲“故事”时,乔伊斯选择了意识流
意识流之一概念最初是心理学术语,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一段的碎片”,它“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流动的,我们就称它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吧。”[3]
《画像》一书中主要运用了内心独白与自由联想等有意识流特征的手法。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章斯蒂芬生病住院后的那段心理描写:
窗外的光线是那么灰暗啊!但是,看起来很舒服。火光在墙上飘忽不定。简直就像波浪一样。有人在往炉子里加煤。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们在谈些什么。这是一种海浪的声音。也许海浪一起一伏,在谈论它们自己的事。[4]
这里说到小斯蒂芬把人的声音听成了海浪的声音。而文中后来描写了他在生病迷糊中看到的大海与海员的情景。而且在这时,斯蒂芬第一次有了“死亡”的概念。这是一个孩子生病后的感觉,很虚幻,但是很真实,让读者了解到了主人公心理的成长过程。
书中的情节就是在这么一系列的内心独白与自由联想中发展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关系也是这么含糊的表现出来。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要自己去通过人物的心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如北大教授吴晓东说的那样:“现代主义小说使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5]
三、结构的创新。赋予全知全能的“他”。
在刚开始读《画像》时,也曾为一个个破折号后面的没有引号的对话烦恼过。然后就慢慢习惯了,并体会到了这么一种电影式的对话模式,给予小说生命,仿佛他们就在你的周围讨论这宗教、命运以及欲望等等的一切。戴从容把它称为一种乔伊斯创造的“特殊形式”,它“突出形式在文本中的功能”,而“这种现代手法直到《画像》才出现”。[6]
《画像》一书中有不少人物对话,无论从开始在食堂里同学间的争吵,到家里那场宗教与国家的辩论,再到斯蒂芬与忏悔神父的交谈,大量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使文章的结构变得松散,仿佛读者并不是在读一本小说,而是看一本剧本。然而,这些对话却把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与文中的心理描写相得益彰。我们很难从一个人所做的事中了解一个人,但是我们却能在他的话、他的思想中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也许这就是乔伊斯运用大量对话的原因吧。
而书中用的是第三人称的“他”,却赋予了“他”全知全能性。读者不仅可以读到“他”的故事,同时能读到“他”的所思所想。这种“直接的内心独白”可以让读者看到了最原初的、不加整理的、没有修饰和控制的意识活动,是一种与读者最贴切的交流方式。这与20世纪小说观的一种主导倾向——崇尚作者退出小说是很符合的。仿佛是“他”在讲“他”自己的思想全部透露给读者,让读者对人物有一种更好的认识。
四、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家的画像
乔伊斯的作品不多,但是每部作品都成为了争论的对象,这与大多现代小说家的遭遇都颇为相似。但是他们却超显存在,对此漠不关心。就像《画像》中斯蒂芬说的一样:“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的他的艺术作品之外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7]
乔伊斯给自己的这幅抽象的“自画像”让人难以接近,好像并不是为别人而写,而是为自己所作的,是一种想象与叙述的产物。这与高尔基等传统的作家的自传体小说有明显的区别。在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中,读者读到的是一幅幅这时的俄国生活写照。也许这就是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最大区别吧。
五、参考文献:
[1]:[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傅浩译,《乔伊斯诗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92页。
[2]:吴晓东著,《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6-43页。
[3],[5]:吴晓东著,《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89-91页,序论(1-6页)。
[4],[7]:[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黄雨石译,《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25-26页,246页。
[6] :戴从容著,《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太感谢了!!
这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再也无法圆谎的世界,詹姆斯•乔伊斯选择了彻底的堕落,这不是玩世,而是放弃,因为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这世界的荒谬,只好用自己的态度,来寻找同伴。
你觉得斯蒂芬的觉醒对漫长的人生来说是福是祸?孤独,他不怕的孤独,因为他内心有对灵魂 真知的态度。 但这样没人相伴的孤独孤高会不会使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幻境里呢?
是不是flung?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试:
怜悯是这样一种情感:在任何深重而恒常的苦难面前,怜悯控制人心,叫它与那受苦之人连结起来。恐惧是这样一种情感:在任何深重而恒常的苦难面前,恐惧困住人心,将它与那隐秘的缘由联系起来。
只在快10年前读过黄雨石的版本。
但,单就楼上上上的那段文字来说,我觉得是黄雨石最佳。
如果记忆没错的话,这一段是迪达勒斯和一个耶稣会的神父谈论哲学问题,按照经院哲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方式,对怜悯和恐惧进行定义。
放在这个语境里,黄雨石的翻译是最有经院哲学味道的,也是最符合“对一个概念下定义”这种语言行为的,尽管它初看上去有点叫人难以捉摸,但实际上,更简洁,更严密。
乔伊斯从不徒有虚名
——第三人称的叙述与第一人称的视角交替。
鬼斧神工很突破很牛|流的感觉
皱折?皱褶?
他自己其实是烧毁了这书,他妹妹抢救的,谁知道是不是原版呢
啊,ls真的假的呀
回LS,上周老师上课时候才学的
结尾结得有意思。
而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
这是乔伊斯《都柏林人》里面《死者》的原句。
无语中……
基本都是些general的概論,沒有任何針對的分析。太空。
赋予时间以具体的形式——————不错
顶啊!!!
原来以为会很晦涩但是发现很朴实啊!!!
好文章啊
徐晓雯
不欣赏李靖民译的这版,语言的色彩与原文不匹配
我更喜欢李靖民的 从这段对比看他的更适合中文的习惯 不会假意文邹邹
李靖民译的应该是这三种里比较好的一个了。其实小说开篇处的对照更容易看出来,会发现谁译的好不好,甚至谁译的是不通的。
显而易见,徐晓雯的好。比如urbanely这个词,黄雨石和徐都做到了信,但徐更达。而李的译法,不准确。
再看看原著吧。两个人都差点打起来,怎么可能礼貌周全呢?翻译不是查字典,堆砌词语,要真正反映出原文的内涵和韵味。我觉得赵松说的对,小说的开篇更容易看出来谁译得好。李靖民译得是最严谨,最准确的。
再比较一段
Suddenly he became aware of something in the doorway. A skull appeared suspended in the gloom of the doorway. A feeble creature like a monkey was there, drawn thither by the sound of voices at the fire. A whining voice came from the door asking, “Is that Josephine?”
黄雨石译:突然他注意到门口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在黑魆魆的门洞里仿佛出现了一个悬在半空的骷髅。一个瘦弱得像猴子一样的人出现了,它显然是因为听到火炉边谈话的声音跑来的。门口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问:“是约瑟芬吗?”
徐晓雯译:突然间他注意到门口有个什么东西。一个头颅仿佛悬搁着出现在昏暗的门口处。有个瘦猴般弱小的身躯,听到炉边有说话声,就来到那里。门口传来哼哼唧唧的问话:“是约瑟芬吗?”
李靖民译:忽然,他觉察到门口有个什么东西,原来是一颗脑袋从黑乎乎的门洞里探了进来。接着,迈进一个瘦弱得像猴子一样的小姑娘,她显然是循着火炉边儿说话的声音跑来的,站在门口哼哼唧唧地问道:“是约瑟芬吗?”
还是最喜欢黄老的版本,忠实,也好懂,不愧是钱先生的高足,求真。
更喜欢黄雨石的笔调
显然是徐的条理清晰,英文理解和汉语表达能力都高出一筹
喜欢徐晓雯的,跟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像。
李的思路清楚,表达也清楚,这是中国人能看明白的思路。
...第一感觉是徐比较文气...黄很保守... 李的...放得真开 ...其实按忠实度的话还是喜欢黄的版本w
我只看过李译的. 看的时候有些地方觉得怪怪的.
Cranly pointed his long forefinger at him.
“Look at him!” he said with scorn to the others. “Look at Ireland's hope!”
They laughed at his words and gesture. Temple turned on him bravely, saying:
“Cranly, you're always sneering at me. I can see that. But I am as good as you any day.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about you now as compared with myself?”
“My dear man,” said Cranly urbanely, “you are incapable, do you know,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thinking.”
冒昧地翻一下:
克兰利戳着他那长长的食指点着坦普尔。
“瞧他!”他含讥带讽地对众人说道。“瞧这位爱尔兰的希望哟!”
他的言谈和手势惹得大家齐声哄笑。坦普尔勇敢地转向他,说道:
“克兰利,你老嘲笑我,这点我明白。但是随便哪天,我都不输于你。拿你和我本人比比,你可知我对你是什么看法?”
“我亲爱的人儿,”克兰利语气温雅地说,“你无能,知道吗,压根不配思考。”
不好意思,你这个译文里有两个错误:
1. “turn on sb.”是一个固定短语,意思是“attach in words”,即是“用语言攻击”,不是“勇敢地转向他”。
2. “any day”也是一个固定短语,意思是“anyhow”,即“无论如何”的意思,不是“每一天”。
还有上面提到的“urbanely”这个词。乔伊斯是人们公认的语言大师。看看原文中这个词两边引号里的英语原句,就知道乔伊斯用词的特点了,不然再看看整部小说,用词独特是他的特点。大家想想看,他会犯徐译那样的低级错误码?再说了,其实刚才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固定短语的理解错误,在徐译版本里有都出现了。黄译和李译是正确的。
楼上,请问,你凭什么认为“urbanely”可以有讽刺的意义,而“礼貌周全”就不可以是讽刺意义呢?难道一定要直接译出词语背后的含义,而不是准确传达原文,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吗?你对翻译的理解太死板了。犯低级错误的只是你自己。
另外,徐译中的“他们对着他的话语和手势哄堂大笑。”也有问题。“对着他的手势哄堂大笑”还算说得过去,但怎么能说“对着他的话语哄堂大笑”?。第二个比较译文的徐译“头颅仿佛悬搁着出现在门口处”和“身躯来到那里”都不讲不通。前面有人说,徐译忠实原文,可原文里也没有“仿佛”的意思呀。可见徐也觉得“头颅悬搁着出现在门口处”不合情理,加了“仿佛”二字,但即便是这样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头颅悬搁着出现在门口处”表达确嫌生硬,可以处理得更好,但仍然体现了译者忠实原文的意图。那种一个人的脑袋悬在那里,身体隐没在昏暗中的画面感。“一个脑袋浮现在门口的昏暗中”也许好一点。黄译“骷髅”是不准确的。李译直接把背后的含义译了出来,有添加,谈不上忠实。
any day是“随便哪天、不论怎样”的意思吧,我翻译的这处貌似也没错吧。
2010-12-26 20:53:03 purplepine
楼上,请问,你凭什么认为“urbanely”可以有讽刺的意义,而“礼貌周全”就不可以是讽刺意义呢?难道一定要直接译出词语背后的含义,而不是准确传达原文,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吗?你对翻译的理解太死板了。犯低级错误的只是你自己。
+65535
是啊,翻译除了应表达出原著的感情,还应该表现出原著所表现出的感情表达方式。
编辑病突然间发作,发现标点符号都有问题。
单说“They laughed at his words and gesture. ”这一句的处理。初涉翻译者常犯的一个毛病,是指示词用得太多,如本句中的“他的”。比较前面各位的翻译:
黄:他的话和他的动作引得他们大笑。[第二个“他的”多余。]
徐:他们对着他的话语和手势哄堂大笑。[如评者所言,“对着话语”不通。]
李:他的话和他的动作引得大伙一阵哄笑。[第二个“他的”多余。]
名字让我无法可想:他的言谈和手势惹得大家齐声哄笑。[此译最佳。]
黄:他的话和他的动作引得他们大笑。
个人觉得这样也不错,读来 话与动作 都凸显了。
“...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about you now as compared with myself?”
“My dear man,” said Cranly urbanely, “you are incapable, do you know,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thinking.”
一问一答间逻辑关系:你知道我心里正怎么"看think about"你吗?而后针对think,cranly讽刺的是temple更本没能力"思考thinking"。从这点上看,很明显李译发挥得太远了,不太好。
不过我依然觉得李译很不错,胜在语言地道,很活,翻译腔几不可查,就阅读起来的流畅感来说,李译最顺(代价也有就是)
我喜欢黄译一点,符合我的语言习惯
徐译最贴合原文,但读起来不是很流畅。李译很流畅,但跟原文的风格有偏离。黄译介乎二者之间。
围观+学习
如果译者无视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及本质性差异,不考虑两种语言各自特点鲜明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在译文里生搬硬套原语的文字表现形式,那就无异于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就拿上面列举的几个翻译实例来说,如果译者硬是要机械地对应着英语原文的文字表现形式来转换成汉语,那么其产出的所谓汉语译文,要么会缪传英语原文承载的信息,要么就是蹩脚的汉语,佶屈聱牙,不堪卒读。
林语堂先生在其《论翻译》一文中对此种译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此种译文既风行海内,其势力蔓延所及,遂使译学博士有时候也可以给我们三十六根牙齿嚼不动的句子。(林语堂1994:306)
作家王刚先生也在其以《我们不能容忍外国名著被翻译成蹩脚的汉语》为题的一篇博文里,谈到的了他对此类译文的感受:
读的时候,根本没有阅读的快感,脑子里也没有形象的画面感和丰富的联想,只为那干板直硬的翻译揪掉了不少头发,有的词语直译得令人发指,有的词语我这辈子根本没有见过,完全是翻译家的发明。那完全是满嘴外国话的汉语,让人生疏的不得了!
这样的作品哪里还能愉悦读者,阅读简直变成了一项任务!(王刚 2010)
见李靖民著《英汉翻译实践要略》
如何提高英语翻译能力
(摘自李靖民著《英汉翻译实践要略》
作为一名从事英语翻译的译者,尤其是初学翻译者,要想学好翻译,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性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
一、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恰当而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跨文化信息传递活动,其本质是信息传递。从形式上看,翻译活动的确需要涉及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在实质上,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本身的表现形式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译者是信息传递者,其所从事的活动绝不是简单、机械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对应转换,而是借助语言这个信息载体的转换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传递活动。
译者的工作对象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两种语言及其使用者。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跨文化信息传递活动,就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原语解读作者寄载于原文的各种信息,并通过译语把原文所承载的各种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也就是译者借助两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把原语作者明确表达的和隐含其中的消息、思想、观点、意志、情感等各种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
这个活动涉及三个主体:原语作者、原语读者/译者、译语读者(这里的原语作者、原语读者/译者、译语读者也分别指原语说话人、原语受话人/译者、译语受话人,以后不再赘述)。首先,原语作者作为信息传递者,将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信息,以符合原语文化传统规约的表达模式寄载于原语文字(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讲,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翻译过程);第二,译者作为特殊的原语读者,即信息接收者,通过原语载体获取原语作者传递的信息;第三,译者作为信息传递者,将其从原文获取的信息以符合译语文化传统规约的表达模式寄载于译语文字;最后,译语读者通过译语载体获取原语作者传递的信息。
可以看出,翻译活动始终是围绕着跨文化信息传递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因此,作为译者,了解翻译的信息传递本质,认识自己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信息传递活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翻译质量的优劣,取决于译者通过原语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通过译语传递信息的能力。译者必须在充分而准确地理解并获取原文所承载的显性信息和各种隐性信息的基础上,尽可能恰当而准确地用译语将原语作者意欲表达的各种信息比较完整或曰忠实地传递给译语读者。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完整”或“忠实”往往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尽可能减少信息衰减,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信息冗余,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般说来,原文作者在将信息寄载于原语文字时,总是会预设其确定的读者对象能够根据各种共有的知识和经验,推理明了其意欲传递的信息,包括语言文字本身体现出的表层的显性信息和伴随的隐形信息。因此,译者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要想比较充分而准确地获取原文承载的各种信息,就应当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在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努力发挥相应的推理能力。
译者在将其从原语获取的各种信息寄载于译语时,需仔细分析两种语言载体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避免受到两种语言文字表现形式本身的束缚,应根据具体情况,以信息传递为中心,在译文里对各种信息的比重进行恰当的调整,以便按照符合译语文化传统规约的表达方式,来确定译文中比较恰当的文字表现形式,来安排译文信息层次的顺序,使读者能够以最小的认知努力来获取最佳的语境效果,从而能够比较充分而准确地获取原文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
三、作为一名译者,应当自觉地培养自己的翻译意识。也就是说,译者应当在了解翻译的信息传递本质,熟悉翻译涉及到的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及本质性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翻译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去体会翻译,认识翻译,提高自己作为译者的自觉意识,从而在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心中有数,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可以怎么做,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能力。学习和了解一些翻译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是仅仅了解和熟悉翻译理论知识,并不一定就能够成为一名好的译者。翻译家金圣华女士在她的《桥畔译谈》中说:
太多人说过翻译者就像演奏家,原著就好比乐谱,乐谱上的万千音符,必须通过演奏家的演绎,方能以优美悦耳的乐声,传到听众耳中。……很多人以为学会两种语文,就可以从事翻译,其实翻译的技巧精妙得很,空谈理论而不加实习,根本不会明白译事的艰辛。(金圣华 1997:33)
正如演奏员应当懂得基本的乐理知识一样,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译者也应当了解一些基本的翻译理论知识。但是,也正如演奏员仅仅懂得乐理知识,不等于就能演奏出优美悦耳的乐声一样,译者若仅仅明白翻译的道理,而不能把这些道理灵活地运用到翻译实践活动中去,缺乏翻译实践能力,是无法成为一名好的译者的。翻译实践能力的提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译者必须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没有大量的实践历练,不可能在实质上提高翻译能力。
或许看看其他翻译作品,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下面是英国作家杰克•林赛的《被出卖了的春天》(Betrayed Spring)里的一段文字的译文:
Sure enough, Tremaine lost his job. …. He remained in downcast silence till Phyl joined in; then he turned on her, “Every time I listened to your advice, I got into trouble. It was you who urged me to join the demonstrators. All right, I blame myself. But it’s the last time. We were cat’s-paws, that’s all.”
“Cat’s-paws!” cried Phyl, so indignant that she couldn’t muster her thoughts.
“Don’t bother your Dad,” said Mrs. Tremaine. “He’s got a lot on his mind.”
果然不出所料,屈里曼丢了工作。……。他垂头丧气一声不吭,直到菲儿插嘴说话方才冲她发起火来:“每回我听了你的话,总得倒霉。都是你催着我去跟着那帮人示威。得,怪我自己耳朵软,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啦。明摆着,我们上了人家的当。”
“上当!”菲儿喊起来,气得想不出说什么才好。
“别跟你爹爹顶了,”屈里曼太太说。“他的心事够多了。”
给大家推荐两篇文章读读,会对这里的讨论有帮助:
李靖民的“解读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来源:http://360.bigear.cn/news-87-105165.html
尤妮娅等的“透过翻译美学探析《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两个中译本”,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ceea143d4431b90d6d85c718.html
真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去找来英文本看。
这本书的文体是随着主人公的成长一直在变化发展着的,开头的童年部分你可能会感到有趣而浅薄,但后面会越来越耐看。
嗯 说得好了!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为乔伊斯的早年之作,没有捉弄人的文字游戏,没有故作高深的哲学探讨,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也没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讥嘲"
“年的懵懂和恐惧,少年的狂躁和不安,青年的困惑和清醒。这是一个灵魂企图摆脱束缚的奋斗过程”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9/11/18
请问是您吗?
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中华读书报》的,承蒙愚行豆友的提醒,我刚刚看到了那篇文章《乔伊斯从不徒有虚名》(署名雨嘉)http://www.gmw.cn/01ds/2009-11/18/content_1010392.htm。怎么说呢,雨嘉抽离了我这篇游戏文章中最具概括性的文句,也是我自认为比较得意的文字,能被雨嘉如此赏识,而且还和伍尔芙这位大美女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意外之极,荣幸之至!
嘿嘿,亚细亚兄真是豁达
不大厚道..
靠谱的书评
部份語句明顯是摘抄的。
2011-09-15 14:28:35 曼仔 部份語句明顯是摘抄的。
哪一句是摘抄的?点出来服你!
你自己對比一下你的和這本書的最受歡迎評論。。。
无语了,拜托楼上看看发表日期好不好。
青岛出版社的那个版本我也收着一本。注释是做得蛮好的。看第三遍时,就用的那个本子。
@亚细亚人 难道这位是译者??
to 神秘的奎恩先生:
您太高看我了。译者是黄雨石先生,1919年生人,曾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钱钟书先生的学生。
因为我看你说雨嘉的句子有来源于你的文章的,但是我看雨嘉的那篇文章和李靖民先生的译后记那篇里面很多类似的,所以我误解为。。。。。。。不好意思啊。。。。。
真不是你英语水平差 跟爱尔兰人提乔伊斯他们也是要皱眉头看不懂得
@神秘的奎恩先生: 这个楼里。。。还有我学长的朋友 今天被提醒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