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
2010-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奇生
457
无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本书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前言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 区长 五 乡镇长 六 保甲长征引文献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一“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技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党派之上。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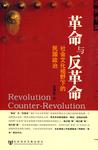
无
作者详细阐述了革命词语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形成分析,和国共两党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和革命历史观为自己夺取政权,捞取人心获取政治利益而服务的。所谓的革命与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集团自己塑造出来攻击政敌的工具,而这一工具的塑造对中国现代历史影响极大,从1911年到1976年其实就延续了这一个极端的过程。而把不同与自己意见的一切都打成反革命和极端排他性思维依照我看来更是中国民智启蒙时代的结束,极端主义忽悠时代如十年动乱时期来源的重要思想起源。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再见了,革命!就是直到今天,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官方思维在两党笔下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排斥的狼奶教育,培育出来的左右派极端粪青在国内如此之多也丝毫不奇怪了 在王奇生看来, 1920年代三党竞争革命话语是随意性的典型体现。国民党提倡国民革命,共产党提倡阶级革命,青年党提倡全民革命。三党在革命目标和对象的设定上并不相同,但均以革命党自居。与此同时,各个党派甚至派系内部,争夺并垄断对革命的解释权,将反革命的头衔加到对方头上,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视革命同路人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在此基础上造成了后来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滥觞。
王奇生深入分析了三大政党围绕着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互动,以去熟悉化的眼光检视革命话语和革命文化的建构。不仅是检讨革命话语的正当性问题,许多近代史上的热点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中也被重新研究,比如二三十年代中共上海和地方基层党组织的生存问题,战时校园中的国民党党部和大学教授入党问题,乡村绅权的演变和基层地方官的转型问题等等。这些集中起来的关键问题经过重新分析,定论后面多了一个问号,给人最深的感觉就是,看似熟悉的民国政治和民国社会,还有很多东西有待重新诠释。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近代史书籍,执笔持中,论述缜密。
题目是:革命与反革命,但是全书展开来,在前半部分已经将这个问题说明。后面更多的是介绍民国一些真实的历史的细节层面。
目前在近代史的研究出版方面,似乎尺度有所松动,论点越来越公正客观,史料也越发详细。而且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书,这一套《近世中国》只看完两本,都不错。
这本书是目前我所读到的民国史中很棒的一本,不仅仅是论点客观公正、史料翔实丰富,更重要的是文笔非常棒,难得!
书中的官邸很有见地,很启人反思“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如何界定”——不过是话语权罢了
革命与反革命,是王奇生的代表著作之一,对于中国的近代史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值得一读!!
“革命与反革命”是一部非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
该书写得非常细致,对档案、文献做了细致的梳理,让我们对当年的国共状况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具体人物有了新的评价,值得一读。但是书中似乎对革命与反革命这一主题不是太充分
很客观的对国民“革命”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不仅涉及到国共两党,还有当时颇为活跃的青年党,对三党竞革的描写,对于准确地理解当时的历史很有帮助,也能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是怎样从北洋时代进入国民党时代的。作者引用数据真实、翔实,很有历史感,发人深省
用更加宽阔、宽容的视角来分析民国政治,及其支撑政治运营的社会、文化基础,可使读者更加全面、客观的回顾历史、正视历史、还原历史,并以此为鉴,透视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环境。毕竟,历史是延续的。
绝对值得一看的好书,作者从一个较为微观的视角观察了民国初期的政治,作者的结论得自一些曾经不为学界重视的资料,因而该书有很强的可读性。
不带有色眼镜看历史,很不容易。本书引人思考。
学习中国历史!正在看……
通过最为基本的社会视角来看中国这个社会。
从另一种角度写历史
资料非常详实,让我对真实的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叙述比较客观到位,对于厘清当日各种学说主义之争大有裨益。
民国百态。
不用说了,当当怎么还没给我加积分啊
耳目一新。从教科书中跳出来,换个角度思考。
读起来会有一种另类角度,足矣
研究近代史应该看得一本好书,值得购买阅读收藏!
王奇生先生的继《党员、党权与党争》之后的力作~非常好,值得所有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阅读!
王奇生的奠基之作,水平很高,近代史难以忽视一本书
和王奇生的另外一本书《党员党权与党争》一样,既有论文般现实的史料论证作者的论点,可读性又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这本书一定要读
这本书看过 留个纪念
留着细细品读
王奇生教授的作品,很富启发性,值得一读
不错,有学术味道,作者心血跃然纸上。
不错,不过还是有一些旧东西
年读好书,应该不是浪得虚名
标题党,如题呗!!
不敢多说什么,只能感性的说书拿着很舒服啦
虽然是论文集,但是挺有新意。值得看
正在拜读中~
值得读。信息量大。
已经窥探很久的书了,赶上活动赶紧买了。。呵呵还没读~不过一定不错
书不错 很值得读
还可以,大陆写国民党的书只能这样了,有总比没有好。
王奇生老师的书很值得读
王奇生老师是民国史研究的大家,在二档的经历无疑使他的作品更加可信
王奇生的书,每本都是精品,都值得一读。
经典的,一定要看
视角创新
书质量很给力,绝对正版!
视角与众不同,难得的好书
切入点比较新颖,类似的书在市场上比较难买到,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做得很到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材料翔实 叙述精要 好好学习~~~
一直喜欢他的著作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喜欢与不喜欢,在于你是否喜欢这个题材方面的书了
没事的事假翻翻,挺不错的
值得购买,值得收藏,有深度
王奇生老师的大作,值得一读。
内容还未看,但是整体排版印刷都挺好。
作者的治学态度很严谨。
大概翻了一遍,感觉不错。值得购买
专业书有内涵,很不错
(一)
由埃及起,中东及非洲一带的“革命”正风起云涌。
我躲在家里每天上网眺望一下局势,看到穆巴拉克终于收拾起家伙事儿跑了,卡扎菲到目前还死撑着,估计也已是秋后的蚂蚱。然后就是看王奇生的这本《革命与反革命》。
说实话,这个时候看这样一本书,连自己都怀疑,我是否包藏祸心,惟恐天下不乱,有静待其变之嫌。更有甚者,是否也如这个季节感受到了地气的虫儿有些蠢蠢欲动?不过总起来说本人绝对是“守法公民”,基本上只围观不说话,不发表煽动性语言,不表达欣喜兴奋的态度,顶多笑一个呲牙咧嘴的,以做在场证明。看书不过是想看看每当革命爆发,是否有些共同的特点,有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先兆,什么样的结果,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律。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给我预期的答案,它只是历史叙述,规律要靠自己去寻找。
(二)
作者说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是战争和革命。要我说,战争只是革命的表现形式。说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事实上,战争有些也是文人发动的,是文人革命启用的形式。
中国的革命狭义地算,从1911年到1949年,历时近三十年。宽泛地看,往前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往后可以延伸到1976年文革结束,共计八十年时间。前三十年国民党主导,后五十年共产党主导。
1949年国家政权更替,中国革命并未终结,之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后的革命,较1949年之前的革命,范围更广,席卷全国,参与人数更多,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
这期间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年--1927年,一次是1966年--1976年,两次“大革命”不仅是名称相同,而且采取的手段也有相似之处。文化大革命中的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等,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就曾经用过。
(三)
本书的实际内容与它的副标题更为契合,即“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它的副标题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副标题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药名”和“商品名”,如“达克宁”是商品名,“硝酸咪康唑”是它的药名。再比如“皮炎平”实际成份是“复方醋酸地塞米松”。真正起效的是商品里所含的药物成份。这本书的商品名为《革命与反革命》,其主要内容讲的是“民国政治”。
本书涉及内容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个人、社会、群众、党的关系,三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在革命与反革命问题上的互动,反革命罪的缘起,党员、党组织与都市及乡村的关系,国民党权力机关的演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蜕变与转型等。个人感兴趣的有这样一些:
一、三大党派均大力宣导“革命”。清末以来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法政之不成功偿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掀起。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渗入大众层面,革命高于一切,甚至成为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反革命”则被建构成一种最大之“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三大政党之争不在于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的方法。所采取的革命方法不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所设立的目标不同而定。
二、国民党执政22年,可以说没有建立起集权。1929年,国民党仅控制了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控制的地区达到25%,人口扩大到66%。它能毫不含糊控制的省仅限于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国民党向基层的渗透也远远实现不了对基层的控制。以西南联大为例,看国民党对大学的控制。
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广泛在大学里高立党部。国民党中央对大学的唯一法规是规定大学区党部有权列席校务会议,仅仅是“列席”。事实上,国民党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区党部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不参与不干涉学校的行政。
西南联大约50%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对于其它党派的人都能给予包容而不加排斥。是“民主的保垒”、“自由的堡垒”。
——“联大容忍精神的最好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轮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治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方面批语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协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1946年《观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撤销了军队和学校党部,将校园拱手让给了中共,中共在大学校园里的活动日趋活跃。这是国民党中央的一大失误,国民党让出的阵地,中共全都接手了。共产党占领了农村、工厂、学校等国民党组织薄弱的广大阵地。
(四)
我是不赞成革命的。并不是因为反对革命通常所使用的暴力形式,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也不是害怕有人要被杀头,杀头要画圈,有的人画不圆,念念不忘要重新画。“要革命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也不是因为目前生活稳定,算得上安居(算不上乐业),担心革命失去现有的生活,因而具备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犹疑性和不彻底性。也不是因为我不是流氓无产者,不期望翻身解放,不需要借革命之机去“摸小尼姑的头”。这些都不是。
我之所以不主张革命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革命这种手段并不能给我们造就一个好的社会。它毕竟不是水到渠成的正常手段,而是人为地去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非常手段。纵向比较中国历史,横向比较世界历史,靠革命获得一个美好社会的几率微乎其微。我们缺少启蒙,我们缺少启蒙的程度堪比中世纪的欧洲。(可以做个课题)
我们喊了近百年的启蒙,并不是启蒙本身有多么困难,而是当局本意上不允许启蒙,现在还在往外抬两千年前的孔老二。其实启蒙说难也难,说易也不难,就是允许各种思潮自由辩论!
(五)
天渐渐暖了,傍晚的时候骑自行车出门,华灯初上;微风,吹面不寒。
不想买也没什么可卖,最后进了新华书店。绕过了商务印书馆的哲学架,是我最想看又最不敢看的,怕把自己看呆了,现在似乎已经有了苗头;又绕过了中华书局的历史架,文言,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走到人物传记架,不想看,在我们国家,评价人物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人物写得不伦不类,我们能看到几个对于历史人物的中肯的评价?!
清风不识字,何时是个头儿啊?!望着诺大的图书卖场,除了吹喇叭、抬轿子的,除了风花雪月哄小孩儿的,除了养生保健防防治百病的,但凡有点儿思想内容的无不云山雾罩。在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
蒋介石: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的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而说出这句话正是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南昌,这就是历史!
革命总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词。
有助于深刻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
在导师办公室里的桌子上看到的这本书,就打算自己也买一本,书兼学术与文学性与一体,很有趣味性,喜欢历史和政治的读者不可多的的一本好书。
对于一个影响了我们那么深刻的历史名词如何形成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里面提到的关于GCD的某些事实也是很有趣的。
很少看民国的书,但是这本一定要看看
资料较可观全面,对了解历史很有裨益。
学中国近代史的可以买一本。
希望大家都习惯这本书
王老师的这本书很不错,值得买,绝对不错,值得一读,强烈推荐
大致翻了翻,感觉有点枯燥。可能仔细看的话,有些地方能够让我爱不释手的。
王先生的扛鼎之作。。。
有深度,有内容,耐读
王奇生先生的作品还是值得一读的
书的质量好,给孩子买的,说不错。。
视角独特,文字犀利
严谨,很好的书,值得一读。
比较有意思的书...在洗手间读的话能够拉久一点
内容不错,值得一读,很棒的书。
很喜欢,纸张看着舒服,价格合理。
之前看过王奇生关于国民党方面的著作,感觉挺好。
人写的历史变来变去,希望越来越接近真相
感觉材料铺排多,分析少。历史现象描述多,解释少。
有些观点比较新
這本書印刷較差,出版社為了省錢,把腰封直接印在書上,不喜。
很难让人能一口气看下去
一本不错的书,闲的时候开阔一下眼界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二次買這本書了
比较好,值得一看,推荐一下。
给老婆买的书,她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