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短篇小说选
2008-3-1
译林出版社
埃德加·爱伦·坡
363
275000
孙法理
无
一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年1月9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父亲大卫·坡原是学法律的,却做了演员,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坡也是演员。父亲1810年以后就没有了音信,母亲1811年又因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时坡才两岁。富裕的烟草商人约翰·爱伦夫妇没有孩子,喜欢上了他,便收养下来。孩子原名埃德加·坡,被收养后,全名是埃德加·爱伦·坡。按照西方习惯,简化时仍然该叫埃德加·坡,但是因为继父这层关系,简称习惯叫爱伦·坡。1815年,爱伦夫妇带孩子去了英国。1817年爱伦·坡在斯托克牛英顿的一个学校入学,学了五年拉丁文、法文等课程。那个宏大而散漫的学校和馨香而多树的小镇后来进入了他的小说《威廉·威尔逊》。小镇也充满英国历史的遗迹。伊丽莎白女王、她的母亲安·布琳、她的宠臣爱塞克斯,还有著名的作家笛福,都曾在那里居住。1822年,爱伦夫妇带了孩子离开英国,回到美国的里士满。1826年,爱伦·坡进了弗吉尼亚大学,却因耽溺于赌博惹得继父非常生气。继父为他付还了赌债,却不愿再供他读书。他因为不愿意搞烟草生意,跟继父就未来事业的发展大吵了一架,离开了弗吉尼亚。1827年坡在波士顿自费隐名出版了诗集《
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的特点是“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可怕发展成恐怖,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上升到怪异和神秘。”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在创作中总是精雕细琢、巧妙构建,在诸如变态心理、死亡的恐怖、起死回生等题材中,运用这种手段来烘托气氛,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惊险、强烈的恐怖效果。它们是关注的是最高境界的死亡之美、快乐与残酷的联想。故事的主人公都笼罩在死神的阴影下,身染重症,劫数难逃。
作者:(美国)埃德加•爱伦·坡 译者:孙法理
科幻小说
瓶中手稿
卷入美尔斯卓姆大海漩
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未来书简
福德玛先生病例
天蛾
推理小说
金甲虫
莫格路凶杀案
玛丽?罗杰疑案
失窃的信
哥特小说
丽该雅
埃榭大院的崩塌
贝伦妮丝
密约
陷阱和钟摆刀
阿芒蒂雅朵酒
跳蛙
红死病假面舞会
心理小说
逆反心魔
露馅的心跳
黑猫
威廉·威尔逊
人群中人
钟楼怪客
关于我的祖国与家庭,我能说的不多。不公平的待遇与多年的暌违迫使我远离了祖国,也生疏了家庭。我继承来的遗产给了我难得的教育,而我这爱好思索的心灵又使我对早年的辛勤研究所积累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对德国道德学家的研究使我尤其愉快一不是因为他们那疯狂的雄辩赢得了我无知的崇拜,而是因为我执拗的习惯让我轻而易举地看出了他们的破绽。我常常受到指责,说是我缺少才情,枯燥乏味,也被扣过缺乏想象力的帽子,我的庇罗式的怀疑情绪也使我经常名声不佳。事实上我担心的是:我的心灵对物理哲学的热爱使它带上了这个时代极常见的一种错误的色彩——我指的是对一切问题都用物理哲学原理检验的毛病,即使问题与它毫不相干。总而言之,我比谁都难于被迷信的幻觉所欺骗,也绝不会轻易偏离严格的真理领域。对这一点我觉得必须事先申明,否则我将要讲述的难以令人相信的故事就有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梦呓,出自平庸的想象,而非心智的切身体验,但在现实经历里,幻觉的梦呓是既无地位也无意义的。我在国外旅行多年之后,于18××年离开了人口众多的富裕的爪哇岛的巴达维亚港,向巽他群岛出航。我的身份是旅客——引诱我的除了魔鬼般地纠缠我、令我难于安静的神经质的躁动之外,没有其他原因。我们的船很美,载重约四百吨,是在孟买用马拉巴柚木建造的,有铜箍加固。运载的是拉卡岱伏群岛出产的棉花和油料,还有椰子壳纤维、椰子糖、水牛奶油、椰子和几箱鸦片。货载堆得马虎,因此船行不大平稳。我们趁了点微风就出发了,好多日子都在爪哇以东的沿岸下碇,除了偶然遇见几艘我们要去的群岛的东方式的双桅船之外,再没有可以排遣旅途单调的东西了。有一天黄昏,我倚着船尾的栏杆眺望,在西北方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独立云团。它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颜色之外,还因为它是我们离开巴达维亚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云团。我专心地注视着它,直到太阳西沉。那时云团突然向东西两边延伸开来,化作了一条狭窄的云气带,铺在海平面上,像一道长长的浅滩。月亮的暗红形象和大海的反常特点立即引起了我的警觉。海水正在飞速地变化,清澈得似乎反常。海底虽然清晰可见,测量下来已有十五嚼深。这时天气已热得叫人难以忍耐,而且空气中带着种种气味,盘旋着,升腾着,仿佛烧红的烙铁。夜色渐浓,且没了一丝风,一种难以设想的更可怕的宁静忽然降临。舵楼甲板上的烛火没有丝毫摇曳;用两个指头将头发弄得下垂,也不见飘动。不过,船长仍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何况我们正往海岸漂去。他命令收帆、抛锚,而且没有安排人守望。船员大多是马来人,索性故意在甲板上拉长身子躺下了。我下到了舱里,对于那不祥并非没有充分的预感。实际上一切的迹象都提醒我,必须警惕热带风暴的来临。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船长,他却满不在乎,不屑于答话就走掉了。但是我的不安仍使我难以入睡。夜半时分我又往甲板上走去——我的脚刚踏到升降梯口便被一种水车疾转般的强烈轰响吓了一跳。我还弄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已感到船体有一阵震动,直达船心,转瞬之间铺天盖地的浪花已经从船头打来,把我们掀向横梁末尾,冲来冲去,而且从头到尾淹没了甲板。那猛烈的打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艘船。帆桅断了,落进了海里。这样,船身虽全部浸到水里,却在片刻之后又从海里吃力地冒了出来,在风暴的无穷压力之下摇晃着摆正了身子。
《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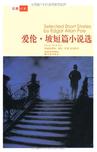
无
经常在别家的推理小说书中见提到爱伦坡,特地买了爱伦坡的书,主要是来看他的推理小说的,虽然他的推理小说只有4,5篇,但是篇篇经典,不愧是推理小说先驱者,永不过时的爱伦坡,书也很物美价廉,良好出版社啊
书一点都没有压皱,棒!!
译林出版,爱伦坡的作品,还是硬皮,好。
译林出版社的译本向来质量很高,纸质不错,有种书卷气息,草木的感觉令人陶醉。爱伦坡的文章也很好看,晚上看冷汗一身一身的。
刚收到书,还没看过,质量很好
描写诡异,情节引人,语言精练,很独特的一本书。
书封面有点旧,而且明显被压过。不过不影响阅读。
书页都掉了,但书不错
或许是期望过大,这书一般
故事没怎么看完纸质不太好可能没看进去吧有点怪异的小说
看着眼睛酸痛,我不喜欢
之前看了评论说这版翻得不好,觉得能出版的东东应该不会太差,没想到翻成这样,粉失望,OVER
对这个译本,我觉得合格。怎么说呢?第一,从纯语言的角度讲,语句这些还是可以,有可读性;第二,编辑太不负责任了,错字、错误的标点、少些的标点等基本上还是能够发现不少。所以,我也只能给个合格的评价。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翻译的不错的,文章也比较吸引人,尤其是哥特小说部分
对于爱伦·坡,我很感兴趣,也很是喜欢,但他的小说的一本相对来说太少了,选择也少。非常感谢楼上的建议。
作者:杜予景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丽姬娅》发表于1838年,被誉为爱伦•坡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的妻子丽姬娅离奇死亡却又死而复生的故事。小说因为诡秘的背景和怪诞的情节成为典型的哥特式恐怖小说,也是完美诠释爱伦•坡“效果论”及其美学思想的作品,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但正如哈罗德•布卢姆所言,“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让人感到陌生的熟悉” ,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经典作品永远等待着我们做出全新的阐释。重读《丽姬娅》,我们发现那看似神秘恐怖的小说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关于能指和所指、在场和缺席、东方和西方、死亡和重生、梦幻和现实、婚姻和现实的最严肃的思考。
丽姬娅——一个东方幽灵的隐喻
小说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讲述了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构很简单:与妻子的相识,妻子的死亡,再婚,前妻的复活。叙述者的叙述里没有涉及和丽姬娅生活的任何痕迹,他用大量的笔墨在构造着丽姬娅的特征。
丽姬娅这个名字(Ligeia)本身就充满了隐喻。Ligeia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海妖中的一位,这个简单的名字隐含多种指涉:1. 妖媚的女子;2. 遥远的异域女子;3. 幽灵的特质。活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所有亲见者,却已死亡。
鬼怪,幽灵,死而复生是爱伦•坡小说里常见的题材,《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玛德琳小姐,《艾蕾奥瑙拉》中的艾蕾奥瑙拉小姐都有着死而复生的鬼怪特征,而在本部小说中,作者一直重复着丽姬娅的幽灵特征。
首先,小说一开始就暗示着这个人物存在的可疑性。“说真的,当初我跟丽姬娅小姐怎样认识,几时相逢,甚至究竟在何处邂逅,全想不起来了。那是多年前的事,何况我又饱经沧桑,记性坏了……”“眼下,手里写着这篇文章,心头陡然想起,她姓什么,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神秘的女子或许本来就如《聊斋志异》书斋里、古庙中穷书生对女子的一种想象,来去无踪,叙述者自己也在强调丽姬娅的虚幻性:“再不,难道还是我自己想入非非——是热恋的神龛前一种风流绝伦的供奉?”)她不但来历神秘,还来去无踪:“要我画出她那雍容华贵的风度,要我描出她那无限轻盈,飘飘欲仙的脚步,真是妄想。她来去无踪,像幽灵……”
其次,她不但是一个幽灵,她的一切特征完全符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这个有着东方海妖名字的女子不但有着纯东方的美丽外表,还有着代表东方的古老历史、学识、财富。文中对她外貌的描述集中在她东方特色的黑色眼睛和乌黑的长发:“眸子黑得熠亮,偌大的漆黑睫毛盖过眼睛。眉毛长得不太整齐,也是这样黑……”“再端详熠亮的、浓密的蓬松乌丝,活活道出荷马式形容词‘如风信子’的意义!”“如风信子”出自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美少年海辛托斯,两人掷铁饼时,阿波罗不幸击死海辛托斯,无法救活,其血化成风信子,花瓣上印有AIAI字样,荷马将此字代表黑色。风信子的花期过后,若要再开花,需要剪掉之前奄奄一息的花朵,所以风信子也代表着重生的爱。这里短短几个字,却包含丰富内涵,这是一个有关爱情,死亡,重生的故事,预言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虚化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将她的出生背景也历史化了:“她的家世倒确实听她亲口谈过。不用说,是个历史悠久的世家……”丽姬娅的学问更是无人能及。“她精通古典语言,就我对欧洲现代方言的知识来说,根本没见她被难倒过。说真的,碰到任何深受崇拜的课题——就因为那是学院夸耀的学问中最深奥的一种——又何尝发现丽姬娅给难倒过?……”她不但精通各种学问,还能指导“我”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总之,丽姬娅是知识,特别是古典学的化身。除了智慧,她还神奇地拥有财富,小说中叙述者只用一句话点明了玄机:“我倒不缺世人所谓的财富,丽姬娅给我带来的财富,远比凡人通常注定享有的还多,要多得多呢。”这个财富为他后来买下寺院,宫殿式的华丽铺张,娶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整篇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故意的不可靠叙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符号化的东方,一个带着浓厚东方色彩的神秘幽灵,带着一切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对东方的想象和表述:神秘、古老、智慧和财富,这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对近东的投资,“埃及热”出现,一些介绍埃及的文章在当时有影响的杂志《北美评论》上发表,1823年,波士顿运来了两口埃及石棺,1826年,两具木乃伊在纽约工艺美术馆展出。爱伦•坡也深受影响,1837年他在《纽约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的埃及”的评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1838年9月发表的《丽姬娅》中出现阿拉伯女子也不足为奇了。爱伦•坡毫不掩饰对近东的偏爱,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包含着阿拉伯元素,最直白的是1845年发表的《与一具木乃伊的对话》,以一个复活的木乃伊的口吻,褒扬了埃及文明。在《丽姬娅》中,“我”和她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欲的关系,更是一种母子关系。“但当初倒完全晓得她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支配我,竟像孩子一样安心,听凭她指导我研究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失去了丽姬娅,我只不过是个孩子,暗中摸索罢了。”在西方文学中,东方常被表述为男性回归的母性,1824年,同时代的爱默森把亚洲理想化为“人类孩童的游戏场,一个遥远的追忆地”。惠特曼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西眺”中把印度看成“母亲的房屋”,诗人自己是新世界“孩童”,去找寻“未被发现的东西”,因此,东方既是“母亲”也是“未知”,根据萨义德的论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那些神秘的东方神话,被基尔南恰当地称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在《丽姬娅》中,丽姬娅被表述成文本化的东方符号:神秘、美丽、智慧、富有。它表述着叙述者对于东方,对于女性占有的双重权力话语。小说中丽姬娅这个幽灵的形象始终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是一种指涉,她悬置在梦幻与现实、地狱与人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成为殖民征服和女性征服的符号。
罗维娜——缺席的“在场”
罗维娜在小说中笔墨不多,却明确地建构了她的身份:南方贵族小姐。她金发碧眼,出身高贵,和丽姬娅相比,她是美国19世纪中期南方淑女的代表,她拜金:她嫁给“我”就是因为新娘家“贪图金钱”,她忍让:“妻子就怕我这种火爆的脾气”;她矜持,不知闺房之乐:“她躲开我,简直不爱我”,和丽姬娅相比,罗维娜在文中面目模糊,“我”只知道她是金发碧眼的纯正白人血统和高贵的出身,他们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但比起小说前半部描画的我和丽姬娅的生活,前者充满了想象和崇拜,没有世俗婚姻的实质,后者虽然是夫妇却形同路人,却有“我”意味深长描写我们真实婚姻的词句:“新娘”、“新房”、“在新房里无忧无虑度过的第一个月”,这是一个真实的、异化的婚姻关系,“我”和罗维娜小姐的婚姻才存在于现实世界。新娘是名门淑女,当时因为贵族家境的没落,看中“我”的财富嫁给“我”,现实的婚姻缺乏激情,使我无时无刻不对东方的丽姬娅充满期盼,“我”故意把新房布置得充满了阿拉伯情调,等待着丽姬娅的来临。在小说《丽姬娅》中,我们看到的“在场”是现实中的妻子“罗维娜”,她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婚姻中,但是她又“不在场”于我的爱情生活中,“看出她躲开我,简直不爱我,可我心里反倒高兴”,“在吞了鸦片的乱梦中,我会呼唤她的名字,或者在万籁俱寂的晚上,或者白天,在隐蔽的幽谷山坳里,仿佛只要我心痒难抓地,热情如焚地诚意怀念亡妻……”这个本应该在场的妻子罗维娜却是“缺席”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发现了梦幻和现实,“在场”和“不在场”的辩证关系:丽姬娅生活在我的梦幻中,本应该是“不在场”的地位,却一直是“在场”于整个故事中,看似“在场”的妻子罗维娜却始终“不在场”,德里达的差异原则,一个符号要发挥功能,指称事物,携带意义和传递意义,只能依赖于在它之前或之后的“不在场”符号,在整个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意义是由丽姬娅来表示的。小说的最后,在半梦半醒之间,丽姬娅和罗维娜交替出现,丽姬娅的借尸还魂具有极强的隐喻含义:从拉康的心理学视角出发,罗维娜是能指,是“在场”,是意识,丽姬娅是所指,是无意识;无意识的欲望,既是永远得不到满足,又是永远不可摧毁的,无意识的能量就从一个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企图指向所指,但永远无法达到所指。拉康用一个结构模式来表示:S能指/所指,斜杠代表了能指对所指的压抑。拉康运用语言学的模式来对无意识进行分析,提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的命题。并用这个结构模式分析了爱伦•坡的一个短篇小说《被窃的信》,这里我们也可用来分析小说《丽姬娅》中“我”的心理模式,主体的心理分裂成意识和无意识,分别由罗维娜和丽姬娅来表示,丽姬娅从头至尾是“不在场”,是他一生永远的缺失,是被压抑的无意识部分,而罗维娜是“在场”,是被允许进入社会秩序的意识,小说结尾只有在半梦半醒之间,进入“我”意识的深处,等待着丽姬娅幽灵的惊鸿一现,稍纵即逝的幽灵显现就如同我们的无意识一样深藏在大脑的深处,偶尔灵光一现。
无意识的男性欲望书写
整篇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哥特式的爱情和死亡的故事,但仔细阅读我们能发现藏在故事背后“我”的隐秘欲望,拉康的欲望学说区分了需要(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三者的差别。拉康认为人的需要是生理性的,它的对象是具体的,“它总是以具体的缺失对象为欲求指向。”对于要求,拉康认为,它是由需要异化而来,“要求本身涉及到的是它所要满足的以外的别的事。它要求的是一个显现和一个远隐。”因此,要求不仅是为了从他者那里得到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具体客体,更重要的是从他者那里得到爱。而拉康认为,“欲望是缺失的转喻,主体无论欲望什么,得到的只能是满足需要的具体对象,他只能不断地‘要’,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可是每一个能指却都转喻式地与本体论上的失却相关。因此,欲望永远无法得到真正满足。”由于欲望是缺失的欲望,是产生于能指与能指之间缝隙中的“无”,因此欲望是一个永不能满足的深渊。而能指链之间的裂缝就是缺失,缺失是能指之无,是不在场的在场。丽姬娅代表着妖媚而有致命吸引力的危险女性,罗维娜是天使型家庭主妇。如果说我对罗维娜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和要求,两个女子以“在场”和“缺席”的交替出现则揭示了我无法言说也永远无法满足的无意识欲望。从文本表层看,我对于东方女人所代表的美丽、神秘、财富、学识的幻想体现了我的生物的需要和要求,是一种可以从他者那里满足的客体。文中“我”反复以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口吻所进行的对于新房细致入微的描述更体现了叙事者不为人知的欲望,新房尖顶的塔楼成五角形,拱形的天花板,精工描绘的回纹图案,再加上阿拉伯的摆设,无不呈现了伊斯兰教的闺阁建筑。“我”把新房建立在伊斯兰教的闺阁里有何用意呢?伊斯兰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伊斯兰教闺阁式新房”这样的空间叙事又以“在场”的形式表述了“不在场”的欲望:男人同时对女巫和天使的向往。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在文本中既被美化成美丽温柔的天使,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到歌德的葛雷特,又被丑化为女巫形象,从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美杜莎到《圣经》中的夏娃,这种既把女性看成是美丽温柔的天使又把她们看成恶魔的事实反映了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双重角色,也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矛盾态度,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让他们产生厌恶。这种意识一直会被以父亲名字所代表的社会法律秩序所压抑,只以无意识的欲望而存在,通过空间隐喻表现出来。当主体以语言说出自己的需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能指的歪曲或矫正。这种对两类女人的需求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男人最隐秘的欲望。反映了男人对女人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在小说中整个叙事主体是男性“我”,两位女性一直处于失声状态,整篇小说代表着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主导话语,他们对于东方,对于女性的欲望表述。而女性在文中却只有一次发出了声音,那就是丽姬娅弥留之际的诗歌:“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服死神。”这为罗维娜的复活埋下了伏笔。尽管爱伦•坡是基督徒,但他对个体意志的力量充满了兴趣,在很多作品中写到了死而复生。美女与死神抗争是爱伦•坡感兴趣的主题之一,这和他童年丧母,成年又失去心爱的妻子弗吉尼亚有关,亲人的死而复生又是他文本下另一个隐秘的欲望。
结 语
爱伦•坡生前并没有得到文学界足够的重视,甚至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应了他的那句话,“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读者……”如今爱伦•坡早已跻身一流作家之列,其诗歌、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也成为美国经典文学的一部分,人们开始在历史和文化的变动中寻找隐藏的历史话语和权力话语。《丽姬娅》在其表面的爱情和死亡文本背后所隐藏着的有关殖民、男性和永生等权力话语,为研究他的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摘自《山东文学》 作者:杜磊 李哲 张晓红
爱伦•坡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他在诗歌创作上注重描写灵魂深处的状态,并富于音乐感和忧郁美;提出诗歌要写“美” 的唯美主义学派原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拥有自己系统的创作文学理论。他最杰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上,小说的主题是恐怖和死亡,通过 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人格中被忽略的病态或阴暗的方面达到预设的恐怖效果,这使他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的创始人。
萧伯纳(Bernard Shaw)曾声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但是,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命运更坎坷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要研究美国文学,对爱伦•坡的作品不可不了解,而要了解他的作品,首先应该了解他的一生。
爱伦•坡(1809-1849)自幼父母双亡,被一富商收养,早早饱受人间冷暖世道艰辛。曾受过贵族化教育,后来化名参加西点军校,因不堪忍受严格的校规的约束,故意触犯校规,方把他开除。爱伦•坡生性乖戾,这大概是由于天性洒脱同养父的严厉管教相抵触的结果。但他酷爱读书,富于想象,对诗歌有特殊的兴趣。18岁发表了第一部诗集。爱伦•坡生活坎坷,特别是1847年爱妻病故,从此一撅不振,嗜酒成性,精神失常。
爱伦•坡的一生穷愁潦倒,备尝辛劳忧患,自幼生性乖戾,故常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恨,心情郁郁寡欢。无论在他生前也罢,死后也罢,在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爱默生(Emerson)称他为“打油诗人”。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他的文字不值一读。然而在大洋彼岸爱伦•坡一直享有盛誉,英国作家斯温伯娜(swinburne)和肖伯纳(Bernard Shaw)等人对他的天才成就都称赞不已。法国19世纪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和马拉梅(Mallarme)等人将他奉为至圣。到20世纪才得到美国本土的承认,评论界对爱伦•坡作出高度评价,认为爱伦•坡在西方文学史中占有不朽的地位。
在他短短一生中写下的不少作品里,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小说都反映了,美的幻灭,希望的渺茫,忧郁的怪异。在他的小说中,着意描写了人的内心世界,探讨为世人所忽略的精神状态,极力表现了人的思想病态。致力于描绘现实和幻蒙两者交界地带的状貌,从而扩展了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正是在小说这个领域中爆发出了“他的天才”的荒诞性。为了达到预设的效果,爱伦•坡在创作中总是精心雕琢巧妙构思,在诸如变态心理,死亡的恐怖,灵魂的轮回,起死回生等病态的题材中,运用各种手段烘托气氛,制造惊险恐怖的强烈效果。
特别是爱伦•坡后期的小说情节愈加阴森恐怖,感情炽烈可怕,让人精神极度紧张,而且有些失常,同时也能窥测到人的变态心理和犯罪意识的深处,这使他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的创始人。例如:《厄舍尔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为了达到预设的效果,作者开首就作了铺陈:阴郁破败的古宅,阴森的水池,凄冷的墙壁,凋落的树干等字句。还有古屋内的陈设更是昏暗压抑,漆黑的地板,破朽的家具,一切都无不透露着阴森诡异之气。小说中的孪生兄妹一个肉体在腐烂,一个精神在解体,都患有不可名状的不治之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病态心理。哥哥把未死的妹妹提前埋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妹妹破棺而出死在哥哥怀里,古屋突然倒塌,至此恐怖气氛达到高潮故事戛然而止。故事字句和段落环环相扣,在古屋和人的相互衬托中,使故事叙述者和读者一起意识到古屋和其主人不可避免的毁灭性厄运。在《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中,爱伦•坡逼真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病态犯罪心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人物病态心理及由此产生的虚幻感觉,达到预期的恐怖效果,使人读了不寒而栗。另一篇《阿芒提拉多的酒桶》(The Cask of Amontillado)也是坡惯于描写的恐怖和死亡。故事发生在阴森的酒窖,仅有的两个人物也存在着人格上的缺陷。还有《椭圆形画像》(The Oval Portrait)、《红色死亡的化装舞会》(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莉吉娅》(Ligeia)等一些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小说,尤其是描写人格中被忽略的病态或阴暗方面和对人心理的细腻描写,正是如此美国文学批评界才认为这是他创作天才的最高表现。
爱伦•坡主张,在一首诗,或着一篇故事中,每一个字,每句话,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有助于实现整个作品的预期效果。因此,他的小说语言凝练,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冗长的,没有一个细节是可有可无的。如在《阿芒提拉多的酒桶》(The Cask of Amontillado)这部小说中,蒙特利瑟脱口而出的拉丁语,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反映了他受教育的程度,并自然地把他的文化修养同他残酷的报复形成强烈的对比。
爱伦•坡在西方还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侦探小说情节生动,推理严密。代表作《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窃信案》(The Purloined Letter),和《金甲虫》(The Gold Bug)都被奉为这类小说的先河,对后世起了很大影响。
爱伦•坡的诗歌创作尽管缺乏时代性,而其主题和审美方式却有超前性和独特性,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同时也对法国的象征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诗歌中追求的是一种遥远的,忧郁的和陌生的美,在梦幻和怪诞的想象世界中寻求心灵的宁静。他的成名作《乌鸦》(The Raven)体现了他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和伤感主题的偏爱。《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富有音乐感和忧郁美:“每当明月初上,那清晖总为我带来梦境/梦里再见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每当星临长空,我总感到那明亮的眼睛/它是来自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因此,每夜潮汐潮落,我总躺在她身边/那时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那濒海的坟墓旁/在那海浪喧嚣的墓地上”。这首诗诠释了作者的创作原则——诗歌的基调应是“忧郁”,人最“忧郁”的事莫过于死,最富于诗意的死莫甚于心爱的人离逝,这一刻最接近美。
除了创作,爱伦•坡在文学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爱伦•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他关于小说和诗歌的创作理论如《写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1846)、《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1850)、《评论霍桑的〈古老的故事〉》(Review of Twice-Told Tales)等都显示了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被视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称赞,爱伦•坡的伟大在与他以开拓和独创精神创作美国文学。他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人物心理细腻逼真的病态描写在文学史上是无人可比的。因此,他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不可忽略的。
摘自《文汇报》 作者:止 庵
一部推理小说,第一、要有罪犯,隐匿甚深;第二、必须是谋杀案,或许不止死一个人;第三、案件终归破获,但很不容易,破案的人起初是侦探,后来是警察;第四、侦探要有个助手,譬如华生之于福尔摩斯,黑斯廷斯之于波洛,多少帮点忙,此人常身兼小说的叙述者,当由侦探破案变成警察破案时,要有更多的人介入;第五、还得有些看似相关末了证明与案件并无牵连的人;第六、案件可以发生在城市,也可以发生在农村,也可以不要这种大的背景,譬如“密室推理小说”,就限制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
美国作家爱伦•坡写了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塑造了第一个侦探形象杜宾。从那以后,一代代推理小说家就在上面六项之内,变着法儿给自己设置障碍,特别是这两方面:第一、不可能犯罪;第二、不可能侦破。推理小说家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作品也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好看。
严格说,无论杜宾,还是福尔摩斯、波洛,原本都是局外人,大可不管破案的事。但是为什么要管呢,除了正义感之外,他们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本事。在《莫格街谋杀案》中,杜宾说:“近来观察于我已成了一种必然。”这是侦探的第一样本事。提起福尔摩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总是那个叼着烟斗、拿着放大镜的形象。说来烟斗有没有两可,放大镜却很重要,因为作为侦探必须勘察现场。他会发现许多别人没有留意的蛛丝马迹。有些推理小说家就在这儿给自己设置障碍,以至有“盲侦探”、“坐轮椅的侦探”之类,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归得完成勘察工作。在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莱姆系列”中,负责破案的刑事鉴定专家莱姆全身瘫痪,只有一个手指能动,现场勘查、搜集证物有赖于女助手阿米莉亚•萨克斯,两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莫格街谋杀案》还提到:“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觉察并赞佩杜宾所独具的一种分析能力。”这是侦探的另一样本事。他们要对所发现的线索加以分析,得出结论,从而破获案件,找出凶手。分析所依赖的是逻辑,而观察则是实证的方法。在柯南道尔的《铜山毛榉案》中,福尔摩斯说:“即使我要求公正地对待我的技能,也是因为它不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它是超越我个人之上的。犯罪俯拾皆是,逻辑却难得一见。”在迪弗笔下,萨克斯搜集到的材料,要靠莱姆分析。侦探需要眼睛,还需要脑子,前者可以有人帮忙,后者必须依靠自己。从《莫格街谋杀案》到最新的推理小说,一概离不开这两样东西。
讲到推理小说,一直有种疑问,就是这类作品有什么意义。三十年前,《译林》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大受读者欢迎,惹来某位学者告状:“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再往前推五十年,程小青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侦探小说的质料,侧重于科学化的,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又可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谈侦探小说》)不妨直截了当地讲,推理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已经出了一百多种的“午夜文库”有句广告语:“阅读之前,没有真相。”其实好的推理小说,不读到最后一页,真相不会大白。阅读推理小说的乐趣,就从翻开第一页开始,到读完这本书为止。
进一步讲,则如博尔赫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博尔赫斯口述》)推理小说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传达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理念: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体现理性与正义的作为,总是有成效和有意义的,善最终能够战胜恶。直到如今,大概仍有不少读者期待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