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2008-4
中共党史出版社
沈国凡 编,王文正
319
无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口述者王文正,参加了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主犯的审判,之后又作为审判上海“四人帮”余党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是唯一同时参加了这两次重大审判的人。这位八旬老人,凭借其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和清晰的思维,回述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前后后的真实历史。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是第一本专题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罪行及审判过程的著作,既有大量一手历史资料,又以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来,史料性与可读性兼具,同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成为承载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好文本。
.
引子第一章 武装叛乱一触即发1.我为什么要来回忆已经快被遗忘的历史2.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3.公安部“内线”告密4.密谋武装叛乱第二章 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1.海军政委临危受命2.海军专机密降上海.第一部 背景档案第三章 拉开“文革”序幕1.江青南下密谋2.选中姚文元3.朱永嘉的加入4.江青为姚文元打气5.建立“保密车间”6.为何在《文汇报》发表7.拉开“文革”序幕第四章 上海“文革"第一事件1.针锋相对,2.吵闹闹的成立大会3.冲击上海火车站4.安亭车站一片混乱5.市委来人传达“陈伯达来电”6.天上飞来张春桥7.安亭退“兵”8.阳奉阴违的“救世主”9.签字还是不签字10.毛泽东将票投给中央文革第五章 《解放日报》事件1.拒绝报道2.《红卫战报》出笼3.九天九夜的围攻4.违心地妥协了第六章 “后院起火”事件1.市长办公室闯进造反的国家干部2.“后院起火”3.秀才造反第七章 “一月风暴”1.陈丕显“出山”。2.不平静的黎明3.一场闹剧4.“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场风波第八章 率先刮起武斗风1.张春桥电话指令2.密室策划3.剿灭“赤卫队”4.在处理“赤卫队”的案件中,我首次接触王洪文第九章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1.密谋针对“联司”的打击行动2.以定行动计划3.G号计划开始行动4.准备与“联司”的决战5.血腥镇压第十章 组建“第二武装"1.全国第一支工人武装2.罪恶的阴谋第十一章 法律和道德的沦陷1.所谓“侦控林彪事件”2.“兵公法领导小组”出笼3.哭泣的法律4.当道德败坏的人掌握了专政工具第二部 法庭内外第十二章 从特别法庭审判员到上海法庭审判长1.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2.江华曾两次找我长谈3.特别法庭庭长的希望第十三章 纷纭复杂的上海滩1.跌宕交错的局势2.为什么不审判首犯马天水第十四章 站在时代的分水岭1.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专程来沪2.我提出不同意见3.有关设置“特别法庭”第十五章 初步拟定的罪行清单1.再上北京,请示最高人民法院2.以事件为依据列出的罪行3.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4.如何认识罪与错5.这些都不予定罪第十六章 再起风波1.各持己见2.“心急可喝不得热茶”3.曾汉周的答复第十七章 法庭审判1.提起公诉2.法庭对质3.王秀珍服法认罪4.仍然有顽抗到底的人第十八章 审理“冯新华事件”1.率先刮起“批邓”风2.谁是冯新华3.艰难的法庭审判第十九章 有关判决书内容的争论1.市委常委会上出现僵局2.我再次发表不同意见3. 中央没有同意市委的意见尾声 最后的判决附录1附录2
第一章 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1.我为什么要来回忆已经快被遗忘的历史 我这个八旬老人,为什么要来回忆这些已经陕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呢? 原因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写“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书籍与文章中,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你看,这本书中说:“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可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女人应该叫汪湘君,而不是汪碧君,在整个法庭审判的“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女人中,没有那个叫汪碧君的女人。汪湘君是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1日,以参加策划武装叛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骨干在当时的职务,有的书中写道:“民兵总指挥施尚英”,而当时施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不称总指挥,通常只说他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此书的下册中说:“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这也不对,他的实际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群众称他是“上海五虎将之一”。 该书中还写道:“l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h…” 我是特别法庭审判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据我所知,在所有参加的审判员中,根本就没有这位“笔者”。这位“笔者”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是“参加旁听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而绝不是“参加了”对这件案件的审判,两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否则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就会多出这么一个人来,后人来查找相关资料时就会被搞得莫明其妙。 更有在时间上,此书作者也弄错了,应该是“l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至11时”。这天更没有把姚文元押上法庭,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已认定姚文元构不成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罪,所以决定此事不对姚文元进行法庭调查。 除了时间和史实的错误之外,一些文章中将法律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有两处称黄晨为“原告”。 在特别法庭开庭调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查抄上海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时,法庭通知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只能是一个“证人”,怎么她成了公诉“四人帮”的“原告”了呢?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家公诉机关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公诉的,受害人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原告”。如此严肃的史实,怎么能搞混呢? 作为亲历了整个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审判和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庭审判员,我感到很难过。这些作者,大都没有亲自参加过北京、上海这两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旁听了一两场,便将这种旁听写成“参加”,更有的是查找了一些有误的资料,便匆匆成文成书,造成多处失实,错解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贻误 读者和后人。我作为共和国这段特殊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参加者,对此十分着急。 我考虑到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当事人回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的书出版,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件历史事件都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太特殊了,太突出了,没有对这伙人的最后审判,对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算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就不能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就我所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一本当年亲自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并同时亲自参加审判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审判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全面记录这段决定我们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图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全国所有的法官中,参加过这两场(而不是一场)决定共和国命运大审判的审判员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年事已高,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手中许多当时的文字资料还在,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l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l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l959年2月至l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止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l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 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 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上海的反革命集团尤为猖獗。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打着革命旗号行动乱之实的罪犯们,终于在法庭上得到了应用审判,审判过程中,表现了 家回到了正常轨道后,法律尊严的恢复以及审判程序的公正。本书根据亲历这段历呼、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的王文正先生口述采写,内容生动而翔实,真实记述了那一段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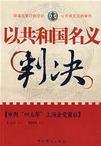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