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
巴尔扎克
小丽
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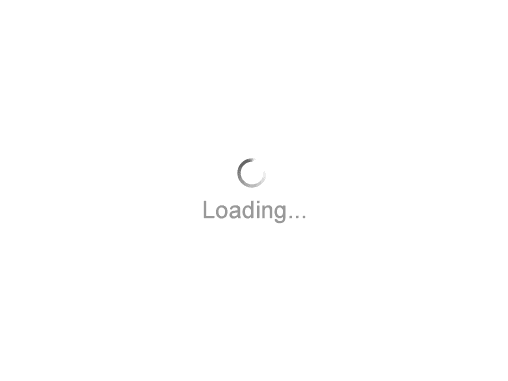
无
黄舒骏在《纪念1995》里唱过“全台湾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
是的,正如R&B在乐坛的走红一样,几乎全体文艺青年们提起法国文学都是杜拉斯、萨冈、萨特、加缪,诸如此类。
什么浪漫破碎的语言,什么独辟蹊径的词汇,这个主义,那样解构,诸如此类。
但是,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法国小说却不是这样的,它琐碎、写实、絮絮叨叨、从不颠覆主谓宾定补状,不管写市井小民还是写王公贵族,不管是家长里短还是传奇冒险,话都是好好说的,字都是好好码的。
雨果、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大小仲马、左拉……诸如此类。
雨果是跌宕起伏的申奥大片、小仲马是文艺细腻版《知音》、大仲马是包袱抖得极佳的美剧、而巴尔扎克,则是TVB——
不管之前你看了多少遍,只有电视台再重放,也能继续看下去。
不管它放到哪里,马上捡起来,也能继续看下去。
睡前随便看一点,看困了就扔掉,第二天继续,没有今天非看完不可的迫切。
老巴之于我,就像是一个老熟人。
小时候考试成绩好一点,老娘才会给我钱买书,那时候家附近有一家特别小的书店,店主是一个老头,儿子在美国,自己无聊了就出来开店,卖佛香和旧版书。他店里有安徽文艺出版社老版本的傅雷译巴尔扎克,保持着六年前的书价,大多不超过十块钱。
初中的时候,老娘给二十块,在别处只能买一本,在这里买老巴的书就能买两本,所以贪图便宜的我就把除了《幻灭》之外的老巴基本都收全了。
看得第一本是《邦斯舅舅》,最近一本则是事隔多年之后的《幻灭》,基本作为睡前读物,每天看一点,翻来覆去的看,别人都嫌老巴啰嗦,他写法国内地一个普通老妈子,也会从这个城市的历史、地理、风俗写起,然后接着描述这个老妈子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喜欢吃什么东西养什么猫有什么亲戚说什么闲话年轻时爱过什么人有过什么风流,层层叠叠的前程往事细枝末节。
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烦,相反,我很喜欢看他唠叨巴黎街道是怎样内地的溪谷是怎样,交际花怎么装饰自己的金窝银窟,名利场的一场派对菜肴何等精美……
老巴有本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叫做《比哀兰德》,讲的是来自法国内地一个清纯如天使的小女孩是如何被万恶的资本家亲戚折磨至死,里面写到小女孩的资本家亲戚们从巴黎告老还家,在内地修起自己的宅子,由于品味恶俗得出奇,被当地的贵族太太含讽带刺一通描述,整整挖苦了一章。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变态的癖好,就是反复看这一章,看那些对于暴发户品味的细致描述,看得津津有味。
所以,我对于老巴一直缺乏“他写的是名著”这样的自觉,他在我印象里太似隔壁叔伯大妈,门房、裁缝、画家、兵痞、穷学生、阔太太、交际花、商人、女佣……各种八卦顺口就来,都要先从祖宗十八代上讲起,详细备至。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跟别人八卦起老巴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叫做《奥诺丽娜》,甚至比那本叫做《比哀兰德》的更加不出名,却是老巴小说里颇奇特的一部。
其实老巴笔下的感情大多妄执而偏激,比如父亲对女儿不计代价的爱(《高老头》),比如母亲对儿子盲目的爱(《搅水女人》),比如收藏者对于古董深入骨髓的爱(《邦斯舅舅》),比如风流鬼对于交际花吸毒上瘾般的爱(《贝姨》),比如吝啬鬼对于金钱海枯石烂的爱(《欧也妮葛朗台》)……
但是这个世界很有趣,你写一个来自东方的高帅富和欧洲少女在越南的露水情缘,会有很多人被感动得死去活来把你写的话抄在小本子上奉为圣经;你扯什么吸血鬼家族的万人迷对平凡女高中生一见钟情,会在全球赚上N亿票房;再艺术人文一点,你写两个帅哥在风景如画的山上搞一搞不自不觉就狗血了一生,拍出的片子能拿奥斯卡。
但是你要写两个丑陋的音乐家大叔怎么相亲相爱(《邦斯舅舅》),你要写容貌平庸的女孩怎么为一个品行低下的男人蹉跎一生(《欧也妮葛朗台》),你要写已经年老力衰的老风流鬼怎么为一个暗娼搞得家破人亡(《贝姨》)……就显得不那么high-level。
情深之状态、程度并无屌丝与毅丝之别,但是罗曼史这种事儿绝对跟参与者的长相身高乃至金钱密切相关。
所以我才说《奥诺丽娜》是老巴书里的一个异数,篇幅不长,人物极少,场景紧凑,主角都算是漂亮人物,探讨的问题更是广大文艺男女青年们所喜闻乐见的——爱情、激情、背叛、婚姻、一往情深、永不妥协、男性的痴情与付出、女性的决绝与自尊。——把那个嚼烂了千万遍的题目“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演绎到了一种境界,天生就是一个舞台剧剧本,每一幕都有G点。
由于我一直把老巴小说当加长版的故事会看,对于这部书也并没有太大感觉。但有一日,我在例行的宅基腐大业中和人八卦起这部小说——
说起书里被妻子抛弃但是又一往情深地公爵,如何每天站在自己为妻子准备的楼下看到灯火熄灭才离开;
说起书里那则故事——“诗人爱上全城最红的舞女,在不知道人家怎么对他的前提下,买了全城最美的一张床”;
说起那位按照天涯眼光“红杏出墙跟小三私奔又被小三遗弃“的妻子,每日在阁楼里模仿自然的花草树木做着手工,说着” 吕克雷斯当年用她的匕首和血替女性的宪章写下了第一个字:自由!“;
说起书里对于那位女主,那位夫人外貌的描写,什么“天国的幽花”,什么“她是那种像猫一样让你可以抱起来温存,一会儿放下再重来的女人”,什么“接近透明的皮肤下看得见纤细的血管,一碰就会像粉红色的水雾那样散开”;
甚至只是说起书里关于热那亚海浪的描述,说就像是“女人的情话,被一句一句地逼出来。:
说着说着,我就有一种搁在家里的黄脸婆,仔细看看竟然是个天仙的感受。
自此,我才真正意识到老巴或许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一个擅于发现庸常生活戏剧性的作家。
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权的动荡、社会的摇摆、贵族的没落、新阶层的升起……全部被老巴打碎、搅拌、汇到日常生活中去,炒成一锅家常的蛋炒饭。
他的笔下既有一些颇有身份的人物,贵族政客商人艺术家,也有一些颇卑微的人物,门房仆人穷亲戚流亡者,老巴细心地写着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如何一步步作出自己的抉择,演绎贪婪真诚卑劣高尚虚荣朴实,让你举得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是的,“顺理成章”这是老巴最大的能力与魅力所在。
老巴故事里的情节很多也颇狗血,但是他能够通过非常细密的前事铺垫和灵魂描写,一步步将人物的心理与行动推到最后的命运上去,让你发自内心觉得“这个人就该这么去想这么去做”,这是终究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邦斯舅舅》里写到邦斯想为自己侄女介绍一个德国的银行家,而老巴花了整整一章来描写这位银行家的老爹怎么起家,他自己又是怎么起家,这样的过程造就了他怎样的性格、习性与脾气,最后当老巴写到这位银行家因为独养女这个原因拒绝了邦斯侄女时,所有人都会自然地把这一页翻过去,想:嗯,的确该是如此。
老巴笔下的人物并非没有歇斯底里情绪爆发的时刻,但是他从来不会把笔下人物的感情一下子推到极端,他往往是让人物情绪慢慢积累,小火慢炖,熬出浓汤。
就像足球场上那种把皮球一步步传进球门的踢法,老巴非常享受这种耐性推进突然加速的过程。
老巴这个人还是一个很分裂的人,他信教信催眠术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在书中歌颂信仰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宣传因果轮回,但是他并不相信这些东西完全能胜过险恶的世道人心,能赢过利益与欲望的夹击。
他写品格高尚的宗教导师,也写利欲熏心不折手段的宗教投机者;
他写天使般的女性如何通过善良获得幸福,也写天使般的女性如何一步步被利益和欲望迫害至死;
他写平凡的大学生如何为萍水相逢穷困潦倒的老头子付出善意也写这位大学生长大后如何心狠手辣帮助情妇夺取老公家产;
他写保持才华出众与世无争的艺术家如何获得好报也写才华出众与世无争的艺术家如何被人谋夺财产。
有时候想想,在老巴笔下“坏人得逞”的结局还是颇多的,《邦斯舅舅》里满怀小市民阴险的西卜太太最终也捞到了好处过得挺舒适,害死邦斯的亲戚们到手了邦斯全部的财产;
《高老头》里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榨干老爹最后一点油水断送老爹性命之后照样夜夜笙歌;
《欧也妮葛朗台》里朴素真挚的欧也妮等了初恋一生等回一个心狠手辣攀龙附凤的混蛋,最后孤独终老;
《贝姨》里圣母一般的阿特丽纳夫人最终还是输给了自己丈夫按捺不住的寻花问柳淫欲;
《夏培上校》里耿直高尚的上校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妻子情愿接受自己“已死”的现实;
《禁治产》里品性高尚的男爵难逃阴险妻子的“疯子”指控;
《比哀兰德》里纯洁天真的少女还是一步步被老女人的折磨和利益的勾结给逼上绝路。
老巴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社会史学家,他如实地反映着社会与人情,同情美德,但并不美化美德的遭遇;颂扬宗教,但并不回避人性的污秽;他只是非常仔细地讲诉着现实,所以看老巴的书,是不会有太大情绪波动,他只是让你觉得非常发自内心的无奈——
他并不将社会描述得一片黑暗,但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心好报这样的奢望;
他并不信任人性和人心,但也不会吝啬对于美德与高尚的赞美;
有时候,我会想老巴是不是心中也是非常纠结的,因为他有一本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不用去看的小说叫做《于絮儿弥罗埃》。这部书描写了一个从头到脚从外貌到灵魂无不闪耀着圣光的少女,如何在宗教的呵护下,发挥爱与善良感化尘世的恶意,获得终身幸福。——说实在的,棒子剧都没有这么假,芒果台自制偶像剧都没有这么扯,但是老巴做到了。
也许,在缺乏家庭关爱,成年后又一度疲于债务,身高和长相都欠佳,对于社会折磨认识很深刻的老巴心中,存在过那么一个理想——真善美终究可以战胜尘世的一切利益与欲望,但是老巴也知道这种想法——too simple too naïve ,所以他也只是偶尔发泄发泄这种幼稚的情绪。
我常常会不自觉地将雨果和巴尔扎克做对比——
雨果的文字是有情绪上的阅读快感,如同过山车一般令人心襟激荡,而老巴的文字,就是一辆特慢绿皮火车,慢悠悠地载着你看世间风景。
雨果的文字,如烈日骄阳,将人性的光辉与阴影、悲壮与卑劣照得分明,而老巴的文字,就是小小的一枚烛火,你秉持着它探到人性那些幽微的洞穴里去,一路曲折肮脏步步惊心,但罅隙偶有花朵绽放,你无法单纯地去谴责或判断,因为你会在一路的曲折肮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所包围着你的社会的影子。
傅雷在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书里说“要小心人性,像巴尔扎克笔下西卜太太之流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比比皆是”。
当你手持老巴的蜡烛,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社会中点亮,你都会看到同样深不可测的触目惊心的洞穴,来自于你身边每一个熟悉的人,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
这个矮丑挫的法国男人曾经说过: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而他用笔写下的世界却永远随着日升月落而运行着。
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老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命题——
我将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切都讲给你听。
利益的肮脏、庸常的罪恶、人心的阴险、世俗的消磨力、情感的危险,全部一五一十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我还会告诉你,品性、美德与善良并不一定能为你带来好运,你也许还会因此碌碌无为或者命运多舛。
我更会告诉你,你的痴情会葬送你自己,你的固执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你的理想最终会被现实磨灭,你的正直会让你穷困潦倒,你的天真会给无数阴险之辈以可趁之机。
现在,你告诉我,在这样一个人间,你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
喜欢雨果的人,常常会嫌弃老巴絮叨无聊,作品缺乏戏剧性冲突与慷慨激昂的想象力。作为一个两个都喜欢的人,我非常欣赏雨果这篇写给巴尔扎克的葬词,这完全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深刻理解——
“这里有大量的真实、亲切、家常、琐碎、粗鄙。但是有时通过突然撕破表面、充分揭示形形色色的现实,让人马上看到最阴沉和最悲壮的理想。
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不自觉地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行列。巴尔扎克笔直地奔向目标,抓住了现代社会进行肉搏。他从各方面揪过来一些东西,有虚像,有希望,有呼喊,有假面具。他发掘内心,解剖激情。他探索人、灵魂、心、脏腑、头脑和各个人的深渊,巴尔扎克由于他自由的天赋和强壮的本性,由于他具有我们时代的聪明才智,身经革命,更看出了什么是人类的末日,也更了解什么是天意,于是面带微笑,泰然自若,进行了令人生畏的研究,但仍然游刃有余。他的这种研究不像莫里哀那样陷入忧郁,也不像卢梭那样愤世嫉俗。“
老巴当然既不陷入忧郁,也不陷入愤世嫉俗,他带着研究的超然态度和纠结心情,守着一位社会史学家的客观,忠实得描摹着人间,描摹着比革命、主义、改革、战争更加永恒的东西——生生不息的庸常生活和永不改变的人性。
正如雨果在那篇葬词里对这系列叫做《人间喜剧》小说的描述——
“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整个现代文明的走向,带着我们说不清楚的、同现实打成一片的惊惶与恐怖。”
这篇很好
击节赞赏!解人!
角度新颖,理解透彻,好文
看得深,看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