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象
96/10/08
遠流出版
羅蘋.梅瑞迪絲(Robyn Meredith)
藍美貞,高仁君
无
◎亞馬遜書店讀者評鑑:4.5顆星
英文書甫於今天夏天上市,作者呈現了相當多中國與印度發展的新數據、新資料,因此是目前瞭解中、印兩國目前發展狀況、未來發展方向最佳的讀物之一。可作為與中、印有商業往來的公司,投資全球股市、基金人士的重要參考書籍。
作者在書中顛覆美國一般見解,主張美國不應該害怕中、印這兩個崛起中的經濟勢力。美國(身為世界的購買者)與中國(世界的工廠)分別擁有第一與第四大經濟體,但它們將在2015年達到同等地位。雖然美國政客指責中國產品,但是作者指出,美國人民卻因為被低估的人民幣而得到好處:美國企業因為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而獲利。同時,在2003年,印度(世界的後勤辦公室)接收大部分從美國境內移出的一千萬個白領工作。不過,作者觀察到,每一美元匯出,匯創造1.94美元的財富,其中有33美分會回餽到美國。
作者認為中國在1978年市場開放,印度遲至1991年才開放市場,中國的改革也因此做得比較好。展望未來的發展計畫,作者認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較高,而印度的基礎建設與教育系統則遠遠落後,中國的成功機會更大。
=======================================
美國W. W. Norton七月出版,衝入亞馬遜網路書店前200名讀者評價4.5顆星,至今銷售仍保持1000多名,勝過其他同類書籍!
中國以共黨專制行資本主義之實,致力基礎建設,發展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印度擁有優質高等教育與英語優勢,以電腦軟體、金融、法律的服務見長,成為歐美企業的「後援辦公室」。
中國、印度納入全球經濟,成為各國企業降低成本的萬靈丹。近年來企業獲利亮麗、股市房市共創榮景、消費品一再降價,全靠中國與印度豐沛而低廉的勞力在背後支撐。
隨著中印共有數億人擺脫貧窮,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歐美企業想望已久的消費市場也逐漸浮現,刺激了各項消費品價格上揚。同時,需求增加也就意味著耗損地球資源的速度加快,生態危機加劇,這又回過頭來造成石油等原物料飆漲、通貨膨脹蠢蠢欲動、環保議題升溫,進而牽動地緣政治的板塊移動、貿易摩擦……。
作者以一流國際媒體記者的流暢文筆、堅實數據與理性分析,把中國、印度崛起的緣由、歷程與衝擊如此複雜的經濟現象,敘述得極為準確、清晰而可讀,功力直追《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
========================================
“構造經濟學”
文/摘自《龍與象》引文
二○○三年六月,印度總理瓦巴義(Atal Bihari Vajpayee)搭機前往北京訪問。這是一趟劃時代之旅,距離上一次印度領導人訪問北京已近十年,當時的中國,放眼望去盡是腳踏車和呆板枯燥的建築,以沈重的腳步追趕二十世紀。但這次瓦巴義的飛機降落時,他以為自己看到的是海市蜃樓──北京市郊數千家工廠林立,這些工廠幾乎全在過去十年間蓋的,工廠給勞工穩定的薪水,也帶給眾人希望的未來。中國已從過去直接跨入未來。
他踏進極為現代的新機場,這只是是中國眾多新建機場之一。瓦巴義和代表團成員開上北京新建的高速公路,看到光鮮亮麗的汽車一輛輛飛駛過無盡的建築工地,陽光下,數百架起重機的剪影編織出一片都市風景。寬闊的北京街道,兩側耀眼的新摩天樓節次鱗比,這些建築都是近十年開始施工,中國經濟起飛的速度,比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更快。瓦巴義從車窗看出去,看到了比統計數據更清楚的事實:印度已遠遠落落中國。
幾十年來,印度與中國的經濟一直孤立於世界之外,緩步前進。人民窮苦,生活改善無望。然而,中國在一九七八年對世界敞開大門,印度卻沒有,兩國的命運就此改觀。
瓦巴義率團訪問中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五年,數千萬中國人開始發現,隨著經濟起飛,他們的未來將為之劇變。自一九七八年起,海外企業投資總額超過六千億美元,遠超過美國在二戰後根據馬歇爾計畫,協助歐洲重建的金額 1。外資在中國興建數萬家工廠,雇用上千萬勞工。一般勞工的薪資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五倍,數千萬人擁有行動電話、電腦,甚至汽車與公寓。(譯按:目前中國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過四億。)
相較之下,印度似乎仍停留在從前。幾十年的老舊機場殘破不堪,沒有高速公路,路面坑坑洞洞,車輛壅塞,放眼望去,路旁盡是骯髒破屋。城市貧民窟人滿為患,他們就著汙穢的水道洗澡、洗餐盤、大小便,環境衛生堪慮。一九九一年,在中國經濟開放十三年之後,印度勉強開放外國投資,之後經濟改革忽而開放、忽而限制,縱使印度人民一般生活狀況已較改革之初進步,但比起中國平均改善的幅度,還是落差很大。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來,已有巨大變化,國民所得成長至印度的兩倍。雖然中、印兩國仍屬窮國,但是到了二○○一年,中國已有八三%的人脫離每日靠一美元生活的貧窮線,而印度只有六四%的人脫離 2;二○○五至○六年(三月底)會計年度,外國人對印度投資七十五億美元,而在中國,外資每六個星期的投資就已達到這個金額。當印度經濟牛步前進時,中國已是飛龍在天,躍入未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印度有民主、有廣大的英語人口、明確的司法體系,而且和西方關係深厚;中國政權專制、英語人口少,法治也不健全。不過瓦巴義從座車裡可以清楚看見,中國人民的生活大都比印度人好。
這本書講的是中、印兩國如何改變自己命運,也改變世界的故事。兩國從開發中國家蛻變為超級強國,印度採取緩慢而穩定的成長,與中國拔地而起形成明顯對比。這兩個國家在各個方面都截然不同,就像甘地與毛澤東殊異。印度民主,而中國專制;資本主義的印度經常反商,而共產中國卻親商。印度眾聲喧嘩,國內通行三十種語言,全國時區(因所跨經度範圍而)與世界其他各地相差半小時,這點也讓人混淆,因此例如台北是半夜十二時,在印度孟買是晚間九點半。中國則簡單許多,普通話通行全國,時區劃分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相同,而且無疑由共產黨當家。
中國的實力一眼可見,而印度的則較不容易發現。印度的強項在於人力資源能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還在迫害資本家的時候,印度的經理人已從征戰國內市場中獲得經驗,因此商業經營表現得比中國好。中國在文革時期曾關閉大學,印度則加強大學教育,培育出新一代的醫師、學者、科學家與工程師。
中印兩國的共同點在其轉變,以及改變世界的方式,這是自美國崛起於國際經濟舞臺以來,最教人震撼的。中印的影響力可從以下見出端倪:沃爾瑪超市的商品降價再降價;美國國內油價大幅攀升;美國人的薪資縮水,甚至連呼吸的空氣也不再相同。消費者打技術支援電話,接聽的人操著外國口音;大批從南中國海運往西半球的貨櫃船滿載貨物,吃水特別深,這些貨物全來自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中國工廠。從原始數據來看,事實最為清楚。印度與中國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大國,兩國在未來幾十年將持續成長,並在下一個世代前主導世界經濟。
突然之間,中印兩國提供勞力與合作,既是西方的客戶,也是競爭者。從紐約到東京、從倫敦到法蘭克福,各大企業的董事會主管都染上印度熱,就像十年前的中國熱一樣。那些企業大老闆連咖哩與熱炒都分不清,就爭相住進亞洲新建的五星級飯店。他們住的地方雖然光鮮亮麗,卻只敢用瓶裝礦泉水刷牙漱口,以免生病。他們穿梭大半個地球,因為這兩大崛起經濟體的飛速成長,相形之下,美國、歐洲和日本有如原地踏步。一時之間,和印度、中國做生意,成了西方企業快速擴充的唯一希望,也唯有靠這方法,西方企業老闆才能讓股東滿意。
或許,最驚人的改變是發生在新興的全球就業市場。即使近如九○年代,激進派仍擔心全球化可能危害窮人利益,其實,這個論點在中印兩國完全行不通 。美國企業與各地的資本主義者到亞洲,雖不是為了幫助受壓迫的窮人,但最後還是幫了他們。姑且稱他們為意外的行動主義者吧!
過去十年來,由於全球化帶來工作機會,即使工資在西方標準看來實在微不足道,印度和中國合計卻仍有兩億人口脫離貧窮。這讓那些關切世界貧窮問題的人大感驚訝,如果甘地、尼赫魯、毛澤東等關心窮人的二十世紀政治人物仍在世,他們也會嚇一跳。工作機會轉移海外,這個趨勢遠超過多年來保護窮人遠離大企業的力量。美日英等開發國家遭遇工作外移的挑戰,而窮國則贏得工作機會。全球化改善了窮人的處境,同時也讓歐美中產階級倍感威脅。
本書將探討透過網路連結亞洲勞工的能力對世界商業有何影響。數百萬工作機會在西方消失,為數龐大的中印勞工取代了西方人,他們做相同的工作,甚至以極低的薪資搶走西方白領的專業工作。許多產業的西方人忽然發現,如果工作內容相同,他們再也無法期望薪水能超過開發中國家人員的十倍。印度大學畢業生樂於擔任企業免付費專線的客服人員,聽取美國消費者的抱怨。此外,數千萬中國年輕人從鄉村搬進城市的工廠宿舍,為外國代工製造成衣、數位相機與電腦;歐美高薪人才也面臨遠距競爭,因為中印兩國每年投入職場的大學畢業人數,已遠超過所有歐洲國家與美國的總和。
對歐美的中產階級來說,全球化的黑暗面令人恐懼。世界勞動市場一下子增加了超過十億勞工,許多西方人將被迫丟掉工作,如果不採取行動,增加自己的勞動競爭力,就得眼睜睜看著生活水準降低。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農人遭工人取代;二十世紀工廠生產線讓許多血汗工廠勞工失去生計;不過就在十幾年前,藍領工作移往墨西哥,許多美國工廠因而關閉。歷史一再重演,每次都為世界勞動市場帶來陣痛。
中印崛起的意義不僅是工作外移,它也關係到後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的轉變,關乎如何平息對石油的渴求,也關乎環境巨變。這就是結構經濟學──中印崛起牽動了全球政經形態丕變,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發生。
全球經濟的關聯已密不可分,彼此交織影響猶甚以往。中印的改變正以快速且驚人的方式,引導世界未來的走向。過去全球市場從未有過如此高度連動,想像一下,如果十三世紀的絲路與十六世紀的香料之路(Spice Route)合併為一個大市場,湧入大量貿易,這一全球貿易的結合又因現代科技而超載。現在中印兩國銷售至西方的貨運量不再以駱駝或 帆船來計算,而是以貨機、貨櫃輪船或網路交通來算。
本書要告訴你,中印兩國崛起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未來這兩大國的潛在影響力,讓人感到害怕,又容易低估情勢。《龍與象》試圖證明,世界不僅能適應中印的崛起,還能更加繁榮。但我們必須先瞭解這兩個已對西方敞開大門、走入二十一世紀的大國。
=======================================
精采試閱
第五章:拆解式生產線
一如往常的午後,中國南方的工廠大門口前堆滿當日剛出產的貨物,磨損的卡車隆隆駛出來,準備前往香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重要樞紐。當夕陽餘暉灑在香港碼頭,貨車駛進鄰近社區,周圍運輸工廠林立,整條街道上演著同樣的故事:內地來的貨車一停下來,一群穿T恤短褲、精壯結實的男人便從一旁爬上貨車,爭相搬運紙箱。搬運工每天的工資就按紙箱重量計算。工人以超高效率將成箱貨物搬進附近倉庫過磅,接著又大步走回貨車卸貨,倉庫裡的工人逐一為箱子秤重、量尺寸,並貼上電腦條碼,標示紙箱內容說明。整個作業流程與鄰近的優比速(UPS)或聯邦快遞毫無兩樣。另一組工作人員則將貼了條碼的紙箱堆進貨櫃,再把貨櫃直接裝進飛機或貨輪。等到卸完貨,貨車司機隨即返程,越過邊界,開回大陸的工廠裝載更多貨出口,而在倉庫這一頭,空貨車離開不久後,另一輛隨即定位停下,等工人快速搬運貨櫃上車,再開一小段路運往機場貨櫃區或香港的大型貨櫃碼頭。
教人意外的是,這些中國工廠並非以成品裝箱直接運抵西方的貨架,而是把半成品從一個工廠運到下一個工廠,零件經工廠生產線加工,整合為成品後,當天就馬上運走,因此,貨櫃裡的一些零件可能早已進出過好幾個港口,最後才運抵威斯康辛州的沃爾瑪超市或英國倫敦音響專賣店。傍晚時分,香港運輸物流公司會通華聯國際(Trans Global Logistics)的倉庫正在裝櫃,將成箱的中國製汽車車窗運往韓國組裝廠,堆在一旁的Treo手機的半成品,準備送往台灣工廠加裝高科技零件,倉庫裡還有中國製布料,等著運往倫敦。另一邊是進口貨物,包括成堆日本製晶片,準備運往中國工廠,加工製為電腦運算處理器。還有一些完成品,多半是大陸好幾個工廠的零件組裝而成,包括兩千雙New Balance網球鞋,裝滿一個二十呎高的箱子,等待運至洛杉磯的鞋櫃(Footlocker)連鎖鞋店;數百件中國製藍哥(Wrangler zip-fly)牛仔褲,等著運到巴基斯坦;旁邊箱子裝滿了設計師品牌毛衣,毛衣原料來自法國的亞麻纖維,在中國中部紡成麻線後,再運到南方織成毛衣。從原料到成品,製作經過好幾個工廠,成品以亞洲航空空運,經韓國首爾運到紐約伊林費雪(Eileen Fisher)的倉庫。中國人除了搭單程巴士去找工作外,通常難有旅行的餘裕,而許多中國產品經歷曲折的出口旅程,即使是最有經驗的環球旅行家,恐怕也會厭倦。
世界貿易方式已經改變,歐美消費者在貨架上所購得的商品,是順著截然不同的新組裝線,往返全球各地而來。十年前,這種從工廠到消費者之間,猶如彈珠台般曲折迂迴的途徑是不太可行的。但在一九九○年代,企業開始尋找能以最低成本製造產品零件的區域;在此同時,拜精密科技之賜,過去認定只是夢想中的物流路線,也化為實際:在不同工廠,甚至是不同國家間,已創造出完美無瑕的連結。節省成本的努力配合高科技的威力,企業得以改變大多數消費商品的製造方式。
前一次同等規模的製造業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當時亨利˙福特藉由推行生產線,革新商業世界。他把製造汽車所需的全部原料和零件,集中在同一地點,要求工人各就各位,每人只負責製作或安裝一項零件,直到合作完成一輛汽車為止。北密西根的鐵礦石以船運到底特律,從福特車廠的一端進入,汽車成品則從另一端出來。其中過程包括將鐵礦煉成鋼鐵,壓製成車蓋、車門,然後安裝引擎等數百種零件,最後,汽車成品送出廠外。一九二○年代,總計四萬名工人在福特的底特律廠區賣力生產T型車,這相當於一個城鎮的人口。一波又一波人口移居底特律,到自動車廠討生活,消費者則能購買自己想要的各種顏色的汽車──只要是黑色的都行。
到了二十一世紀,一切都改變了。亨利˙福特的組裝線被分割成數千部分,分散世界各地。新的作業系統叫做「拆解式生產線」,這是許多公司為降低成本、提升品質,兼以縮短成品上架時間,急於把產品製程拆解成數個部分的結果。這種製程與上個世紀截然不同,因而「組裝線」這詞彙已被「供應鏈」所取代。現在生產過程的每一步驟,猶如一條靈活鎖鏈中的環節,一個串一個,綿延不絕,好像一條剪不斷的供應鏈。鞋子、手提電腦、毛衣、玩具和大部分消費商品的傳統組裝線,皆已支離破碎。至於車子這類昂貴產品,供應鏈更是複雜至極:每輛汽車平均約需要五千個零件,而且還是來自世界各地。即使是便宜玩具,也可能是來中國某省十多間不同工廠製造的零件組裝而成。如何確保在供應鏈上有效運輸貨物,也變得極複雜而重要,甚至當今經理人已在商學院研讀這個過程,並利用專門電腦軟體追蹤管理來自全球的零件。豐田汽車等大型製造商,要求供應商在各別零件上加裝無線射頻辨識標籤,以協助公司電腦系統在正確的時間點,把零件從卸貨港口的貨車,送往最後組裝線的運輸帶。把不同零件拼湊在一起,猶如一場令人眩目的舞蹈,涉及了日新月異的科技、真正的跨國企業,還有遍佈全球成千上萬的工廠。
以下就是目前拆解式生產線的運作方式:如J. C. Penny之類的百貨公司可能訂購十萬件襯衫。首先,該公司也許向韓國廠商購買紗線,運到台灣染色並織成布,襯衫鈕扣或許來自日本公司的中國廠,然後這些鈕扣和剛織成的布料,又被送到泰國剪裁、縫製襯衫。流行趨勢瞬息萬變,商家希望盡快把襯衫上架,因而將布料及鈕釦分送五家不同泰國廠,各廠僅需趕工輸出兩萬件襯衫。如此一來,完工速度將比單一工廠生產十萬件來得更快。簽下訂單五星期後,這十萬件襯衫已在世界各地上架。乍聽之下,似乎沒必要搞得如此複雜,但這種貨運狂熱卻可降低存貨,所以值回票價。倘若這批襯衫在見異思遷的消費者換了口味後才上架,勢必造成存貨問題。
如今每項產品的製作涉及眾多工廠,並需藉助高科技來追蹤組裝時應該添加的零件,因而生產客製化商品已變得更加容易。這也與亨利‧福特的組裝線大異其趣;當時只生產單一顏色的單一樣式產品。耐吉開放顧客在網路上訂製專屬網球鞋的理由之一,在於負責表層的承包商已經足夠專業,可以根據顧客要求縫製不同顏色花樣。戴爾電腦可以依客製訂單來組裝電腦,正是因為它不需要自行製造每個零件,只需要安裝不同外部供應商所製的零件。對今日的消費者而言,選擇顏色只是第一步,許多產品連最小細節也可以客製化。這與福特的黑色T型車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拆解式生產線是國際化的骨幹。拆解組裝線,並將生產線散佈全球的能力,大大改變了公司及所屬員工的角色。人們不再需要遷居底特律,才能在福特汽車工廠工作。反之,汽車公司拆解組裝線,將工作移往其他擁有廉價勞工、佐以具備優良運輸條件的地點。遷移的是工作,而不是人口。根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研究顯示,約有一五%的北美公司和二九%的歐洲公司,已不再為國內市場製造任何產品。
拆解式生產線使公司變得極有效率,在最便宜的國家生產成品零件,然後把零件運至下一個工廠據點。這個方式也讓工廠得以專注於各自最具生產力的部分,替全球消費者降低產品價格,並把工作機會散佈全球。波士頓顧問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高級顧問湯瑪士‧霍特(Thomas Hout)估計,國際化供應鏈的效益,導致美國銷售的工廠貨品降價達五%。另外,根據美國智庫進步政策研究院(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數據,過去十年來,美國進口T恤價格平均降低了三○%,從一九九六年的二‧一四美元,降至二○○五年底的一‧五一美元。
無論是經驗豐富的西方企業,還是參差不齊的亞洲企業,都達到史無前例的專業化。舉例來說,中國深圳就有公司專為玩具、玩偶製作數千種塑膠眼睛,而且只生產眼睛。因此這家深圳工廠成為許多玩偶國際化供應鏈的一環。這種專業化的結果,導致許多公司不再製造他們銷售的產品,或者說,不再銷售他們製作的產品。頂尖企業現在只專注於他們擅長的部分,聘請專門承包商製作產品零件、組裝來自其他承包商的零件,或把成品裝箱,準備運到消費者手中。如此一來,許多全球最成功的企業,都須依靠發展中國家替他們生產產品,無論是玩偶、鞋子或電腦。當工業化國家忙著去工業化時,發展中國家卻汲汲營營於工業化。
許多金字塔頂端的美國公司歸結:他們真正的角色在於開發新產品或行銷商品,而非辛苦製造每個零件、把產品組裝起來。很少西方公司可以把自家產品的組裝工作做得最好、最便宜,所以他們找人代工。舉例來說,蘋果公司創造並行銷iPod,然而iPod核心零件的晶片卻是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一家小公司所發明,機身則在中國製造,再運往世界各地。美國沃爾瑪百貨興建大型商場,以低廉價格替消費者向製造商下單訂購商品。雖然沃爾瑪銷售商品數量位居美國企業之冠,但是沃爾瑪本身卻沒有工廠。光是沃爾瑪百貨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量,就比加拿大全國自中國進口量還高。
公司為何要大費周章,從根本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主要目的在於降低成本,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計畫再複雜也不嫌麻煩。就拿亨利‧福特的組裝線來說,二○○六年,福特汽車公司付給美國員工時薪二十七美元,如果加上健保及其他福利,時薪為五十二美元。福特公司組裝線上的美國汽車工會成員,擁有高技術能力,當然足以勝任製造儀表板的工作。但是如果福特自密西根汽車工會的零件供應商訂購儀表板,只讓福特員工負責安裝,卻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因為供應商只支付員工約十五美元時薪,就算把福利算進來,也只有二十五美元。又譬如說,福特在北卡羅來納雇用非工會的供應商製作儀表板,時薪將降為十美元,或含福利在內的十六美元。這讓福特可以更便宜的價錢取得儀表板。若福特的供應商又把儀表板零件外包給全球其他地方的公司,那麼就能以更低的價格供應儀表板。供應商可能會向中國工廠訂購計速器,員工日薪僅二美元;把儀表板後的線路代工交給墨西哥工廠,員工日薪僅四美元;暖氣通風口則購自另一家中國工廠,員工日薪僅一美元。由於製造儀表板的塑膠需要動用昂貴而高科技的製模工具,所以很可能是在供應商的美國工廠製成;該廠員工再把各零件組合成儀表板,然後交貨給福特。打造一個「全球化」的儀表板,即使加上海外運送零件往來的費用,相較於亨利‧福特的組裝線模式──要求員工在偌大廠房內製作計速器、線路轉換器、暖氣通風口、引擎和其他零件,最後才組裝成車,還是很划得來。
從組裝線到拆解式生產線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幾。首先,美國汽車公司的供應鏈,由底特律外移到其他各州的零件工廠。接著,最簡單、勞力最密集的零件,改由工資低廉的墨西哥工廠進口。現在則有越來越多日益複雜的零件,是向中國、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購買,然後飄洋跨海運來,安裝在美國汽車上。頂尖企業只在國內工資高昂的工廠內,製造價值最高、難度最高的部份,以及那些需要依賴專利知識的部分。不過,海外工廠的技術愈來愈好,足以生產各種消費商品的專門零件,這類工廠往往位於中國。中國至少佔據大多數拆解生產線的其中一環,以工資低廉及現代化的基礎設備,成為極具競爭力的製造業點。不過,今日的拆解式生產線的全球化程度驚人,因為其他國家在生產特定產品及零件方面,已比中國更便宜或更有效率。
中國似乎擁有取之不盡的低薪工人,這點雖然重要,卻還是不夠。還有國家的工資比中國更低廉,例如大多數非洲國家、鄰近的孟加拉、柬埔寨、越南及部份印度地區。工作機會在全球遷移,尋找最低工資的落腳處,但低薪卻不是工作遷移的唯一理由。在最後組裝如服飾、鞋子或DVD播放器等勞力密集產品方面,中國非常具有成本競爭優勢,即使部分高精密零件必須在其他地方製造。但若是僅涉及少數員工,而需大量投資於如機器人等昂貴器材時,美國、歐洲、日本及韓國的效率,仍然略勝中國一籌。在組裝線分解開來後,每項工作得以在全球最合適的地方完成。
隨著貨車、火車、航運和飛機形成綿密的全球運輸網絡,國際貨運也變得更便宜。距離上海機場只需五分鐘車程的優比速倉儲中心,外觀平凡無奇,卻是全球大量新產品的集散中樞。厚紙箱、木箱整齊堆疊成列,各列編碼,看來就像是一個超大型的車庫。一百四十名員工每月要處理八千噸出口品,以及三千噸的進口品。在某個春天,一列裝滿電子產品配備的木箱,從紐約甘迺迪機場運至上海,一旁是一堆看似捲好的地毯;這些「地毯」其實是昂貴的日本布料,準備送往中國製衣廠。布料旁邊則是四呎高的紙箱,內有每星期定期運送的汽車天線;這些天線是由通用汽車公司澳洲廠所製造,準備運到通用汽車上海廠。旁邊還有兩個貨板的迷你滾珠軸承,打算要送往美商希捷科技(Seagate Technology)距此地約兩小時車程的無錫工廠,該公司專門生產電腦、電玩、數位相機、MP3播放器及其他小機械產品所需的儲存器。另有一隻巨大木箱裝著來自荷蘭飛利浦公司所製造的活動式X光機,這是寧波一所醫院所訂購的。倉儲一角有個保險室,儲藏價值不斐的微處理器,隨後將運往距此地不遠的蘇州電腦組裝廠。這些複雜的微處理器來自加州的美商超微半導體公司,在這個上鎖的保險室裡,隨便一個厚紙箱裡面的價值就可能高達十萬美元。
這些進口量相較於持續出口量,只是小巫見大巫。每天淩晨開始,十輛載著硬碟的貨車,依序停靠在UPS倉儲,員工開始秤重、計量、紀錄貨運,並填寫通關文件,紙箱只在倉儲待上數小時,就由貨車載往機場。這些硬碟是希捷科技中國廠所製造,將從上海運往芝加哥、洛杉磯、達拉斯、馬來西亞及香港等地;平均每日產量二十五萬個,也許你家電腦的硬碟就是其中之一。同一時間,一輛風塵僕僕的藍色貨車從三小時車程遠的寧波趕到,橘色叉架起貨機迅速駛往貨車後方,卸下裝滿汽車零件的木箱,這批貨即將運往俄亥俄州楊格城的德納企業(Dana Corporation)。接著,員工又從白色貨車卸下廣達電腦上海廠所生產的電腦螢幕。貨車司機啟動引擎,然後前往上海機場,把這批螢幕送上飛往馬來西亞檳城的航班。戴爾在當地按照客戶的客製要求組裝電腦,然後再把電腦運回美國。
其實,現今的拆解式生產線不只應用在工廠作業,服務業也開始仿效工廠組裝線的概念,將服務流程分散於全球不同地區進行。亨利‧福特率先發展的組裝概念,起初運用在汽車業,接著,製造業每家公司幾乎都採相同做法,最後連服務業也跟進。將組裝線的概念運用在服務業,摩城唱片(Motown Records)創辦人貝理‧戈迪(Berry Gordy Jr.)堪稱先驅,他曾在福特公司組裝線工作,見識過組裝線的生產流程。一九六○年代,貝理的唱片公司藉此生產流程,大量創造賣座歌曲,旗下歌手都必須遵循這套標準化流程,從寫歌、錄音、品管部門,最後到行銷。摩城唱片採用的組裝線模式,如今已不再侷限於歌曲製作,而是廣泛運用在全球供應鏈,包括電腦程式撰寫、消費產品設計、銀行貸款處理或顧問公司簡報的製作。近幾十年,愈來愈多公司將白領服務工作外包,就像福特或其他汽車製造商當初逐步將製造工作委外一樣。一開始,他們將工作外包給美國公司,接著又外包至印度等境外地區,藉由可靠的科技溝通,將廉價勞力納入生產供應鏈,一如中國工廠透過高速公路基礎建設,得以和國際貿易接軌。
中國正加速輸出白領人力,印度則增加工廠出口,兩個低薪國家在各領域的競爭力,取決於基礎建設。印度的基礎建設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英語人力,透過現代電信與電腦科技,他們與西方連結,這是印度吸引白領工作的優勢。中國政府則努力建立高級的硬體基礎建設,例如總長數十萬里的高速公路以及現代化機場,有利中國主導製造出口市場。如果沒有高容量及可信賴的現代化基礎建設,全世界複雜的供應鏈系統便無法運作。中國新增工廠與印度客戶服務中心的增加,加快了傳統組裝線的分解,提升中國製造業與印度服務業的產能。
印度和中國再度與世界接軌,分散各地的生產線徹底改變了世界商業版圖,對開發中國家大有助益。由於新工廠帶來工作機會,世上最窮的數億人口得以脫離貧困。根據世界銀行統計,過去二十年來,中印兩國經濟成長,大幅減少了全球極貧窮人口比例,由四○%降為二○%。其經濟利益相當驚人:例如印度政府估計,未來十年印度若維持每年八%的經濟成長,將可幫助三、五億人口脫離貧窮。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數百萬個工作機會在全球移動,鄰近亞洲國家開始擔心在世界貿易舞臺上失去一席之地,各國更加關切本國勞工的未來。其實,他們無需害怕,中印兩國並未獨吞所有的工作,全球貿易量持續增加,早已大幅改變發展中國家的角色。由於分散式生產線的模式普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有了意外的新角色。例如,孟加拉或越南的產業技術雖無法製造、出口整台筆記型電腦和汽車──包括矽晶圓和最先進的引擎,但製造簡單零件絕不成問題,這些零件運往其他地區組成複雜的產品,如此一來,發展中國家即使缺乏高科技能力,也能參與供應鏈的上游,負責最初步、簡單的製造流程,例如編織襯衫的布料、生產汽車的電纜,再將產品運到中國進行組裝。二十年前,富裕國家的進口產品大約一四%為開發中國家所製造,到了二○○六年,這個比例增加為四○%。根據世界銀行估計,由於國際貿易大幅成長,二○三○年該數字將增加為六○%。拜香港、上海貨運倉儲的高效率之賜,來自未開發且經濟停滯國家的一些小企業,現在也能加入全球供應鏈的一環,而未被中國所取代。
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印度。由於企業日益走向虛擬,印度和中國經常分工負責同一個全球產品的生產線。透過跨國供應鏈管理,企業將組裝線分散在世界各地,例如僱用印度人做白領工作,以支援中國負責的藍領工作,也就是說,印度工程師先設計汽車零件,再運到中國進行組裝,就像印度班加羅爾的飛利浦工程師撰寫電腦程式後,由中國工廠的員工接手,組裝數位電視、手機與DVD放影機等產品。對許多企業來說,印度與中國在供應鏈中形成互補關係,而非相互競爭。同時運用這兩個開發中國家的優勢,便能形成強而有力、無法抵抗的營運工具,既可降低公司成本,又能縮短生產週期。
積極擁抱全球化為企業帶來顯著效益,但也隱含極大的風險。在一長串供應鏈中,只要任一環節出了問題,從海嘯、暴風雪等天災到貨倉發生火災,或是船塢工人罷工等問題,都可能造成產品銷售突然停擺,讓客戶空等,公司獲利蒙受巨大損失。然而現在公司已瞭解,大幅削減成本可抵消這些風險,但同時得考量中國政治的穩定度、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以及禽流感等疾病危機,這些意外隨時可能改變全球化風險的評估結果。
許多美國企業正把工作移往海外,雖然他們把製造產品的辛苦工作交給中國工廠,把無聊的後勤工作交給印度的客服中心,但他們仍得依賴高薪的美國員工處理較複雜的工作。尤其是曾在美國工廠、客服中心、房貸處理公司或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人,因整個辦公室外移而失業,這些人在工作被剝奪後,可能還會找到有趣的新工作,但多數的員工也可能因為缺乏技能而遭市場淘汰。
========================================
媒體讚譽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故事,作者寫來引人入勝,詳實生動。」──諾貝爾 2001年經濟學獎得主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作者分析有條有理,生動易讀。」--CBS新聞節目「60 分鐘」主持人華里斯(Mike Wallace)
「中國與印度正在進行一場不同途徑的比較實驗,中國走的路,已經有過南韓與台灣先例:極權國家只要選擇對的發展策略,很快就會有進展,但是到了某個程度,不夠民主自由,會讓成長緩下來。但是印度卻已經是民主國家,要起步跑,有著迥然不同的決策過程,而且不是全面開放,必須一個一個產業對付。
《龍與象》就是在描述這場影響全球的大實驗,實驗結果現在還沒有揭曉,中國可能持續政治緊縮─經濟開放的模式,就像現在的新加坡,而印度的未來則仍有宗教與種族紛歧撕裂民主政體的危機,誰能勝出,將是廿一世紀最令人關注的賽事。」──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郭崇倫
「梅瑞迪絲在這本書中推翻了一般(美國人對中國與印度興起)的傳統看法。」──出版人週報(Publishers weekly)
「對這兩個快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梅瑞迪絲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塞迪洛 ,墨西哥前總統(Ernesto Zedillo, former President of Mexico)
「梅瑞迪絲完全掌握到重點:全球化就是機會!」──艾斯谷,優比速的總裁與執行長(Mike Eskew, Chairman and CEO, UPS)
馬洛蒂斯在這本書中推翻了一般(美國人對中國與印度興起)的傳統看法。
──出版人週報 (Publishers weekly)
馬洛蒂斯系統化的分析……非常生動,值得一讀!
──麥克‧華萊士《60分鐘》(Mike Wallace, 60 Minutes)
對這兩個快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馬洛蒂斯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
──塞迪洛 ,墨西哥前總統(Ernesto Zedillo, former President of Mexico)
這是令人激動的新聞採訪報導,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新聞之一。
──史迪格里茲,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作者
(Joseph Stiglitz, Nobel Prize-winner, author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馬洛蒂斯完全掌握到重點:全球化就是機會!!
──艾斯谷,優比速的總裁與執行長(Mike Eskew, Chairman and CEO, UPS)
羅蘋.梅瑞迪絲(Robyn Meredith)
現任《富比世》(Forbes)雜誌駐香港資深記者,長年採訪印度與中國。1990年以特優成績從波士頓大學畢業,先後任職《今日美國報》、《紐約時報》,報導深受肯定:曾以通用動力、豐田汽車、微軟撰寫封面故事,2003年獲選World Leadership's Forum 的最佳記者。
■譯者簡介
藍美貞
政大新聞系畢業,現擔任中天電視新聞部《文茜世界週報》撰述委員,曾參與《我的人生—柯林頓回憶錄》、《公民品牌 感性行銷》、《美國總統的七門課》、《極速革命:寬頻》的翻譯。
高仁君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電子傳播畢業。現為專職翻譯和自由撰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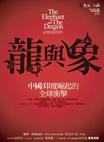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