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謀殺,以及生命的意義
2011-12-26
大塊文化
道格拉斯‧肯瑞克
300
莊安祺
无
我們愛誰、恨誰, 又為什麼會殺人、救人, 以及,為什麼人需要意義而非混沌。 數十年來,亞歷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肯瑞克一直是將演化生物學結合社會心理學的先驅人物,也是從演化觀點研究人類動機與感情的頂尖科學家。本書嘗試以演化學的觀點分析:人類表面看似不理性的行為,其實有著極深層的理性基礎。如果你想瞭解愛、利他主義、英雄主義以及成功,你也必須理解世界同時存在的憎恨、自私、膽怯以及失敗;如果你想了解人類天性何以產生哲學家、慈善家以及詩人,那你更要瞭解我們與豺狼、猿猴以及陰溝裡老鼠之間的若干關係: .歐吉桑為何偏好妙齡女郎,以及為什麼越老的男人反而能吸引更年輕的女孩? .為什麼色情雜誌或是漂亮女生有害於正常人的心理機制? .為什麼男人與女人在挑選結婚或約會對象時的標準差不多,但選擇性伴侶時卻又大異其趣?從一夜情現象切入,女生顯得特別挑剔,男生則是來者不拒。 .為什麼人會有殺人念頭?又為什麼不論男女,想殺的對象都以男性居多? .為什麼瞄一眼也會惹來殺機--非我族類的恨。 本書書寫風格「結合了名廚波登的《廚房機密檔案》以及史帝芬.品克的《心智探奇》」,可讀性頗高,書裡逐章就一個議題,探討我們所有的重要決定都是透過一組既簡單又自私的法則,從交錯的故事帶出認知科學、演化心理學及複雜理論,讓讀者藉以分辨人類行為從簡單自私到偉大利他的種種差異。 現代演化心理學泰斗、社會心理學家肯瑞克,披露人類本性自利以及與動物相差無幾的一面,而這個特性又如何和我們最偉大無私的成就息息相關。他巧妙地整合了認知科學、演化心理學,和複雜理論,勾勒出主宰我們生活原則的全貌。他掀開我們文明的面板,揭露出人類其實很像嘶吼的土狼和長嚎的狒狒,滿腦袋都是殺人的欲望和性幻想。但在他眼裡,許多根深柢固、顯然非理性的行為,比如--一夜情、種族歧視,和炫耀地大肆揮霍,到頭來都是他所謂「深度理性」的證明。 雖然我們的腦袋裡盡是讓祖先得以生存下來的簡單自利的偏見,但現代人絕非簡單自利的穴居人類。肯瑞克認為我們由祖先繼承而來的這些心理機制,最後塑造了人類今天所過的多面相社會生活,也帶來了人性中最正面的特性,包括慷慨大方、藝術創意、愛,和家族的關係。而由這些簡單的機制中,浮現了一切社會的複雜層面,包括國際之間的衝突,和全球經濟市場。肯瑞克探索社會心理學的堂奧,並由他自己實驗的驚人結果,提出詳細的圖畫,說明是什麼使得我們有關懷之情、創造的能力,和複雜的奧祕--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成為人類。 本書以肯瑞克自己多彩多姿的經驗--由他貧民窟裡愛爾蘭親戚的犯罪傾向、他自己數度被高中開除、失敗的婚姻,和殺人幻想,到最後成為知名演化心理學者、兩個年齡相差二十六歲的兒子的慈愛父親。本書探究我們心理的偏差和失敗,以及我們大腦莫大的成功。本書獨樹一幟,教人著迷,揭開了我們生理傳承的陷阱和承諾。 ◎聯合推薦 王道還/生物人類學者 伊格言/小說家,《噬夢人》作者 康古力/FHM總編輯 黃子佼/資深媒體人
道格拉斯.肯瑞克(Douglas T. Kenrick) 晚近演化心理學已被視為人類行為科學不可或缺的一環,肯瑞克教授任教於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系,係最早嘗試將演化生物學結合社會心理學的頂尖學者,他是演化心理學奠基者之一,也是社學科學裡少數被公認為最具創意又平易近人的學者,有人形容他兼具學者與喜劇演員的天分,還兼紐約皇后區街頭混混的特性。他犀利雋永的風格,和不顧政治風向追求科學真理的真誠,在這個時代獨領風騷。肯瑞克教授擔任人類行為及演化學會(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常務理事,曾發表逾一百八十篇科學專文和數十本專著,其中包括暢銷教科書《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本書係他的第一本通俗科普書。他的文章見諸《行為與腦科學》、《心理學評論》、《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演化與人類行為》等刊物,以及《新聞周刊》、《紐約時報》、《今日心理學》等全美各大媒體。現居亞利桑那州坦佩市。
中文版導論:科學與人文之間 王道還緒論:你、我、達爾文和蘇斯博士1.在陰溝裡2.為什麼《花花公子》對你的心理機制不利?3.殺人幻想4.在轉瞬間產生外團體的恨5.心靈就像著色本6.次級自我7.重建馬斯洛的人類需求金字塔8.心智如何扭曲9.孔雀、保時捷和畢卡索10.性與宗教11.深度理性和演化經濟學12.損友、混沌吸引子和如螞蟻的人類結論:仰望星辰註釋書評
內文試閱為什麼《花花公子》對你的心理機制不利? 對於逃離紐約市寒冬冰雪爛泥的難民而言,亞利桑那州大陽光燦爛的校園簡直是天堂。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和幾個年輕的心理系男同學一起到校園大道上,一邊享受藍天白雲與和煦的天氣,一邊討論本週的課業。但這些表面上意義重大的對話每隔五十五分鐘就會被短暫的課間休息打斷,這時我和同學眼花撩亂,連目光都難以接觸,更不用說專心討論行為主義和現象學之間的哲學分野了。 我們之所以分心,是因為在十五分鐘的課間休息時,一大群大學部的學生湧了出來,尤其讓二十四歲的我心猿意馬的是:在那些學生之中可有不少是面孔漂亮,身材健美的年輕美眉,穿著打扮就像她們要去為《運動畫刊》泳裝特輯拍照似的。光是要勉強按捺住我的叫喊,就已經是生理的挑戰了。我還記得那時我想,隨便哪一個亞利桑那州大的女性,都比我這一生所見過的大部分女人都美。 但當人潮散去,有趣的事就發生了。在學生換教室之際,我們身旁每秒總湧過數百人,人潮中大半的女孩看來都像是時裝模特兒,但等人潮減少到每分鐘只有十幾人時,好像來這所大學上課的女生姿色就平庸許多。究竟上課鐘響之後,那些漂亮女生都到哪裡去了? 我開始思索這些美女消失的原因:或許美女比較會老老實實上課,要不就是直奔圖書館,而姿色平平的學生則愛蹺課,空堂時愛在校園大道上漫無目的地閒晃。但這不太可能。因此我開始疑惑是不是有別的因素—或許同學和我對亞利桑那州大美女的佔比有所偏差。我揣想可能是:當男人的眼睛掃瞄大批群眾時,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表最吸引人的女人,等她走過,他再掃瞄接下來的兩三百人,注意下一個美女,雖然她在統計數字上毫無意義,但其魅力卻難以抵擋。但等人潮散去,經過的人疏疏落落只剩涓滴細流時,我們看到每一個個體,心裡的電腦也變得比較不含偏見,於是新的心理評估是,你眼前群眾中的人是平凡的一般人。我想這是比較好的解釋,但假設歸假設,光是假設根本不值一文。我花了二十年的時光和許多複雜的實驗設備,才能測驗這樣的想法是否正確。 不過,不論我的認知想法是否有任何偏見,我卻一口咬定亞利桑納州大的美女比紐約多。因此當我聽到鄰居大衛說:「亞利桑那州大無美女」時,未免吃了一驚。大衛和我一樣都是剛由紐約來此就讀的「移民」,因此他和我抵達亞利桑那時應該不會對一般人類女性的長相有太多不同的想法。而且大衛的高標準並不是因為有如雲美女齊集在他門口供他驅策之故,他的長相平平,老是抱怨週末沒有約會對象。既然如此,他還挑剔個什麼勁兒?一天他在家裡辦轟趴時,我走進去一瞧,總算看出了線索:大衛的臥室裡貼滿了《花花公子》的中央折頁美女豔照。 走馬燈印象 時間快轉三十年,來到二○○二年,我的研究團隊剛獲得一筆豐厚的政府補助,讓我們得以購買有趣的科學玩具:最先進的眼球瞳位追蹤器。瞳位追蹤器雖不能讓我們讀懂其他人的心,卻能讓我們知道人在看什麼。認知心理學一個理所當然的理論是:注意力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除非你坐在完全隔音的暗室,全身包在棉花球裡,不然你就無法注意周遭環境中的一切,不信試試看,你就知道吃不消。就連我現在坐在書桌前,眼前就已有數百樣事物—左邊是:眼鏡、錢包、手機、咖啡杯、葛瑞格?摩頓森(Greg Mortenson)著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平裝本、支票簿、釘書機、空塑膠袋、小兒子連安坐在牙醫治療椅上的側面照、一堆滿布灰塵的電腦磁片;電腦顯示幕上:韋氏字典、藍燈書屋的同義詞典、牛津引語詞典,以及其他幾本參考書;右邊是:削鉛筆機、印表機、半筒CD光碟、微軟公司的滑鼠、滑鼠墊,還有一堆電線;顯示幕下:一堆讓我可以享用免費義式濃縮咖啡、免費義式冰淇淋的優惠卡、鳳凰健身房的兩張門票,還有正在鍵盤(本身就有上百個鍵,每個鍵上還有好幾個符號,比如@、fn、~、Alt、,、>&%)上打字的兩隻手。這只是我眼前恰巧有什麼的一些例子,如果我轉頭,房間裡還有其他數百件物品。難怪我的鑰匙永遠找不到! 現在想像一名學生坐在擁擠的校園裡,擁有寬闊的視野,人潮由不同的方向湧來,全都穿著五顏六色的襯衫、短褲和鞋子,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有的人一頭紅色的長鬈髮,有的則是黑色的短直髮,各色亮晶晶的耳環閃閃發光、這邊是刺青,那邊是印著政治標語的徽章。如果這名眼花撩亂的觀眾想要注意經過他身邊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所穿的衣著,他們手上的動作,以及他們所有的對話,結果如何?他根本就辦不到,即使連幾秒鐘也不行。就如一個世紀多之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國哲學家、心理學者)所說的,這個世界只是一團嗡嗡然的混亂,唯有靠我們忽略幾乎一切的能力,才能勉強忍受。 但瞳位追蹤器卻讓我們得以看清,在一群經過的群眾之間,究竟是什麼吸引了受測者的眼睛。在實驗室中,這個實驗比受測者真正走上校園大道所看到的五光十色好控制一點。受測學生只看六或十張臉龐,在他的視線中停駐一小段時間,然後下一小群人再出現。隨後我們請受測學生指出他們是否見到了某一張臉孔,結果受測者雖然是以規模縮小的慢動作來看這些人,卻記不清楚他們究竟看到了誰,又沒看到誰。不過在這其中,有些人的臉孔比較容易記得住。 男性在觀看我們這群模擬的群眾之時,目光停駐在美女身上的時間是在長相平庸女性身上的兩倍,等隨後我們給他們看照片時,這些男性在指認出他們是否見到某位漂亮女性時也特別正確。但另一方面,如果這些男性看到的對象是一群男性,那麼即使是如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之類的人物,所受的注意也不會比一般人多,而且事後看照片時,受測的男性也不太能由一群男性中辨識出他們是否看到某些特別英俊的對象。這些發現全都符合傳統關於注意力和記憶的假設—你越注意某人或某事,就越記得住他們。只不過女性受測者卻以有趣的方式違反了這個假說。 在我們研究中的女性受測者和男性一樣,也花較長的時間注意美女,而且對於自己是否見過某個美女記得很清楚。不過她們和男人不同的是,雖然她們也注意如喬治?克隆尼型的英俊男人,但後來卻記不得她們盯住的這些男人。這倒出乎意外,因為通常注意力和記憶力之間有單純的線性聯結—你越常看某些人,就越記得住他們。 在後來與范?貝克(Vaughan Becker)、強?曼納(Jon Maner)、史提夫?顧林(Steve Guerin)所做的實驗中,我們請人玩一種名為「專心」(Concentration,又名記憶遊戲Memory Game)的遊戲。參與者得要由一大堆人中找出相同的臉孔配對,結果人人都記得漂亮女生所在的位置。有時我們改變遊戲規則,在受測者面前快速展示所有的臉孔,然後要求受測者把她們看到的人挑出來。結果頭一次測試時,女性可以挑出她們剛看到的俊男臉孔,顯示好看的男人會吸引女性的視線。但多做幾次之後,俊男的優勢就完全消失了,他們雖能吸引女性的注意,但卻在心理運作的過程中遭到放逐。 這個研究似乎證明了我的揣測,男性的注意歷程(attentional processes)有所偏差,可能會誤導他們錯估群眾中好看和平庸女性的比例。這個結論也符合我與貝克、曼納以及後來加入的同事史蒂夫?紐柏格(Steve Neuberg),和我們的學生安迪?戴頓(Andy Delton)、布萊恩?霍夫(Brian Hofer)和克里斯?韋柏(Chris Wilbur)所做的另一個研究。在那項研究中,我們把男女兩性的照片拿給受測者看,有些照片上的人長得好看,有些則普通(長相的美醜則由另一研究的參與者判斷)。受測者在兩種情況下觀看他們的照片:有時他們同時看到整群人的照片,但時間只有四秒;有時他們觀看的時間比較長,或者一次只看一張臉。一瞥整群人照片的作法就類似下課時間站在亞利桑那州大校園大道上的情況—臉孔太多,難以完全消化;而看的時間較長,或者一次只看一張臉的作法,則像上課之後人潮減少的時候,讓大腦有足夠的時間處理所有的樣本。 我們盡量讓受測者發揮注意力,發現研究的結果和我數十年前所揣測的一樣:男性高估了美女的數量(不過他們估計俊男的數量並不受影響)。女性受測者在快速展示大量群眾照片的情況下,也同樣高估美女的數量,但她們並沒有高估俊男出現的頻率。這樣的結果指向關於美女的簡單結論:她們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且壟斷了接下來的認知過程。對於俊男,其結論則有所不同:他們吸引女性的眼光,但卻無法獨佔她們的心靈—好看的男人很快就在認知處理的過程中被淘汰。這種男女之別正符合兩性不同的求偶策略—女性較會挑三揀四,而且對與陌生人的一夜情比較沒興趣,原因稍後再談。現在讓我們回到朋友大衛貼在床頭的《花花公子》。 對比效應:《花花公子》床頭照的問題 男人預設的認知過程創造出滿是荷莉?貝瑞(Halle Berry)、凱特?哈德森(Kate Hudson)、珍妮佛?羅培茲(Jennifer Lopez),和碧昂絲?諾莉絲(Beyoncé Knowles)等美女的想像世界。一方面,在人口過多時,男人可把這點當成良好的副作用:認知過程在迅速負載資訊時,這世界往往看來更美麗。至於女性,她們雖也會高估美女的數量,但卻不會高估俊男的數量,因此她們看到的那一面不像男性看到的那般光明。我和莎拉?古提耶絲(Sara Gutierres)所做的另一項研究則認為,過度耽溺美貌,對兩性都會造成反效果,雖然這兩種反效果截然不同。 在我那個張貼《花花公子》清涼照的朋友痛斥亞利桑那州大無美女時,我正好修了一門「感官與知覺」的課。研究知覺的學者喜歡揭發心理錯覺和錯誤的判斷,而其中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所謂的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s)。其實你自己就可以做對比效應的實驗:在面前放三桶水,左邊那桶是冰水,右邊是熱水(但不要太燙),中間那桶則是室溫。把左手放進冰水,右手放進熱水,歷時一分鐘左右,然後兩手一起拿出來浸在溫水中,結果你就會感到雙邊心理感知的不同。你的大腦會接到矛盾的訊息:左手的神經元會告訴大腦中間那桶水是熱的,而右手的神經元則會傳達同樣的水是冷的訊息。根據哈瑞?赫爾森(Harry Helson)一九四七年所提出的理論,我們會以任何新形式的刺激和我們適應的程度(根據過去經驗—尤其是最近的經驗—做出對正常的期待)相比較,做出心理判斷。熱或冷、重或輕、鹹或甜,全都視你最近的經驗而定。 我認為感官適應的過程也可能適用於對美醜的判斷,因此和古提耶絲一起實驗,測試這個想法。古提耶絲當時是非常用功的大學生,後來成了我的同事,也和我合著了許多關於此說的許多研究。我們的第一個研究是先請受測者觀看其他女性的照片,然後再請他們評斷長相普通的女性究竟是美是醜。其中一半的參與者先看了傾國傾城的絕色美女照,另一半則先看一些長相普通女子的照片。結果就和經歷兩種不同水溫的受測者一樣,不同外表的感官經驗的確影響到人對一般情況的判斷。不出所料,如果受測者先看過一連串美女,再看到長相平庸的女子,就會認為她們比一般人醜得多。 在稍後與勞芮?戈德柏(Laurie Goldberg)合作的研究中,古提耶絲和我想要證明同樣的認知過程是否會影響對於我們所愛者(或者所認識且有可能作為擇偶對象者)的判斷。在那項研究中,我們告訴受測者我們在進行一項「美學判斷的社群標準」研究,說因為人們對於藝術品味爭論不休,因此我們希望由隨機取樣的學生中作一點瞭解。 受測者共分為三組,控制組的受測者看的是如約瑟夫?亞伯斯的《向方形致敬》(Josef Albers: Homage to the Square)等的抽象畫,男生組看《花花公子》和《閣樓》雜誌中的美女夾頁,女生組則看《花花少女》中的裸男圖片。等他們都看完之後,我們請他們評估自己與正在交往男女友之間的感覺。當然這又有一番說詞—心理學家意見分歧,不知道有交往對象會使他們更願意接受新美學經驗,還是讓他們不願接受新事物。我們說,為了要瞭解哪一方才正確,我們得知道受測者在交往關係中究竟投入到什麼程度。結果他們自述的認真程度視他們是否看了裸男裸女圖片而定。在這裡我們又發現了有趣的性別歧異:剛才看過裸女的男性受測者自認為他們比較沒那麼深愛伴侶,而看過裸男照片的女性受測者則沒有那麼輕易動搖。 因此大體而言,見到美女會改變一般人對他們視之為美的適應標準,這對像我鄰居大衛的負面影響是:一旦他認為《花花公子》的美女才是常態,那麼真正的女人—他約會的對象,魅力就不那麼強。對正在與女人交往的男性而言,看到美女的照片會破壞他對有血有肉和他們生活真正相關女人的感受。 難道女人愛得比較深?女性不會受到同樣的負面影響,英俊男子的照片並不會破壞女性對其伴侶的感受,這不就再度證明了男人都是混蛋的假說嗎?但正如我們同僚諾伯特?舒瓦茲(Norbert Schwarz)所提出的,女性雖不會拿她們的伴侶和肌肉男相比,卻可能會拿他們和有權有勢的男人相比,而得到負面影響。 為了測驗這樣的可能性,史蒂夫?紐柏格、克莉斯汀?瑟克(Kristin Zierk)、賈琪?克尼絲(Jacquie Krones)和我做了一個實驗,請學生評估幾個單身男女的簡介。我們告訴他們,亞利桑那州大要進行一個新計畫,協助來自外鄉的寂寞新生,讓他們有機會和異性交往。如果你是參與實驗的男生,就會看到幾個女生的簡介,其中附有我們事先挑選可能是美若天仙,也可能長相平庸的女孩照片。而參與這個實驗的女生則可以看到可能是相貌英俊,也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男子照片。除了照片之外,還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個性評分,在其中一半的情況下,你會受到引導,以為已經有一群心理學者把你所看到的人歸類為「優勢/主權」高的人—是領導潛力高的人;另一半的情況則是:你會以為心理學者把你所看到的人歸類為領導力低的「追隨型」。看過這樣的介紹之後,我們會再問你們幾個有關過去交往的問題,而且為了讓大家更有參與感,因此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報名參加「亞利桑那州大單身聯誼」計畫。 你會如何回應?答案端視你是男是女而定。一如早先的研究一樣,美女會破壞男性對伴侶的許諾。在看了一連串相貌美麗、個性順從,正等著有緣千里來相會女性的照片之後,男性對他們原先伴侶的承諾程度降到最低的地步;反之,女性即使看了一連串帥哥的照片,也不會動搖她們對伴侶的承諾。但女性先別沾沾自喜,因為看到一連串在社會地位上具有優勢的男人,同樣會影響女性的忠實程度,一如男性看到美女照片一樣②。 小明星與大人物 我們看到美女或成功男性之後,是否會改變對自己的感受?古提耶絲、珍妮佛?帕區(Jennifer Partch)和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再一次讓受測者看到已經參與「亞利桑那州大單身聯誼」計畫者的簡介,不過這一次,受測者看到的是與自己同性者的資料。 每個簡介都包括名字、嗜好和興趣表列,以及此人「最傑出的成就」。每個簡介檔案都有兩種版本,描述相同的興趣和活動,只有在自述社會優勢高低之時有所不同。比如以下就是自認為社會優勢高的「卡爾?包爾斯」對自己的說法: 我認為自己有很多朋友,因為大家都依賴我,而我也很樂於接受大家的信賴。我喜歡為朋友和自己規畫新的冒險。我每週工作五天,其他的時間則在青年會教小孩跳彈簧床。我喜歡和人相處,在需要有人負責時,也總是挺身而出,擔任團隊領袖。我喜歡置身領導的地位,這很自然,而且我也因此而認識許多人。有人說我天生就擅長分派責任。在轉學到亞利桑那州大之前,我在華盛頓大學就讀,很榮幸被選為校刊主編。我已經在《跑者天地》雜誌上發表了兩篇短文,全都是談追求卓越所需要的特質。我力求言行合一,身體力行,而這也可能是我迄今成功的主因。 認為自己不具有社會優勢的卡爾則表現不出這樣的行動派氣勢,而非常恭順拘謹: 我認為我有許多朋友是因為大家仰賴我,我也樂於受大家信賴。通常我願參與朋友為我安排的冒險。我努力保持頻繁上健身房,其他的時間則在青年會教小孩跳彈簧床。我喜歡和人相處,也樂於幫人跑腿或協助大家完成工作。我不喜歡擔任領袖,這總教我不自在,也妨礙我認識人,但我卻能把分派給我的責任做得很好。在轉學到亞利桑那州大之前,我在華盛頓大學就讀,有幸被選為最佳校刊員工。我已經寫了兩篇短文,都是談滿足自己所需要的特質,希望能找到雜誌發表。我力求言行合一,身體力行,而這也可能是我迄今很感知足的主因。 有些受測者會看到八個高社會優勢的檔案,這些檔案的設計就是要讓人以為:有許多成功且努力的同性要和你爭相求偶。有些人則看到八個低社會優勢的檔案,意味著求偶的競爭較不那麼激烈。女性看的檔案和男性一樣,只是換上女性的名字,比如用愛米?包爾斯之名取代卡爾?包爾斯。每個檔案都附有照片,因此有些受測者會看到八個漂亮或英俊的同性,有的則看到八個相貌平庸的潛在競爭者。 看到極具吸引力或極成功的同性,並不會改變人對自己吸引力或社會優勢的評估,但卻會改變他們對其他人如何評估他們自己的觀感,而且這種改變和他們對自己伴侶的評估正好相反:看到一大群高社會優勢男性檔案的男性受測者,會覺得自己不太可能會受到女性青睞,成為她們的婚配對象;而看到一堆漂亮女性的女人,則會低估自己結婚的希望。 心靈糖果:注意分量 因此我們的研究認為,如果你是男性,那麼看太多美女會影響你對伴侶的感受;而若你是女性,看到太多努力奮鬥行動以求達到目的的男人,也會消蝕你對伴侶的忠誠。然而在現代社會,到處都是小明星和商業鉅子。好萊塢為了想一圓大家的美夢,因此電影和電視節目〔由《亂世佳人》到《誰想嫁給百萬富翁》(Who Wants to Marry a Multi-Millionaire),和《廣告狂人》(Mad Men)〕,挑大樑的角色全都是年輕美女和有權有勢的男人, 多如過江之鯽。因此如果你常看電影電視,恐怕對你的伴侶和你自己都有所不利。 攤開流行雜誌、打開電視機,或者上電影院一瞧,你就會進入滿是美女和有權勢男人的世界。除非你已經住在好萊塢,不然很可能天真地拿自己生活中的人相比,然後因他們的不起眼而失望,甚至影響你的信心。你該不該寫信給國會議員,要求他們立法限制媒體必須公平報導你身邊相貌平庸成就亦普通的鄰居?或者,為什麼不要求媒體只拍毫無吸引力、毫無成就的失敗者?這樣我們打開電視才會覺得自己和伴侶其實不差—直到我們發現填補這個需要的地下俊男美女富豪錄影帶為止。 為什麼我們會受這樣的影像吸引?我的揣測是:我們的大腦原本的設計就是會挑選美麗和有權有勢的人,因為我們的祖先不是挑選美麗或大人物為配偶,就是和他們競爭求偶。瞭解你的機會和競爭威脅有其益處。當然,我們的祖先活在沒有電視機、電影或照片的世界裡,他們只能看到有血有肉的真人,因此他們的心理機制發揮了原本該有的功能。然而現在這同樣的心理機制卻吃不消了。就某種程度而言,好萊塢和麥迪遜大道廣告公司所創造出的形象,就像冰淇淋的口味,五花八門的口味和形象對原本在截然不同世界用來求生存和繁殖的心理機制上發生了影響,如果攝取過多,就會有礙健康。 那我們該怎麼辦?難道面對演化的機制只能束手無策,憑它不顧我們的意識知覺,引導我們走上歧途?未必。明白脂肪和糖類攝取過多會危險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飲食,瞭解大眾媒體氾濫影像的人也可以適可而止,不要再狼吞虎嚥《花花公子》、《時人》、《慾望城市》,或《與明星共舞》這樣的大眾媒體影像。做完這方面的研究之後,我不再買《花花公子》,而且也幾乎不看電視了。因此我有更多時間去騎腳踏車或讀書(沒有圖畫的,除非是讀蘇斯博士給我的小兒子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比較快樂,但至少我不會拿自己和大富豪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成就相比,也不會拿我老婆和打上馬賽克的花花女郎相比。 本章我們已經討論了不瞭解我們天性可能會付出的代價—我們對美的視覺愛好就像對冰淇淋的渴望一樣,長久下來必會有其影響。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到更有迫切危險的傾向—如果任由我們的天性發展,很可能很快就讓我們進大牢(如幾乎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或太平間。
「肯瑞克融合個人幽默軼事、科學背景,和精彩實驗的集錦,讓演化社會心理學顯得既有趣又有深度。本書發人深省,教人入迷,讓你疑惑自己是誰。」 --理查.藍翰(Richard Wrangham),哈佛大學生物人類學家,著有《找到火:烹調使我們成為人》(Catching Fire :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肯瑞克寫得如夢似幻。」 --羅伯特.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美國史丹佛大學生物科學及神經學教授,著有《一位靈長類的回憶》(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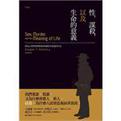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