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尔之书
2010年1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彼得
241
138000
余泽民
无
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想,我说“我们彼此陌生”并不夸张,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当然,如果你读过《一个女人》,也许对我有一点了解)。陌生意味着充满希望,在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过我忍不住想告诉你,对你我只有一个希望:不仅希望你能够成为读者,而且希望你能成为我的读者。(之后,你当然可以读其他的书——我并不是那类爱吃醋的人……) 这本书我写于1988至1989年,当时的东欧正酝酿着剧变,冷战时期的政治体制濒临结束,一个新的体制将要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新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从社会角度讲,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这种希望不仅洋溢在人们脸上,也浸润到了这本书里。我可以向你承诺,你将读到的是一部情节跌宕曲折的小说,有着犯罪小说的悬疑,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比方说,你可以在这部小说里知道上帝会不会吹萨克斯。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上帝不会。所以他才叫查理?派克到天上教他。结果令人沮丧,我们发现上帝缺少音乐天赋,死活学不会吹萨克斯。这部小说里还写了天使,他们疲惫不堪地守在主人公的家门口,坐在一部旧“拉达”牌轿车里(这些轿车是我们从曾经是苏联的苏联那里得到的),也许,他们并不是天使,而是秘密警察。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作家的妻子(这位作家并不是我!!!),她叫安娜。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会爱上她。她是一位泼辣的女性,会用口哨吹布鲁斯,臀部非常有型,用小说里的话讲:她的屁股可真漂亮。那位作家正在写一篇关于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文章,与此同时,安娜偏巧爱上了赫拉巴尔。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另外,它还有一点家族小说的味道,与我后来所写的一部作品《天堂的和谐》机关暗连——那部书有着更加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曲折情节——我将在另一篇《序》里予以介绍,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如果那部书能列入出版社的计划的话…… 关于我自己,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既没有猎杀过大象,也没有当过密探,更没有做过约翰?肯尼迪的情人。(这句话我像是从哪里引用的,只是我忘了原话的出处。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经常发生,所以亲爱的读者,假如你在我的书里找到某句让你格外喜欢,听起来显得很美很智慧很深邃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把它看作是我从某人嘴里引用的箴言,比方说,从托马斯?曼那儿,或从《论语》里。)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坐在房间里,要么写作,要么阅读。年轻时我踢足球(很有天赋),还在大学里学过数学(不太有天赋)。 还有什么该说的? 有一些非常令我敬重的作品已经先后被译成中文,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伟大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在这个世界还有几个我非常爱的人。暂时我先说这么多吧。 我亲爱的中国读者,向你致意,向你问候,我希望我们会彼此喜欢。但我并不想继续缠着你,我知道,你现在想开始读书了。 艾斯特哈兹?彼得
生活再压抑,也抵挡不住心灵的触角潜滋暗长。爱恋,无可避免。 在布达佩斯,安娜又怀孕了,如同那些年的很多事情一样,说来就来,让人束手无措。她想打掉这个孩子,但身为作家的丈夫却照例视之为好消息。安娜只能向她暗恋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倾诉自己的愁闷。这场诉说安静、强大,是一个女人无所顾忌的独白,恨的倾诉,爱的宣誓,是臆想的激情双人舞…… 孤寂而博爱的上帝很想帮助人类摆脱烦恼。为了阻止安娜堕胎,他派两位天使下到人间,甚至亲自拜查理·派克为师,学习吹萨克斯。可是,对于人间的事情,上帝能做什么呢?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想象丰富的小说,彻底颠覆了小说惯常的写法,三部曲的架构以及上天入地的角色设置让人想起空间感十足的歌剧,又似乎回荡着音乐的旋律。作者的文学手法炉火纯青,运笔所至,如行云流水,无所挂碍。阅读艾斯特哈兹,是享受,也是挑战!
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1950- )
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并获得多项欧洲文学大奖,如德国书业和平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匈牙利文学奖和桑多·马莱奖等。
艾斯特哈兹是欧洲最古老显赫的贵族姓氏之一,彼得却降生在这个大家族刚刚沦为平民的时候,对于小说家来讲“最理想的时候”。大学学习数学,曾是足球健将。1976年开始写作,已著书近30种,被译成20多种文字。主要作品有《天堂的和谐》《修订版》《心脏助动词》《匈牙利色情小读物》《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等。
译者简介
余泽民,北京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学位。1991年赴匈牙利,当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插图画家、翻译、果农、家教、编剧、演员、编辑。喜欢做一个浪迹天涯的生活艺术家,译介过2002年诺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系列作品,在《小说界》主持“外国新小说家”栏目,与汉学家合译《道德经》《易经》,著有《狭窄的天光》《匈牙利舞曲》《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等书。现居布达佩斯。
导读/彼得的布里洛盒子 钟鸣 中文版序赫拉巴尔之书忠诚篇不忠篇第三篇译后记
1 威廉斯这人最怪的地方,在于从没有人见过他。教职员手册上只有标示为无照片的一块灰格,尽管温彻斯特年鉴里有威廉斯的照片,不过只拍到了他的手或手臂而已。学校网页上只有短短的个人简历,一样没有照片。温彻斯特大学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寻找威廉斯”对他的一些学生来说,已变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事。 看来威廉斯是在躲他们,或是在捉弄他们。学生们得在开学前找到他们各科教授的照片,已经成为温彻斯特的一项传统,因为大家普遍相信,如此一来,当授课教师走进教室时,有助于缓解学生们的焦虑感。这就像是在老师出现以前,领先窃取一点他们珍贵的权威性一样。 威廉斯此举成了一条大新闻。“逻辑与推理204”这门课的几个学生对威廉斯隐身不露面的行为极为愤怒,深信他一定是在玩弄他们。一个上什么课都拎着公文包、一本正经的乖学生,拿出被他揉烂的《课程手册》,搜寻“欺骗或教职员失职”之类的条目,许多同学也都围在他旁边看。 就在那个时候,威廉斯踏进教室。他穿着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这在温彻斯特校园是相当不寻常的行为。他什么都没带,这比他的衣着更教人纳闷。没有纸,没有文件信封袋,没有马克杯。他身穿一件法兰绒衬衫,下摆还扎进裤子里。没系皮带。脚穿Nike球鞋。教授的胡子刮得很干净,这在校园里又是另一件怪事。外表看起来很年轻(以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来说),左脸还有一点一点的青春痘疤,使人联想到在火车轨道上被压扁的硬币。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他还挺英俊的,动作轻巧安静,给人一种绅士的印象。他的手常常伸在身前,一副在黑暗中找路的样子,也像在说:别怕,我就在你身后。 威廉斯教授走到教室前方的讲台前。班上总共有十五人,八个女生,七个男生;全都是白人,这是温彻斯特校园的常态,而非特例。他们身上都穿着爸妈在暑假时为他们精心挑选的衣服。多数是高年级生,因为这门课是哲学系和英文系要修三年级研讨课之前的必修课。由于大部分学生主修哲学和文学,课堂上弥漫着一股不确定的气氛。这些学生并不清楚在未来的人生里该何去何从,但在各方面表现皆有一定水平。“聪明的孩子,”一位温彻斯特教授曾这么挖苦地谈到他的哲学系学生,“但都被哲101课里的笛卡儿‘桶中之脑’理论给诱拐了”。 威廉斯正要开口说话,某人的手机却响了起来。那个学生羞愧地钻进包里寻找那扰人的东西,他则在前面等着。事实上,他看起来比那个女孩还要不安:他低着头,满脸通红,女孩则愤怒地按下按键。有些教授会让那个女孩难堪,可能叫她哼一段手机铃声,或要求在同学面前把电话打完之类令人不舒服的事。 但威廉斯只是等着。电话静下来之后,他用一种柔中带刚的语气说:“发生了一桩谋杀案。” 没有人知道该对这句话作何反应。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人大笑起来。威廉斯也微微笑着。他盯着讲台,把上面的某样东西拨开。“不是真实的谋杀案,”他说,“不是的。这是一桩可能在未来发生的谋杀案。一个……”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班上学生,手在空中挥动,似乎想把他想讲的词给抓下来。 “一个假设。”前排的女孩说。 “没错!”威廉斯说。他对“假设”这两个字很满意,因为和他想表达的故事情境很吻合。“一个假设。一桩潜藏的谋杀案。一桩未来式的谋杀案。如你们所知,谋杀案成立之前肯定会发生许多事。而那些事,如果你们够聪明的话,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他陷入沉默。他们在研讨大楼上课,温彻斯特最老旧的教学大楼。阳光穿过无遮蔽的高窗倾泻过来,几个学生遮住眼睛周围的光线。这是“东研讨室”这间教室的麻烦所在,光照的问题常使下午的课——好比“逻辑与推理204”——被迫取消,因为强光照得老师和学生都偏头痛了。 “像怎样的事?”终于有人开口。 威廉斯转头面向白板,想找可以在上面写字的东西,但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教授们纷纷囤积自己的物资,没有人留下半支白板笔。他叹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面对学生。 “譬如说,时间。”他说,“首先是时间这个变项。如果被害者和谋杀犯——” “潜藏的谋杀犯。”刚刚回答假设的女孩说。她已经认真起来了,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做笔记,一边猛点头。 “没错。如果被害者和潜藏的谋杀犯没有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发现的话,她就会死掉。” “多久以后?”有人问。 “从星期三算起,六个星期。”教授说。每个人都顿时发现,秋季学期刚好六个星期长。秋季学期之后就是学生所谓的温彻斯特学期,总共有八个星期,期间会有很多学生出国念书。“逻辑与推理204”和所有秋季学期的课一样热门,许多学生希望他们的表现能让欧洲和南美洲委员会惊艳,好赢得前往梦寐以求的国外学校念书的机会。 “其他变项还有,”威廉斯继续说,“地点、动机和情境。” 如果威廉斯有笔的话,他一定会写在白板上。坐在前排的那个女孩在笔记本上敲入这四个词:“时间”、“地点”、“动机”、“情境”,全都改用粗体字特别强调。 “好,”他接着说,“星期三见。” 教授扭头准备走出东研讨室的门,门还开着。整堂课只上了十分钟。班上学生一阵慌乱,这是他们不曾预料的情况。他们既想冲出教室享受这天剩余的时光(威廉斯的课排在傍晚,刚好是他们的最后一节课),也想搞清楚威廉斯和他所说的失踪女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等一下。”携带笔记本的女孩终于说。 威廉斯正要出门,在门口止步。“什么事?” “我们要怎么阻止它发生?”她问。 威廉斯走回教室,脸上带着谨慎的表情,仿佛在担心这些年轻又天真的学生们陷入混乱。“哪些问题才是有关联的?”他问。 那个女孩看起来一脸困惑,从笔记本上方望着威廉斯。她知道她在这里必须谨言慎行。她常常陷入一种困境,就像现在,既有主导课堂走向的冲动,又希望保持沉默,让老师忘记她的存在。所以她才带笔记本上课,她发现敲键盘的声音会让老师注意到她。她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让其他同学抓狂,同时又可以借笔记本让教授知道她在认真听课。这招的确奏效,她每一科都以高分过关,在学校的人缘也很好,完全不会被视为书呆子,就像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一头卷发、戴着胶框墨镜(就像琼?蒂蒂安在C-Span电视台上戴的那种)、闲暇时读维拉?凯瑟的女孩一样受欢迎。她绝对是有人缘的,常常和她赖在一起的姐妹会成员都这么说。她和她的朋友桑玛?麦考伊自称“游走两端的人”——既能坦然推却姐妹会的邀请,又有人脉参加男女狂欢派对。游走在两端是她们认为的在温彻斯特的最佳生存之道。 可是,眼前威廉斯问哪些问题才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深究的问题,她顿时愣住了。如果开口回答,她那成串哲学大道理必然会倾泻而出,其他同学只能无所事事地耗上一个小时。如果保持沉默,那么威廉斯就会认为她只会问一些空泛的问题拍老师马屁,不过是脑袋空空地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罢了。 “她是谁?”坐在后排的一个男孩问,及时解除了她下不了决定的困境。他就是稍早放声大笑的那个学生,笑是他在课堂上常有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事在他听来都十分无聊可笑。就拿逻辑课来说,他选了威廉斯的课之后,很快认定这门课根本在浪费他的时间。这个世界毫无逻辑可言,他知道。不过是在笼统的选项中作决定,问题反复思考却无法解决,只能在灰色地带浑噩度日。(假如你解决了那些问题,那接下来的课程里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就算作好决定、想清楚问题,世界还是会同以前一样奇怪和疯狂。 他名叫布莱恩?豪斯。跟许多人一样,布莱恩在温彻斯特学会让自己看起来像另一个人。譬如说,没有人知道过去十个月以来他为不能说的痛苦所扰,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根本不听T恤上的那些乐团。他参加兄弟会、校内社团和读书会,摆出一副非常投入的模样,实际上却极度痛恨这一切。他本来打算过完暑假就不再回温彻斯特了,但他要怎么跟他的爸妈开口?他哥哥的死带给全家无限的空虚与落寞,一定没有人能理解,幸存下来的他怎么会想虚掷自己的生命。他妈妈已经开始穿起温彻斯特大学的U领运动衫,Volvo的保险杠上也贴着“我的孩子是温彻斯特团长”的贴纸。布莱恩知道自己不可以让她蒙羞失望;然而,自从马库斯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布莱恩又瘦又高,他开始理起光头,因为他哥哥以前也这么做。温彻斯特的女孩子把布莱恩的冷漠视为一种性感的反抗,因此她们喜欢在深夜跟布莱恩在他的宿舍分享她们的想法。这是两码事。他在纽约老家有个女朋友,难道他不会有欺骗她的不安吗?他会,也不会。就某一方面来说,他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背叛。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可是在他的灵魂里满不在乎、枯竭的那部分,从不曾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最后不过是伤了一个女孩的心罢了。这就和所有事情一样,没有逻辑可言;和生死不同。 “这是第一个问题。”威廉斯说。他也越来越认真了,看来愿意回答某些问题,但必须得有人先提出对的问题。“她是谁?她名叫波丽。” 有些学生在笑。“真好笑的名字。”某人说。 “没错,的确蛮好笑的。”威廉斯同意。 “‘波丽想要一块饼干,’”布莱恩说,“‘我想我应该先让她下车才对。’科特?柯本的歌。”他皱皱眉。他其实不喜欢掉书袋,尤其是从流行文化偷来的典故,或许是因为他如此做作——坚持戴上面具、随波逐流的伪装——那正是他最痛恨自己的地方。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已经确定自己不会喜欢这门课。 “没错,”威廉斯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她多大?”一个坐在后面的同学提问。 “今年十八岁。”这也是他们刚进温彻斯特时的年纪。 “她的外表?”另一个学生问。 “个子娇小,身上佩戴许多饰品,还穿了很多洞:耳朵上缘、耳垂、肚脐上都有。她的下背上有个中文刺青,头发染成褐色。她常常意识到自己的身高,希望能再高一点。”简言之,她的外表就和在场大部分同学差不多。 “她人在哪里?”布莱恩问。 “‘地点’。”威廉斯说。“ 她怎么去那里的?”他问。 “‘情境’。”这是之前强调的最后一个概念。意思是:我们离答案并不远。 “胡扯。”布莱恩咕哝着。 “或许吧,”威廉斯说,“或许这一切都是胡扯,但波丽现在有危险,如果你们没能在六个星期之内找到她的话,她就会被杀害。” 全班再度陷入一片死寂。东研讨室里的钟继续滴答作响,光线洒落在威廉斯的讲台上。 “这些跟逻辑有什么关系?”带公文包上课的男孩问。他是这群学生中最实际的一个,也是惟一选修“逻辑与推理204”的学生——对他而言,等于是自讨苦吃。他主修文学,这在温彻斯特是个反其道而行的决定。温彻斯特在80年代改制为大学,原本是一所位于印第安纳州德莱恩市中心的小学院,与西北方一百五十英里外著名的天主教学校相比,总是相形失色,尽管宣传小册上总是欣然指出,领到罗德兹和傅尔布莱特奖学金的温彻斯特毕业生,比圣母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加起来还多。 温彻斯特改制大学之后,课程也如预期的那样变得比较专精实用与深入。就快二十年了,教职员间仍对温彻斯特的转变有不同看法,有些老一辈的仍坚持温彻斯特学院的教学理念。这个公文包男孩的父亲就是个老温彻斯特,现在是天普大学数学系教授。做儿子的数学天分虽然不如老爸,却总是懂得选择那条最直、最不困难的路,直抵迷宫的尽头。 他名叫丹尼斯?佛拉赫提,在学校大家总是戏称他“威胁者丹尼斯”。这是个大大的讽刺——即使他有这个筹码,丹尼斯也绝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他实事求是的个性让他躲过大大小小的冲突,还因为能灵巧地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而成为他父亲加入过的“斐陶斐荣誉学会”优秀兄弟会成员。丹尼斯住在斐陶斐顶楼一间可以容纳十个人的单人房。他喜欢把一头乌黑的卷发盖在眼睛上。对斐陶斐的其他人来说,他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轻易地吸引异性的目光,一直是一道难解的谜。当女孩进到丹尼斯的房里时,兄弟会的成员们会在门前晃悠,窥看地板上的四只脚——这是兄弟会宿舍一项古老(却又常常被打破)的传统。一个小时之后,门会紧紧关上,接着传出轻柔的爵士乐声(明格斯或柯川或蒙克)。大伙儿总是在想,比方说,他是怎么钓到大家喜欢得要死的莎凡娜?克里波?她几乎每晚一进丹尼斯的房里便不见踪影。 答案是魅力。丹尼斯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撒谎也好,耍手段也罢,他总能让自己全身而退,或随心所欲地和别人聊得投机。每当兄弟会出状况被罚款时,他们就派丹尼斯去和社团管理委员会协调。如果委员会会长刚好是女性的话,罚款总会自动降低,或直接从记录上删去。丹尼斯的穿着与众不同(他喜欢穿Brooks Brothers的西装,Mephisto的鞋,搭配一成不变的公文包),说话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在日常对话里,他会用推论和动机之类的字眼)。在温彻斯特校园里,丹尼斯?佛拉赫提和大部分年轻人相比,的确很不一样,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逻辑使谬误毁灭,”威廉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丹尼斯的问题,“它是从一连串抽象的概念中,建构出有意义的归纳或演绎过程。”每个人都准备好要听长篇大论了。有的学生从背包里拿出记事本,打开笔盖准备抄写,但威廉斯又将话锋转回波丽身上。“逻辑会帮助你们找到她的下落。”他说。仿佛突然想起某件事,他补充说,“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我们有哪些线索?”携带笔记本电脑的女孩说。 “今晚将会把第一批资料电邮给你们。”教授回答。 不再有任何问题之后,威廉斯走出教室。他没说再见,一个字都没说便离开。之后,“逻辑与推理204”的学生聚集在空荡的走廊上,讨论这门课的诡异气氛。有些人因为今天没有具体的作业而开心不已。温彻斯特的学生称这类课为“营养学分”,只要去上课就能过关。正当大家在猜电子信箱里会有什么“线索”时,布莱恩?豪斯说,他不知道,也不在乎,反正他根本没打算看邮件。 携带笔记本电脑的那个女孩感到很痛苦。她走出大家围成的圈子,微热的电脑抱在胸前。她满脑子都是威廉斯教授,以及她该如何破解这门课的密码。不管是温彻斯特还是肯塔基州的天主教中学,每门课都有一个密码,一个等着破解的设计。可是在威廉斯的课堂上,她却似乎找不到显著的密码可解。或是她还没找到。这对她构成了十足的吸引力,因为在温彻斯特的这两年里,她终于首次面对一项真正的挑战——如何解开威廉斯这个人和他这门奇怪的课背后的谜。没有课表,没有课本,也没有笔记——没有显而易见的密码!这一切都很新奇,却也使她感到痛苦。当然,她不会跟任何人说。丹尼斯?佛拉赫提问她觉得这门课怎样时,她咕哝了一句若有似无的“还好”(她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这门课。他当然会喜欢,不是吗?)。不过,“还好”二字并不是她对威廉斯的真正想法。那天下午,当她走出研讨室时,她感觉到一股诡异的吸引力。
一首关于生活、苦与爱的曼妙幻想曲 一部向捷克大师赫拉巴尔的致敬之作 Esterházy:欧洲最著名的贵族作家 厄普代克 略萨 热情推荐 钟鸣 导读 艾斯特哈兹?彼得是我们时代最有趣、最具原创性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他的世界是口语的烟花幻术,往往语言本身就是故事……匈牙利文学的最前线。——《时代》周刊 某种程度讲,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也就是美国艺术家安狄?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钟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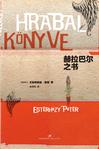
无
一个作家总是影响另一个作家 这在文学史上很常见 赫拉巴尔的书在中国读者里曾掀起过热潮 今天 就让我们去阅读和我们同样喜爱赫拉巴尔的匈牙利作家写的书吧
欧洲现代派文学的水平之高,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大多都是通过诸如诺贝尔文学奖来了解世界文学地图的。然而在此之外,至少很有一些水平不在此之下的作品与作家。彼得算得上其中之一。期待他最重要的作品《天堂的和谐》及《修订版》等中文版早日问世。
通过《一个女人》认识的作者,是强。感觉中国的作家没法比。希望能看到此作者更多的作品。
无意中看到 有人推荐的这本书~~ 本来以为还不错 可是看了一半 内容不是很了解~
这本书带点文学味~ 对于看惯了有主线的书 不太适应这本的理念~~
不能说这本书 不好看~~ 只是不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