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
2009年1月
重庆出版社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
185
高宗禹
无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瓦解》是一部非洲部落英雄的悲剧史诗。奥贡喀沃是尼日利亚伊博部落的重要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白人首次出现在视野里……由于他的傲慢和恐惧,他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部落。七年以后,他终于回到故乡,白人和天主教却在部落里扎了根,甚至他寄予厚望的长子也皈依了天主教,而他最后也含恨自缢。
钦努阿·阿契贝,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一直用英语写作。以尼日利亚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品,其中《瓦解》1958年发表后,即获得了布克奖,其他三部分别是1960年出版的《动荡》、1964年出版的《神箭》、1966年出版的《人民公仆》。阿契贝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目。英国《独立报》称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说“阿契贝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天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被英美等国的大学授予了二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瓦解》不但是阿契贝最著名的小说,也是非洲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品。自出版以来,全球售出了1000万册,被译成50种文字,让阿契贝成为非洲文坛有史以来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
第一部 在这九个村子里,甚至在这九个村子以外,奥贡喀沃都是很有名的。他的名声是靠他自己真本事得来的。当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时,就击败了猫子阿玛林兹,给他自己的村子带来了荣誉。阿玛林兹是个了不起的摔跤手,有七年之久,从乌姆奥菲亚到思拜诺,猫子阿玛林兹从来没有被打败过。因为他的背脊从没有触过地,所以才被叫做猫子。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场战斗中给奥贡喀沃打倒了。老人们异口同声说,自从他们这个小城镇的创立者同荒野中的妖魔一连战了七天七夜以来,这场战斗算是最猛烈的了。 鼓声咚咚,笛子呜呜,观众们都屏着气息。阿玛林兹是个机变百出的能手,奥贡喀沃也滑溜得像水里的鱼似的。他们的胳膊上、背脊上和大腿上的筋络浮现、肌肉暴凸,人们几乎听到它们绷紧得要开裂的声音。最后,奥贡喀沃击败了猫子。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约有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了,在这段时期里,奥贡喀沃的声名就像丛林里的野火遇到燥风似的愈来愈盛。他长得魁梧结实,两道浓眉毛和宽宽的鼻梁使他显出一副严肃的面貌。他出气很粗,据说当他睡觉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外面自己的茅屋里都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他走路的时候,脚后跟几乎不沾地面,仿佛脚底下装着弹簧,像是打算要把什么人扑倒似的。实际上他也是常常这样把人扑倒的。他有些口吃,每当他发脾气,不能及时说出话来的时候,他就用拳头。他对于不成材的男人是没有耐心的。他对于他的父亲就没有耐心。 他父亲的名字叫乌诺卡,去世已经十年了。他一辈子懒散,手里存不住钱,从来不知道为明天打算。如果有钱到他的手里--这种情况极少,他就立刻去买几瓢棕榈酒,挨家挨户去串门说笑。他常常说,每当看到死人的嘴巴时,他心里就想,一个人要是活着的时候不吃掉他的一份东西,那才愚蠢呢。当然,乌诺卡负了一身的债,他欠每个邻人的钱,从几个玛瑙贝一直到很大的数字。 他个子很高,但是很瘦,背有点驼。除了喝酒,或者吹笛子的时候,他总是愁眉苦脸,憔悴不堪的样子。他吹笛子吹得很好,他最快乐的时候,是每年收割以后的两三个月,那时候,村子里爱玩音乐的人都把挂在炉架上面的乐器取下来了。乌诺卡时常跟他们一起玩乐器,他的脸上闪着幸福恬静的光彩。有时候,别的村子也把乌诺卡的乐队和假面舞蹈队请去,留在他们那里,教他们乐曲。乌诺卡一伙人在这样的主人那里,有时要停留三四个集市之久,奏奏音乐,吃吃喝喝。乌诺卡热爱这种美酒佳肴的生活和温暖的友情,他也热爱一年中这个季节;雨季已经过去,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散发出耀眼的美丽。而且因为寒冷而干燥的风正从北方吹过来,天气也不太热。有些年,燥风吹得很厉害,空中弥漫着浓雾,女人和孩子都围坐在火堆旁取暖。乌诺卡热爱这一切,他也热爱那随着旱季归来的第一批老鹰,以及对老鹰唱欢迎歌的孩子们。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怎样到处游荡,去寻找碧空中自由翱翔的老鹰;只要发现一只老鹰,他就会全力歌唱,欢迎它从远途归来,问它有没有带着一两块布回到故乡。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还年轻。乌诺卡成年以后,是一事无成的。他很穷,他的妻子孩子勉勉强强有碗饭吃。因为他是个懒汉,人们总是讥笑他;因为他从不还债,人们都发誓不再借钱给他。可是乌诺卡却还常常借到钱,所以他债台高筑了。 有一天,一个名叫奥可瓦叶的邻人来看他。正好乌诺卡靠在他的茅屋里一张泥坑上吹笛子。他马上起身和奥可瓦叶握手,于是奥可瓦叶摊开他挟在腋下的羊皮,坐了下来。乌诺卡走进一间内室,随即又转回来,拿着一个小圆木盘子,里面盛着一个柯拉果①、一点胡椒和一块白石灰。 “我有柯拉,”他说着坐下来,把盘子递给客人。 “谢谢你。带来柯拉的人也带来了长生不老。可是我想应该由你来剖开它,”奥可瓦叶一面回答,一面把盘子递回去。 “不,这是给你的,真的,”他们这样推让了好一阵,最后乌诺卡接受了这份光荣。在他剖柯拉果的时候,奥可瓦叶拿起那块石灰,在地上划了几条道道,又把自己的大脚指头也涂白了。 乌诺卡一面切着柯拉果,一面向祖先祷告,祈求祖先赐予他们长寿和健康,保佑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吃完柯拉果,他们谈了很多事情,谈到淹没木薯的淫雨,谈到下次祭祖的盛典,谈到同恩拜诺村迫在眉睫的交锋。一谈到战争,乌诺卡就愁眉不展。他实在是个胆小鬼,见不得流血的惨状。所以他改换话题,谈到了音乐,就又容光焕发起来了。他仿佛在内心里听到了埃桂、乌都和奥惹奈①动人心弦和错综复杂的节奏,他还仿佛听到自己的笛子声穿插其间,为各种乐器点缀上一种如泣如诉的幽雅音调。整个效果是愉快活泼、生气勃勃的,可是当他的笛子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时候,人们如果单独去听他的笛子,就会感到其中蕴含的忧愁和悲伤。 奥可瓦叶也是个乐师。他奏奥惹奈。可是他却不像乌诺卡那样一事无成。他有一个装满木薯的大仓房,还有三个妻子。现在他正要取得伊德米里头衔,这是这地方的第三等称号。举行这个仪式是很花钱的,他正在设法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收回来。实际上,这就是他来看乌诺卡的原因。他清一清嗓子,开口说道: “谢谢你的柯拉果。你也许已经听到我不久就要得到新的头衔了吧?” 奥可瓦叶只把话说到这里,接下来的几句话是用一些成语格言说的。在伊博族中,谈话的技巧是很被重视的,成语格言不啻是棕榈油,可以用它把所说的话消化下去。奥可瓦叶是很会说话的,他说了很长的时间;先是旁敲侧击围着题目转,最后才把题目点出来。简单一句话,两年多前乌诺卡曾借了他二百个玛瑙贝,他是来要他偿还这笔债的。乌诺卡听懂了朋友的来意以后,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大声地笑了很长的时间,声音响亮得像奥惹奈一样,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客人不免吓了一跳,默默无言地坐着。最后,乌诺卡才一面笑着一面回答他。 “你看看那边墙上,”他指着对面抹着红土的发亮的土墙说,“你看见那些白灰线了吧;”奥可瓦叶看到几组短短的垂直线,是用石灰划的。一共有五组,最小的一组也有十条线。乌诺卡懂得怎样使人得到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停了一下,闻一闻鼻烟,大声地打了一阵喷嚏,然后继续说道:“那儿的每一组线都代表我欠某人的一笔债,每一道线代表一百个玛瑙贝。你瞧,我欠那个人一千个玛瑙贝,可是他并没有为这笔债在大清早就把我弄醒。我会还你的钱,但是今天不行。我们的长者说过,太阳先照到站着的人,然后再照到跪在他们下面的人。首先我得还我的大债。”他又闻了闻鼻烟,好像那就是在还他的大债似的。奥可瓦叶只得卷起羊皮,离开了。 乌诺卡去世的时候,他什么头衔也没有得到,只落得一身重债。他的儿子奥贡喀沃以他为耻辱,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幸好,人们是按照一个人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按照他父亲的价值来衡量人的。很显然,奥贡喀沃是配做大事情的。他还年轻,却已经是九个村远近闻名的最了不起的摔跤手。他是一个富裕的农民,有两个装满木薯的仓房,刚讨了第三房妻子。尤其难得的是,他已经得到了两个头衔,并且在两次氏族间的战斗中表现得无比的英勇。所以,虽然奥贡喀沃还很年轻,他已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了。在他的族人中间,年龄是被敬重的,但是事业却更受尊崇。诚如长者所说,一个孩子只要把手洗干净,他就可以同皇帝一道吃饭。奥贡喀沃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可以同皇帝和长者一道吃饭。所以,当邻村的人们为了避免战争和流血而把一个孩子送给乌姆奥菲亚村作牺牲时,也就由他来看管这个命运注定要遭难的孩子。这不幸的孩子名叫伊克美弗纳。 当奥贡喀沃听到村里报信人的奥惹奈穿破静止的夜空时,他刚刚吹熄了棕榈油灯,在竹榻上躺下。锽--锽--锽,中空的铁器发着震耳的响声。接着报信人开始喊话,喊完以后,又继续敲起他的奥惹奈。这就是他喊的话:明天一清早,乌姆奥菲亚所有的男人都到市场上集合。奥贡喀沃心里疑惑,究竟出了什么事;他确信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在报信人的声音中听到了隐含的悲剧意味,虽然声音愈来愈远,逐渐模糊了,他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纽如时报》 第一部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而不是像白人那样把非洲人描写成异类。 ——索因卡(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尼日利亚最著名的作家所写的全球阅读最广泛的一部小说。 ——亚马逊网络书店
阿契贝 布克奖获奖作品,全球狂销1000万册,40年后的今天仍盘踞亚马逊榜前50名,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说他在监狱度过漫长岁月时,“有《瓦解》做伴,白人监狱的高墙瓦解了。” 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不、惭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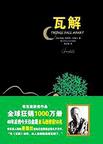
无
老师让写essay, 题目是
“It is a universal truth that people are indifferent towards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them”
要求是“Discuss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with reference to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但是我盯着题目看了半小时还不知从何入笔!!
过几天要交作业,急~~~~~~~~~~~~~~~~~~~~~~~~~~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告诉我写作的思路。。。
There are couples of things that can be listed to explain why the Igbo society fell apart by the conquer of the Westerners, such as the lack of knowing of the white people (Things Fall Apart, p.74, 138), the absence of the legal system that when they faced a problem, they dealt with it by asking God instead of using a law (Things Fall Apart, p.12),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n they fac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illness (Things Fall Apart, Chapter Three, Chapter Nine); All of these shortcoming made the Igbo society cannot follow the step of the new era, and cannot survive from the modernized Westerners.
Nevertheless, besides the campaigns from the white, the crucial causation that made the Igbo society fell apart was traditional customs it had had for a long time. In other word, the harmful parts of the customs of the Igbo society expedited the collapse of itself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Westerner’s military campaign.
However, it could be told that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helped to organized and governed the Igbo in some degree, dealing problems with negotiation instead of war (Things Fall Apart, p.12), and letting people live together peaceful (Things Fall Apart, p.32), for instance; yet, the influences of the customs that separated the Igbo and hurt their feelings are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uniting them together.
As one of the oldest members of the umunna mentioned that “I fear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 because you do not understand how strong is the bond of kinship. You do not know what it is to speak with one voice.” (Things Fall Apart, p.167) And the White people used the new religion to separate the Igbo people that if the traditional people wanted to fight with the followers of the White, they would fight with their own people. That may sound like what Okonkwo always said, the Igbo people did not unit together any more. However, there wa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Igbo society that the ones who said they should be united did the things that separated the Igbo society apart.
At the very forepart that the white men begun to send evangelists, the leaders of the clan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expand of the white man’s new Go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 new religion’s converts were some people without title that cannot be respected in the clans, so they did not care what they did (Things Fall Apart, p.143). And it also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 pregnant that had borne twins for four times which regarded as bad omen in the Igbo customs. When she became the convert of the white man’s religion, her husband and his family thought it was a good riddance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with her anymore (Things Fall Apart, p,151). And then, nearly all of the outcasts of the Igbo society join Christian when they saw the new religion accepted all the people whom seemed as the bad things in the Igbo’s traditional customs (Things Fall Apart, p.157).
According to all of these,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most of converts who joined Christian had no social position, could not be respected in the Igbo society. They cannot participated into any social decision, like Okonkwo’s wife was blamed when she asked about the little boy Ikemefuna (Things Fall Apart, p.14); their thinking and saying cannot be heard (Things Fall Apart, p.143); moreover, they were driven out from the church by the Igbo people only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position simply (Things Fall Apart, p.156). They were low-born person, separated by the Igbo people firstly and cannot fit themselves into the society anymore; therefore, when the new religion came and said that all of them were equal, and they would be loved, th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become converts not long after (Things Fall Apart, p.149).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of Igbo society were sternly cool and unmoved. Such as the tragedy of Ikemefuna, the boy was fancied by Umuofia people, had gotten along with them quite well for three years, and called Okonkwo father (Things Fall Apart, p.34, 52, 57); however, only because the boy was the reparation of that his father killed a Umuofia woman, he should be executed, on the basis of the Igbo customs, which hurt Okonkwo and his son Nwoye’s feelings sharply and deeply (Things Fall Apart, p.61-63).
Besides, deemed to be the typical symbol of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of Igbo society, what the activities and thinking Okonkwo had could sugges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gbo. As Okonkwo, the traditional Igbo was a society of “man” that always fascinated using fight to figure out all troubles, discriminated gentleness and showing any emotion frankly (Things Fall Apart, p.13, 28).
In the saying of the Uchendu, when people got grieves and miseries, they found sanctuary in their motherland (Things Fall Apart, p.134); howbeit, the people could not show any of their difficultness, nor get any pacification or comfort from their motherland, because those were regarded as shamefulness in Igbo society. There would be wounds in the Igbo people’s hearts that cannot heal, such as Nwoye whose childhood friend and brother executed by his father. Thus, when Nwoye heard the poetry of the new religion, he felt a relief in his soul, and was cured by the poetry (Things Fall Apart, p.147); That was why Nwoye was bewitched by it and became a convert shortly afterwards: the new religion of the white man was kind of medicine that can cover their lacerated hearts.
Obviously, it could not blame on those kinds of things that Igbo society did,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at time period;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owing to these harsh and unfair traditional customs which hurt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the Igbo society and the feelings of people, Westerners could conduct military campaigns to conquer Igbo society much more easily, on account of the cured effects that the new religion had on the Igbo society.
Things Fall Apart was published by Chinua Achebe in 1958s. This fiction write about the tribe called Ibo in Nigeria, Africa during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haracter Okonkwo was the leader of Ibo village, functioned in his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iction told a story that African people lived in the way which we weren’t familiar and misinterpret with, and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religions and missionaries. This novel also raised awareness of understanding African culture.
The title of the book is significance. My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fall apart is the tradition of the people in Umuofia breaks apart, then there isn’t any thing can relate them together.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shows the value of the Ibo culture, and it isn’t inferior at all compare with European culture. There is a patriarchal political system, the judicial system that is formally similar to Europeans. They believe in Animism, which is plants, objects and natural things such as the weather have living soul. They do also believe in the mask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their ancestors. In Chapter Ten, it writes “Then the egwugwu appeare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sent up a great shout and took to their heels. It was instinctive. A woman fled as soon as an egwugwu came in sight. And then, as on that day, nine of the greatest masked spirits in the clan came out together it was a terrifying spectacle.” P89. This strong belief effects everyone in Umuofia till the white people take place graduall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shows the encounter of two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es. A British missionary called Mr. Brown, builds a church in the evil forest and converts many Ibo people into Christians. It takes a amount of people from their own culture to another belief and thinking. This kind of strategy makes the culture falls apart, then the people won’t unit together to defend the conqueror. Finally, the nation will be invaded and lost. As Obierika said, “He has put a knife on the things that held us together and we have fallen apart.”P176.
After the Colonial powers enter to the Africa continent, the steps of changing is approach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Africans. The progress here cannot express neither a positive word nor a negative. In micro case, the three generations — Unoka, Okonkwo and Nwoye, make their own life well. Unoka is good at music, he enjoys drinking palm wine and hanging out with his friends. He may be a great musician. Okonkwo is the leader of the clan, powerful and famous. Nwoye i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lives in satisfaction of studying. How can’t we call this is progress? Progress is the process of getting better, or achieving something you want. If these three people all achieve their goals, how can we tell they are not progressive? In fact, just the opposite, the Europeans use rationalization to make the story of the world fits their ideas, to make the thing seems sensible to themselves. They break into the African culture with supercilious opinions. Speaking with excuse to let everybody knows the white people are superior, the Africans are primitive.
At the end of this novel, Okonkwo commits suicide because of their tradition is breaking apart. But what is tradition? Tradition is a belief, custom or way of doing that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mong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Today, I heard lots of people say this is a period of losing culture. But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tradition is made by people, and people love to look backward to the past. The way of people doing is changing over time, just because we hold a thought of progress, we want to be progressive. When people do not satisfy about the present life, then they will go look the past for seeking happiness. Some people are depressed about the custom their ancestor used to have, but they didn’t inherit. But please don’t forget, the tradition you have now will become precious and valuable in the future.
In fact, there isn’t any culture can be treat unequally, even 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destiny and ending I can’t tell which one is good which one is bad. However,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till dominates this world even today.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and recombining by it’s influence, but the process will be merely slow.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瓦解》。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论张颐武序、王雨来序,还是网友们的评论,都难免失于片面。相比之下,张颐武站在西方文明视角上对非洲传统的指指点点、对阿契贝内心纠结的臆测,甚至与我国“五四”的类比,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在序的最后,当我们看到“‘现代性’不是纯洁的东西”方欲击节时,马上又发现,他对现代性积极意义的描述显然中气不足。真相是:没有新生。
事实上,目前为止,还没有用汉语书写的人能够全面的看待,大拿们不能,我们更不能。从自身完整性来说,所有文明是完全平等的——尽管它们的阶段、属性和宿命各不相同——很难说哪个更美好哪个更丑恶,哪个更温暖哪个更残酷。即便消亡,也不能用其他的目光解剖。然而,西方文明是当今唯一的统治文明,我们也同样,生存方式、结构方式和价值理念同样被重构,只不过底蕴厚重的民族过程更加漫长。
读者全都过于注重后殖民主义和激烈的对抗,不同程度忽视了小说的文学性——仅仅是简短的赞赏。鲜活的人物丰富的表演比轰轰烈烈的进程更永恒,正由于此,我们的作家总是低上一筹。
Chinua Achebe brings us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life of the African people. His books read like guidebooks to the climate, landscape, customs, religion, politics and various other detailed aspects of African culture. His first book, Things Fall Apart, tells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Ibo (Igbo) people in Africa and how that collective life crumbles under the impac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For half of the book Things Fall Apart Achebe just patiently describes the pre-colonial life of the Umuofia villagers. Umuofia is often depicted as one individual: Achebe writes how Umuofia “was in a festival mood” when the Feast of the New Yam approaches (37; ch. 5), how it “had dozed in the noon-day haze” and “broke into life and activity” (54; ch. 7), and how it is “swallowed up in sleep and silence” (113; ch. 13), as if this primitive community has one united mind and soul. It does not have an absolute leader, but is guided by elders, grandees, and honorable men who have taken titles. 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y is Okonkwo, the great wrestler famous throughout the nine villages of Umuofia for his personal achievements. Strong and bellicose, Okonkwo represents the ancient veneration for prowess and virility. The indigenous life teems with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 violence, but things are nevertheless held together in harmony by shared beliefs, basically religious beliefs, upon which customs and laws are constructed. Even when one rule is violated, as is in Okonkwo’s case when he shoots a boy of the community accidentally, there are other rules to be follow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violation—Okonkwo has to flee his people and can only return after seven years. Nothing is out of place.
The binding force of religion is a mixture of inheritance from ancestors and maintenance by the villagers’ willing subscrip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ow the people are awed by the beliefs they themselves help to construct. Okonkwo, who fears the ghosts of his ancestors, disguises as one of the nine egwugwu, the ancestral spirits of the village, to serve their judicial function. Although his wives recognize his figure, they keep it to themselves. There are moments when the veil of religion is lifted and truth peeps from below, and people avert their faces. In this way the dignity of the Ibo religion is kept safe, and it in turn keeps the clan safe in a united whole.
It is when the white man, the British, comes, that things begin to fall apart. A clan, Abame, is wiped out by a group of armed white men in avenge of the scout who was killed by the clan people. After that the missionaries come and build their church. They are a milder group, yet their influence is not a bit less disastrous to the wholesome state of the clans, as Christianity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very basis and core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the Ibo religion, which is time and again exposed to be superstitious and powerless. As Christianity wins more and more local people to its side, the African community is more and more divided. It is exactly as Obierika puts it: “The white man … put a knife on the things that held us together and we have fallen apart” (162; ch. 20). Apart from the church the white men also establish a government among the African people and begin to exert their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Meanwhile a trading store is set up where people in Umuofia sell palm-oil and kernel at great prices.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British colonist activities always go together, and though in Things Fall Apart we mainly encounter the first two, we may expect the picture to expand in Achebe’s following novels, given that he arranges his books in a chronological sequence and that in real history the first phase of British colonization in Africa was soon followed by stages soaked with the blood of African forced labourers and slaves.
Achebe does not depict the African culture without exposing its evil. The murder of the boy Ikemefuna from another clan, who has been kept hostage under Okonkwo’s roof for years, and the custom of throwing twins away and let them die in the forest, are both dictated by the so-called Oracle in the village and both come as shocks to Nwoye, son of Okonkwo, and make him feel something snapping and giving away inside him (59-60; ch. 7). Those are the things which first crack an opening, through which the new religion, like a wedge, comes in and drives things apart. Nwoye’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signifies the great moment when father and son,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 of one people, fall apart. On the other hand, British colonialism is not depicted with undistinguished disapproval either. The malign impact killing off African tradition coexists with the benign action of saving twin babies’ lives. Mr. Brown, the first British missionary, represents the humanitarian branch of colonialism with his mercy and patience, and his successor, the Reverend James Smith, though far less sympathetic and more severe, is not reduced to void of admirable qual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 Christians and the village people comes more like a natural outgrowth. But the deep tone of regret is unmistakable. Achebe’s diction is simple, corresponding to the naive and straightforward mind of the African people, yet his voice reaches far. Harold Bloom calls this characteristic tonality “simplification through intensity”.* Achebe criticizes, but he does not rage. He approaches his theme with a calm mood, never appearing to be amazed even at the most outrageous moment, i. e. suicide of Okonkwo after killing the British head messenger and feeling deserted by his own people. Yet the intensity of feelings has already built up through the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a self-sufficient African community, so that when destructive impacts set in the reader receives the shock with full force. The whole book is significan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about the undisturbed life of the African people, the second the collective life crumbling under British colonialism.
* Bloom, Harold, “Introduction,” 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ed. Harold Bloom, NY: Infobase, 2010, 1.
瓦解-Things fall apart
这本书不厚,因为是我接触的第一本非洲文学作品,正式读之前仔细看了作者简介,书成于1958年,当时作者28岁,随后钦努阿•阿契贝就拿遍了除了诺奖以外的所有重大奖项。
看到一半的时候,对这本书最深的印象有两点:一是伊博族人说话时无时无刻不引用的各种古老的箴言;二是这本书让我想起白鹿原。
比如伊博族人男女两方为新娘的聘礼讨价还价时说:正如故事中的狗所说,“如果你让我吃点亏,我又让你吃点亏,这只是个游戏。”这么复杂、隐晦的说法意思是“一人让一步吧”;再比如,“什么时候你看见一只蛤蟆在大白天里跳出来,你就知道准是有什么东西要危害它的生命。”以此形容全镇人大清早都聚集在会场商量对付白人的行动。《瓦解》全书仿佛一个盛装打扮的伊博族人,赤裸着上身、披着熏黑的棕榈叶、光着赤脚,从脸上到腰身画满红白黑的花纹,黝黑闪亮的皮肤衬出黑白分明的大眼,惊慌失措地望着手捧圣经的掘基人。书中有很多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的书里不可能有的那种平静的细节描写,长者如何剖开柯拉果以示欢迎,妇女们如何烧开水怎么拔鸡毛,这一切把那个遥远的民族搬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奇怪的是,在我的想象中,他们都有着一副和我们一样的黄色的脸孔,甚至抽着大烟、喝着高梁酒,或是捧着一碗红薯粥转圈吹凉。他们跟我们好像,或许全世界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相似之处,人类所有文明的发源地,就是那一亩亩的田地、一座座村庄,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生来就崇拜的神,木头或是石头,哪有区别,它们保佑我们,惩罚我们,审判我们,给我们为人的原则、处事的标准,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信仰的浩劫,黑色长袍的传教士口里颂着上帝说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却剥夺了他们祖祖辈辈以来生活的自由,这一切不也曾发生在渭河平原上那个村庄吗?经过一场鲜血的洗礼后,新生的人们会忘记这伤痛,仿佛生活本该如此,而且从未这样美好。
【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
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e;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上帝也许是蟑螂,所以历史可以像蚯蚓,蜷曲着身体,盘旋着前进,总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Things fall apart,正如当下。
一、我们该信仰谁
在白人到来之前,村子里的人们信仰“地母”,这种近乎疯狂与可笑的信仰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根基和族群中不可违反的标准。当白人到来之后,一些人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信上帝,村子也因此而分裂。但不管怎样,村子里的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信仰是他们存在的标识。可维护传统信仰也好,拥护新宗教也罢,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在他们的信仰中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宁愿将自己献身于“信仰”这个词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禁忌和制度,也不肯想想自己的生命究竟有何价值。可是呢,我们又看到了奥贡喀沃,一个敢于在圣洁的日子里殴打妻子的英雄,这当然是他暴烈性格的体现,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自我信任与崇拜。他是氏族传统的捍卫者,但他其实只信仰他自己。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阿契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该信仰谁?传统还是新宗教?抑或只信仰自己?阿契贝自己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最终的答案也许需要历史的回答吧。
二、宗教大法官的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章节——《宗教大法官》。其中宗教大法官面对亲临人世的耶稣,向耶稣本人提出了质疑并阐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其实是魔鬼,因为只有“面包、神秘和奇迹”才能拯救人类,将人类团聚于一处。而耶稣是拒绝了这三者的。在《瓦解》中,我们恰好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例证。
基督教是如何赢得非洲村民的心的呢?先说“面包”。白人“设立了一个商店,棕榈油和棕榈仁第一次变成了高价的商品,大量的钱财流进了乌姆奥菲亚。”(P159)钱真是无往不利啊。试想你面前有一堆金子(或一顿猪肉),你可以拥有它们但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你会做一个叛徒吗?再说“神秘”,恩沃依埃在听到圣歌后感觉“不知怎地像是触到了他的心灵深处”,“圣歌浇在他苦旱的灵魂上,卸去了他心头的重负。”(P132)一股莫名的神秘力量征服了许多人,但他们却不知真正征服他们的并非圣歌之类,而是圣歌所带来的、凸显的、暗示的东西,而很多时候这东西就在他们自己的心中,他们听到了自己灵魂的力量却误以为引起这力量的宗教才是源头,于是便把自己交给了神父。最后说“奇迹”。布道者初来村子时受到排斥,被“分配”到凶森林中,大家都以为布道者们会die,但他们却一个也没死,这奇迹般的现象无疑对传统信仰下的村民们是种巨大冲击。
三、瓦解
白人和基督教的到来瓦解掉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村民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无疑具有族群精神上的意义。在第六章中,阿契贝生动地描绘了一场摔跤比赛。比赛的虽然是个人,但个人代表着村子的荣誉。“鼓声如狂,观众也同样心迷神醉。当两个年轻人跳着舞来到空地中央的时候,人们一齐挤向前去。棕榈叶也无法迫使他们后退。”(P45)族群的强大向心力在次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他者”到来之后,人们开始分化、内讧,最终杀害了自己的英雄。与此同时,古老的传统文化、伦理(P150)与信仰亦被瓦解。另一方面,依附于传统中的原始落后甚至丑陋可怖的一些因素也在新的冲击下瓦解了。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恩沃依埃,他之前听到弃婴的哭声,“觉得心里有一个东西崩断了”(P55),而在听到圣歌后他觉得似乎得到了解脱,他幼小的心灵“完全茫然了”(P132)。新的宗教给了他不同的人生体验与启示,瓦解了他脑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四、恶心与习俗
第七章中提到蝗灾来临,村民们却在夜晚跑出来抓蝗虫,并把它们放在瓦锅里烤熟,后又用棕榈油伴着吃。(P51)这在许多人看来应该是很恶心的事儿吧。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皮蛋刚刚被选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招致国人的一片声讨。其实,这是文化风俗差异所致,我们当然可以对此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至少我们应该尊重这种习俗,如果能拨开“恶心”的帷幕,去后台瞧瞧深处的原由或许会更有价值。
五、其它:P86—P89所讲的关于乌龟的故事很有趣,让我想起阿里斯托芬的《鸟》。
From the poem “The second coming” by Yeats, which Chinua Achebe quoted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ings Fall Apart”, the poet suggested that the coming of Jesus would never be the arrival of an era of peace and holy land but the era of chaos and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This is true in Achebe’s novel, for the arrival of the white had not only brought their religion but also colony therefore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ancient African society. By focusing on Okonkwo’s life and death, Achebe presented the imagines of the African culture and how they had fallen apart. The reason why things fell apart, though not mentioned by the author in the novel, was caused by series of conflict between Okonkwo’s belief and what he had gone through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death of Oknokwo. His death also reflec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Umuofia and the other clans in Africa.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Chinese famous historian Ray Huang had posted, every significant event in history is caused by small events. So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Umuofia and the African society. By studying Okonkwo’s personality and his life, we may find the signs of the declining African society.
Okonkwo, despite his weak father Unoka, was a strong and respectable man who possessed a high reputation among the nine village of Umuofia. However, great as he was, “his whole life was dominated by fear, the fear of failure and of weakness… It was the fear of himself, lest he should be found to resemble his father.” (P. 13) Driven by such belief, Oknokwo was determined to become the strongest man in this land. He regarded any negative emotion such as grief and despair as weak of which he tried so hard in his life to avoid. But such emotion is such a humanity that none could avoid. When Oknokwo killed the boy Ikemefuna, he found himself falling into great depression. “He did not sleep at night. He tried not to think about Ikemefuna, but the more he tried the more he thought about him.” (P. 63)
This was the first crack of Oknokwo’s belief, and with time passed, the crack became bigger and bigger, his belief finally fell into pieces. Before reaching the final conclusion,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to discuss.
Achebe also used Oknokwo as a reference to the other people of the clan. Contrast to Oknokwo, the spirit of striving had been lost among young people. Young people like Oknokwo his own son Nwoye, unlike his father, had no such strong will, reflects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the clan. When the British came to their land, there’s no wonder why they did not fight back the invaders.
Followed by the fading of the spirit came the shaking of religious belief. Religion, what Marx called the “opium of people” ,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Africa society. Like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t ruled many aspects of human’s life. It also has the power arousing the passion of people no matter to construction or war. But when the religious belief became fading and destroyed,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society will also decline and destroyed.
As a pious man who deeply believed in his chi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clan, Oknokwo had faith in the Ibo proverb that “when a men say yes his chi also says yes”. But when Oknokwo’s was exiled from Umuofia, he doubted that “The saying of the elders was not true-that if a man said yes his chi also affirmed. Here was a man whose chi said nay despite his own affirmation.” (P.131) Such doubt can be inferred earlier in the novel when the oracle took Oknokwo’s daughter Ezinma in a dark night, he followed them until making sure that Ezinma was safe. Such behavior though was out of love to his daughter, also had reflected his mistrust to the religion. The exile had aggravated such mistru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Oknokwo began to think about whether his chi really exist, and if it exist, “Why should a man suffer so grievously for an offense he had committed inadvertently?” (P.125) If chi had failed him this time, what about the previous movement he had done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god? Was it right or wrong? Or maybe it’s another trick made by the god. “He remembered his wife’s twin children, whom he had thrown away. What crime had they commited?” (P. 125)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rack of Oknokwo’s belief became bigger and bigger, the British came and convert numbers of clan members into Christian. The next step of the British was to set up a government that ruled the land. With many Christians among the clan and others that had no ideas of colonial, this was no hard to accomplish. When they finally found out that they had lost their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it was too late. The spirit of the clan had also fallen apart along with their freedom. Oknokwo tried to arouse the people,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y were too numb to fight their independence back. “He knew that Umuofia would not go to war.” (P. 205) This was the last straw on Oknokwo’s back; the great Oknokwo was tear into pieces.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found his body hanging on a tree.
The death of Oknokwo indicates the fall of the clan. Umuofia,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clan on this land no longer exists. The story was taken place in the 19th century, a year that the world was in great conflicts whil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urgent in expanding their colonies. What Achebe had told us is such an insignificant story that none historian would pay attention to. However, it’s always these insignificant stories that tell us why and how things fall apart.
《分崩离析》(Things Fall Apart)是尼日利亚作家齐鲁瓦•阿契比(Chinua Achebe)的力作。讲述了非洲土著欧康寇(Okonkwo)的一生故事。欧康寇生性要强,一心希望出人头地,挣一份足以自傲的家业。自己的父亲好吃懒散,母亲终日忙碌,使他从小就对懒惰深恶痛绝。成年以后,欧康寇勤奋劳作,终于开创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家业:一所大宅、三个老婆、充足的粮食。他惟劳动为先,认为勤奋致富是天经地义的。在本族人依宙杜(Ezeudu)的葬礼上,欧康寇错手杀死了死者16岁的儿子,虽然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但是部族的习俗却容他躲避到母亲的亲属那里,放逐7年,方可回乡。欧康寇平静地接受了部族习俗的安排。7年后,他雄心勃勃地返回故里,满心希望大干一场,正待他的生活蒸蒸日上之际,一切却随着白人殖民者的进入而渐渐瓦解。长子纳沃依(Nwoye)不满父亲强悍的家长作风,在白人传教士那里找到安慰。欧康寇对此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在一次与教会的冲突中,欧康寇杀死一名传教士,他自知白人不会善罢甘休,势必牵连全村的乡邻,最终悬梁自尽。
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对比了土著与白人的价值观,并且用土著的眼光去评判白人传教士/殖民者的“文明之风”。土著和白人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土著的世界并非白人所宣扬的一味野蛮无知,他们的伦理道德丝毫不逊于白人所推崇的价值观,即《圣经》里宣扬的那一套,欧康寇误杀人子,放逐异乡就是最好的佐证。相形之下,白人的阴谋诡计(诱捕部族头人),对欧康寇杀人举动表现的睚眦必报,都为白人所宣扬的上帝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人不禁要问:究竟上帝讲的是不是对的?为什么他的子民会说一套、做一套?
小说手法传统,表现非洲土著的真实生活,用意是拨开长期以来笼罩在其身上的迷雾,为欧洲人心目中“黑暗的中心”点燃一盏明灯,让非洲土著从沉默走向言说、从隐形走向真实。在此意义上,阿契比的《分崩离析》可谓用心良苦。可是,这也无疑暴露了小说急于向欧洲人证明自己的企图。或可谓,小说的隐含读者是否是白人?我无法深究这些疑问,阅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有时,不求甚解比之分毫必较更能保全阅读的乐趣。若然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还觅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态?
最近开始由日本慢慢过渡到黒非洲,这本书真让我喜欢 :
1.先说英雄:《瓦解》的价值在我看来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从未消逝的一种人类尊严。也许古老的生活方式连同传说中的英雄都消逝了,但当我看到枯树丛中挂着主人公的尸体时,我觉得他赢了,以一种谁也无法战胜的方式巧妙地把一种东西永远的妥当的安放在了这个世界上,安放在我们心的一个角落,这是一种尊严一种荣誉一种智慧一种神旨一种永不会逝去的东西。我坚信只要是人类的宝藏就永远不会逝去,而《瓦解》只是把这表现出来罢了。
2.再说标题,究竟瓦解的是什么?瓦解表面上看是传统的瓦解、部落的瓦解、英雄的瓦解、男子汉气概的瓦解,但我觉得实际上瓦解只是作为一种现象,一个名词诗意的被作者选择出来放在这里罢了,我更倾向于把瓦解看成是一种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对历史进程的描述,这样一种黑非洲神秘主义的小说氛围中,实际上什么什么也没有瓦解,英雄死了,但基于那片土地的神秘力量却愈发浓厚了,这不是人可以随意涂改的。如果人类曾有过一种精神至高无上,那就得承认她无法被撼动。作者在篇尾借行政长官之手把这一点被客观的记叙下来(《下尼日尔地区原始氏族的平定》)一方面含有讽刺意味,一方面亦可看做是作者的娓娓道来。
3.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卡夫卡在《瓦解》中的影子,在小说快结尾的地方主人公砍下差吏头颅的那个片段,简直就是尼日尔版卡夫卡式黑色幽默。我曾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看到日本版的卡夫卡,现在又看到了尼日尔特色版的,真是奇妙啊。同样的尴尬、苦涩、无奈、荒诞,但不同的是染上了古典非洲特色,正如前言中所说:“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宛如非洲木刻,即便是卡夫卡的法庭也无法消退这神秘的氛围,这土地上的气味。
“我怎么能认识你呢?祖先,你完全不是我能认识的。”从不听从别人的决定的乌佐乌鲁在公共典礼上面对祖先灵魂的问话这样回答。
祖先的灵魂当然是不会真实地参加公共典礼的。在祖先灵魂的面具后面是作为执行氏族法律的九个祖先灵魂的代表者,他们是氏族里最有地位的人群。奥贡喀沃在祖先灵魂的面具后面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氏族里的地位,但是他能认识自己所代表的祖先吗?
或者他有没有在某个时候问过同样的问题。
如果有,奥贡喀沃一定会肯定地回答。
奥贡喀沃的父亲游手好闲,债台高筑。不但没能留有任何可供奥贡喀沃继承的财富,反而全靠奥贡喀沃供养。当奥贡喀沃第一年的耕作遇到天灾变成悲惨的年景时,重病的父亲对他说“不要失望。我知道你不会失望。你有一颗勇敢而骄傲的心。一颗骄傲的心能够经受一场普遍的失败,因为这样的失败刺痛不了他的骄傲。当一个人独自遭到失败,那是更加痛苦更加难以忍受的。”在自杀前奥贡喀沃如果能回忆起这段话,他也许会改变对父亲的看法。但是,他对父亲没有耐心,甚至是鄙视的。尽管父亲也算是祖先的一部分,奥贡喀沃宁可不提起他。
奥贡喀沃在摔交比赛中赢得了名声,通过勤劳的木薯种植积累了财富,从而在氏族中获得了地位。他烦恼的是他的儿子恩沃依埃不像他,不能按照他的路走下去成为家族的光荣。而儿子也并没有给他带来惊喜,恩沃依埃在白人到来以后皈依了基督教。
奥贡喀沃为家族失去了儿子而恼怒,最后,他“看清了整个问题。生气勃勃的火却会产生无用的冷灰。”
在奥贡喀沃眼里,自己是生气勃勃的火而儿子是无用的冷灰。如果真是这样,奥贡喀沃的父亲就是点不起火的木柴。奥贡喀沃认定生气勃勃的火才是生存的理由,然而谁能断定木柴、火焰、灰烬哪一样才是祖先真正的道路?
恩沃依埃,和他的父亲奥贡喀沃一样,“离开他的父亲,他是很高兴的。”他也和他的父亲奥贡喀沃一样,继续执着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往后他要回去看他的母亲和兄弟姊妹,劝他们改信新教。”
奥贡喀沃祖孙三代的命运已经完全昭示了氏族的历史。奥贡喀沃的父亲过着淳朴快乐的生活,与永恒的时间达成共谋;恩沃依埃不能容忍暴力和不公正,向外邦的神寻求未来;奥贡喀沃是这个氏族的英雄,他所做的也仅仅像失去了孩子的鸡妈妈喊叫而已,让夺取了小鸡的老鹰放心用餐,氏族里的故事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促使它瓦解的还不止这些。
在奥贡喀沃的氏族里,女人无疑是地位卑微的。奥贡喀沃暴烈的性格使他对妻子丝毫不手软。祖先正是这样确定男女的界限。“关于氏族中最有权力最神秘的祖先崇拜,从来没有哪个妇女敢提出什么问题。”可是,当奥贡喀沃枪走火杀人,不得不避祸他乡,来到母亲家乡的时候,也正是祖先的声音告诉他“一个男人在事业顺利、生活美好的时候,是属于他父亲的家乡的。但是,要是他有了忧愁和痛苦,他就会在母亲的家乡找到安慰。你的母亲在这里庇护你。”还是对女人和生育有关的事情的类似态度,使得神和祖先的一些命令和习俗显得盲目并且荒唐。氏族和祖先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保持男人的权威,固定氏族内部的最基本的等级划分。
奥贡喀沃和氏族里的人们对氏族外面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以为白人都是麻风病人。以为市场的繁荣只是一种很凶的巫药所造成的结果。
氏族里的祖先和神经常作出不近情理的决定。邻村为了避免战争送来牺牲的孩子伊克美弗纳寄养在奥贡喀沃家,几年后已经融入这个家庭成为其中一员。就在这个时候,神下令杀死他。奥贡喀沃本不想亲自动手,但是为了遵照神的意旨,奥贡喀沃在前面的人失手后孩子跑向他求救的时候拔出了砍刀。
一直以来,奥贡喀沃只是以为他完全认识并且能够代表那个他希望中的祖先。
那个男人的祖先。那个力量的祖先。那个从祖先的时代到他的时代一成不变的,通过不辞辛劳就可以功成名就的祖先。那个在附近村寨和凶森林发号施令的祖先。那个经常作出不近情理甚至盲目的决定的祖先。
他没有意识到,盲目的正是祖先的面具和面具后面自以为带上祖先的面具就可以作出祖先的决定的人们。
那些活着的人们。
“活人的乡土和祖先的国土相去并不远。彼此之间原有来往,尤其在节日,或是老人去世的时候,因为老人是最接近祖先的。一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要经过一连串过渡的仪式,这些仪式使他和他的祖先愈来愈接近。”
《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是钦努阿•阿契贝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之一。《瓦解》讲述了非洲氏族村落的历史和白人到来后发生的巨大变迁乃至瓦解的故事。另外三部展现尼日利亚社会变迁的作品是《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
《瓦解》整部书没有太多血腥的味道,却把非洲氏族社会的瓦解写得肃穆,沉重,仿佛如血的残阳,没落是遮挽不住的,却难免令人心痛。描绘白人到来之前的氏族生活,既怡然自得又风雨欲来,轻松的笔调刻画出生命和竞争的残酷。阿契贝并没有过多地控诉,而是希望更好地反思。
198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的评论说《瓦解》是“第一部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而不是像白人那样把非洲人描写成异类。”
我认为这是对《瓦解》最好的评价。阿契贝讲述的故事轻快流畅,可以加上一个巴尔扎克式的副标题,非洲氏族的风俗研究。
氏族的神死了,祖先被禁闭在面具当中。
前所未遇的竞争瓦解了一切。
权威不是恒久的,它不可能以一种不变的方式永久保存。
奥贡喀沃本身就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喜欢胜利的竞争者。他在氏族的摔交比赛和木薯生产中胜出。但是在另一场比赛中他失败了。
他甚至不知道在那场比赛里胜利是什么。
他只知道那不是他一个人独自遭到的失败,而是一场普遍的失败。之所以他那勇敢而骄傲的心都难以忍受这失败的刺痛,因为他知道,这次,神和祖先也没能免于失败。
L.T./文
迄今为止,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外,钦努阿·阿契贝几乎获得过国际上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而长篇小说《瓦解》,则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在国际上,这位尼日利亚的作家倍受瞩目,被称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至于他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尼日利亚的《每日太阳报》曾经有些自负地认为: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成就理当成为读者选择他作品的砝码之一。W·B·叶芝在《基督重临》中如此写道:“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一切都瓦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这几句诗写出了奥贡喀沃的心声。这个非洲部落里的英雄,敬仰着万物,在一个没有法制的部落里,一切都听凭于神的旨意。的确,《瓦解》就是一个鬼魅重重的小说。在一个信仰万物有灵的部落里,现代文明的清规戒律显然是充斥着虚伪的荒唐。《瓦解》可以满足猎奇心强烈的读者,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地带着现代文明的有色眼镜去看待非洲部落里伊博族人面对世事的态度,我们可能会感觉毛骨悚然。而事实上,这一切的残忍都来自他们对神的敬仰:奥贡喀沃曾按照氏族的规矩,亲手砍死自己的养子。
身为伊博族的阿契贝,虽然在书中以一种诗意的笔调大量描写伊博族的习俗,但他对这些习俗持怀疑态度。从“瓦解”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小说的脉络,这是一部描写非洲原始部落走向毁灭的小说。贯穿期间的英雄奥贡喀沃,也在一步步地走向末路。整个小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奥贡喀沃的发家史。这个父辈劣迹斑斑的人,靠着勤劳和英勇成为了执行氏族法律的九个祖宗灵魂之一;也就是这样一个灵魂式的人物,在一次葬礼上枪走了火,打死了死者的儿子。在氏族的法律中,这得被放逐异乡七年之久。这是奥贡喀沃命运的转折点,尽管他在母亲的故乡依然受到了母亲亲戚的爱戴。在这之间的另一个转折是:英国殃民者开始入侵伊博人生活的部落——先是以宗教的形式。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写了基督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之间的争斗。而后者失败了。这种失败表现在奥贡喀沃身上是:连他的儿子也成了教徒。
一切现代文明的东西,在非洲部落上展开。沉积多年原始习俗催枯拉朽,作为部落法制的维护者,奥贡喀沃将个人命运融为一体,纠结在一起,最终在杀死了一个教会差吏后,自缢身亡。这是英雄主义的悲剧体现。这也是《瓦解》的经典之处,除了时代变迁的主题外,还塑造了奥贡喀沃这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则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与阿斯图利亚斯的《玉米人》一样,前半部分与得行云流水,越到后来就显得生涩、呆板。非洲部落的陋习得到充分展示后,基督教渗入后社会似乎在走向文明,这不是非洲近现代的历史吧?不明白主人公为何崩溃?看来后半部秩序的瓦解写得没有说服力。
我觉得阿切比在写作时确实存在困惑,一方面,与欧洲文明相比,他从心里不认同貌似我国尧舜时代的非洲落后部落生活,但另一方面,非洲人身份的他又不能背弃血缘所在的立场,以免遭到“左愤”们的围攻。他在全盘西化与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中徘徊,抓不准出路,弄得里外不是人。
这也是阿切比自身的崩溃。
作者阿契贝是非洲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实我们一直对非洲文学关注得不多,库切、索因卡,加上阿契贝是被西方文学界关注得比较多的人物。就像人们对东方文学的误读一样,非洲在我们心目中首先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然后再被开启。阿契贝的《瓦解》同样先满足了我们猎奇的先愿,然后再给了我狠狠一击。殖民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救世主,并认为是自己给世界各地带去了文明,而阿契贝告诉我们,非洲固有的文明虽然原始,却是发自人们自身的血性之中的。即使如此,它最终会被瓦解,在两种文明博弈的力量中间,有个叫奥贡卡沃的勇士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我们所倡导的文明、礼仪和温和被他一再地抗拒,尽管如此,他的灵魂深处却依然存在犹疑:当他面临亲情的柔软时和儿子的背叛时,这种抗拒因为犹疑而变得更加剧烈。最后这位“西西弗斯”一样的末路英雄最终自缢在自己院子里——当西方人自以为将文明撒播给这些“野蛮人”时,这位野蛮人为了保存“野蛮的文明”而选择了死亡。要知道,这比活下去更需要勇气,因为自杀在“野蛮人”看来是最可耻的方式。
阿契贝的叙述非常平静,他是一名基督徒,和主人公奥贡卡沃的长子保持着同样的信仰,他的祖上一定也面临着同样的撞击。我们总不可避免地去寻根问祖,在苍茫的物是人非之间寻求所谓的答案。阿契贝不是这样子的,他或许预见到一切问题都是无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小说的风俗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然而,为了更深刻地体味它的文学价值,我打算闲暇了去图书馆找本原版来读。
印量的多少与被译介的广泛程度并不能作为一部作品被称为“经典”的充分条件,我比较倾向于卡尔维诺对“经典”的描述:
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他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他们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他们的人,他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些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他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的作品;但是那些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能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以上十四种描述可以简要地概括成这样几个关键词——历史性、丰富性、亲切性、新鲜性、耐读性、影响性、独特性、独立性。在我看来,卡氏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谓之经典的当属《我们的祖先》,其他的尚需检验。
如果以上述标准看来,本书的确满足一些条件,如历史性、丰富性、亲切性、独特性。但是,作为一本“经典”,它当然还要满足“耐读性”、“新鲜性”、“影响性”与“独立性”。以我个人阅读体验来说,这样的小说读一遍就可以弃之一旁,它太不耐读了,下次阅读也不会带来新鲜的体验;就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即便这是非洲人自己用英文写作的关于本族的历史作品,即便它有着1100万的印量和被译成50多种语言,这不能决定它成为“经典”。它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它的写作本身是独立的吗?与其说它是“经典”,倒不如说它是本满足外界对非洲猎奇的一部畅销书而已。作者本人的身份在当地人或有正常思维的人看来,不过是背叛了传统习俗而信仰基督教的异教者。他在纽约过着他的逍遥日子,享受着“世界声誉”,还“作秀”地关心着自己的“祖国”,并拒绝来自“祖国”的褒奖,这一切真让我恶心!拿热脸贴冷屁股的尼日利亚政府更加不要脸,更加值得鄙视!人家已经不是你的族类了,还去凑什么热闹!
文学的阶级性与革命性是在很多人看来是过时而可笑的,太多的人将文学看成是自己情感的附属品,文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和电影与音乐一样的东西,而且,某种小众的东西更成为了他们炫耀的资本……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对此种相似的堕落做过详尽的分析与批驳,尽管保守,却充满教益。这是一本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因为它来源于《理想国》,注重现实,对后世亦有启发意义。相比之下,阿切比的《崩溃》简直不值一提。作者本身作为一个叛国的人,自然写不出彻底革命的作品,所以,他的主人公只能在英雄行为之后选择自杀,不能完成领导某种革命的任务。结尾处的传教士暗揣着以此为由头写篇小说,这样的结尾让人哭笑不得。作者的立场在哪里?前半部分对于传统习俗的留恋出于怎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外人对非洲的好奇?如果历史不能成为后进者行动的目标与动力,历史与习俗有何作用?身为一个小说家,当然要保持独立性,像阿切比这样的作家“残喘”于祖国之外,骨头都是软的,这样荏弱的作品若可称为“经典”,真是天大的笑话!而一些中国读者居然也在“皇帝的新装”背后叫好,岂不可笑可笑?这样一部不痛不痒的作品,充其量供批判用。
很好读但绝不简单的一本书。读的是一部非洲部落史诗,经历的是一场深入黑非洲内部的,伴着神秘低沉如心跳般鼓点的大梦。不仅仅是内容,它的如非洲传说般的简朴语言,它的如非洲木雕般的清晰有力的线条,以及绝对高超而毫不做作的叙事技巧,都是只有一个真正的非洲人才有可能做到的。
“在他面前,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等感到不安和惭愧。”这句宣传语尽管有点滑稽,还是能说明问题的。索因卡应该不错。库切小说看过一些,确实不如阿契贝。
用整一个下午看完了《瓦解》,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中文译版也就十四万多字,可好作品不在乎部头有多巨大,简练如此的,我完全要把它归为能够涤荡内心,让思维纵深的小说之列。 近现代的非洲大陆是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什么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什么人类社会发展简史的展窗…在资本主义日嚣尘上人类欲望无限膨胀的潮流下,就注定了被鲜血浇灌的下场! 小说的主线,叙述的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领袖辉煌又仓皇,最后近乎是殉葬的一生,他的命运走向正是整个氏族,乃至整个非洲部落文明的历史走向,那就是被殖民者的武力以及他们带来的文化暴力侵蚀吞噬,逐步瓦解,消失不见。小说中没有直接触及入侵与反抗这种政治或是军事问题,而是把宗教信仰放在了矛盾对撞的中心地带,并且用的语言也是平和的沉静的,而非暴风骤雨顿挫激进。我想,这和作者本人对于暴力反抗方式的取舍有关,也符合古老氏族代代相传的生存信念……那些最朴实浅显的道理,却有着最震撼人心的力量,蕴藏着最精辟的人生智慧!“鸟儿为什么不息而飞,因为猎人们射而必中”;“我永远不会身在河边,却还用唾沫洗手”;“我们觉得他们愚蠢,只是我们还不了解,他们只是不属于这里,来错了地方”;“谚语让我们说的话更利于消化”;“男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属于他的父亲的氏族的,当他落寞消沉时却只能在母亲的庇护下哭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有形的暴力可以防备,思想信念的入侵则销骨于无声。这种无形的暴力更危险更可怕。我不认为历史潮流的洗刷有错,去伪存真,滤去糟粕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可是,多站在人文关怀的角度考虑,这些以自己的意志去刻意改变他人生活模式,更替其价值观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更残忍更强大的暴力吗?殖民者们扮演的正是这一部分人类的角色。 主人公是崇尚力量的,他有自己一套男人的坚守,从不惧怕敌人也不屈从于妖魔神灵,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恐惧和软弱,最瞧不起是懒惰,即使心里也会有欢喜伤悲,但绝对不会在脸上泄露半点神色……感叹于作者的描述,简短却极富画面感,阅读的时候仿佛字不是映入眼帘,而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敲击内心。 有时间还会再读一遍,细节之处还可把玩几番。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不得不说,这书远远不及阿来的《尘埃落定》写得好看。我甚至在想,这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是不是全世界人民都同情作家是非洲人的缘故。因其大家对非洲生活(特质该作者所在国度的生活)的不了解,从而带着猎奇的心理阅读该书。猎奇的人多了,这书的影响力也就大了起来。
当然,这书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不至于高到这般。
五年前,我曾经在巴西利亚大学跟一个靠行贿混进访问教师公寓居住的尼日利亚留学生做了一段时间的室友,这是我第一次跟黑非洲兄弟走得这么近。这哥们是尼日利亚三大民族(伊博、豪塞、优鲁巴)中的优鲁巴人,虽是学生,但从不见去上课,终日在看电视和无来由的手舞足蹈中愉快地度过。有一天我提醒他,好歹要看看书,不然对大西洋那边的父老乡亲没法交代,这哥们愣了一会儿,问我:“钦努阿•阿契贝你读过么?”我摇摇头。他乐了,“你还教文学的呢,俺们黑非洲最大牌的作家你都没读过,还好意思劝我读书?”我掩面而逃。
去年秋天,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时候,再度和黑非洲兄弟并肩与房东作战。巧的是,和我合住的俩黑非洲作家里,跟我混得最近乎的又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和钦努阿•阿契贝同属伊博族的青年作家乌切。乌切入住没多久就让俺们感受到了伊博族口头文学的光荣传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乌切同学身穿宽大鲜艳的伊博族盛装,像一个黑非洲氏族里的说书人一样端坐在房东的门廊上,左手一根鸡腿,右手一瓶啤酒,用一口挑战听力极限的伊博英语向坐在四周的各国作家讲述尼日利亚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漫长而混乱的历史,讲到比夫拉战争之后被打败的伊博人如何向世界各地流亡并且顽强不屈地在异乡生根发芽以至于被称为“黑非洲犹太人”的时候,乌切啃光了鸡腿上的最后一片肉,说:“想要更多地了解伊博人、了解尼日利亚、了解黑非洲吗?请去看我们伊博族的文学头人钦努阿•阿契贝的书……”
事实上,钦努阿•阿契贝远非伊博族的文学头人,而是整个黑非洲的现代文学之父,并且还不是那种死在教科书上的大师,而是那种时时刻刻能让黑非洲的文学后进们感到一种强悍支撑力的、大地一般坚实而靠谱的先辈。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里的一系列讨论会上,无论白人、黄种人如何花样翻新地搬出德里达德勒兹齐泽克,但凡有黑非洲作家发言,无论他(她)是来自尼日利亚还是喀麦隆、南非还是乌干达,都会齐刷刷地援引钦努阿•阿契贝的文字,尤其是他1975年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所做的那个堪称后殖民主义批评标志性文献的演讲《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在这篇演讲中,阿契贝认为在被奉为经典的《黑暗的心》中,黑非洲完全是作为欧洲和文明社会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康拉德拒绝给予非洲人以人类的表达方式,甚至剥夺了他们的语言。阿契贝认定康拉德是散布“恐黑症”的恶毒的种族主义者,他应当被永远地从文学大师的行列中清除出去。
国内治文学的学生如果仅仅从选进了各种后殖民主义理论选本的这篇演讲去了解阿契贝而不去读他的小说的话,很容易把他窄化理解成一个“老愤黑”。就算这篇措辞激烈的演讲有点“愤黑”的意思,阿契贝的“愤”也是建立在密集而卓越的文本实践的基础上的。就拿他发表于1959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瓦解》来说,阿契贝旨在通过他的小说技艺扑灭这样一个传播甚广的误解:殖民者到来之前的黑非洲是野蛮的、原始的、远离文明的。阿契贝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志”式的样本:前殖民时代一个虚构的伊博村落乌姆奥菲亚,这个村落在被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渗透之前,自有一套令个体和氏族都过得安详富足的社会运转模式。小说以优雅、简洁的行文结合丰富的伊博口头文学传统(特别是俗谚和匪夷所思的比喻),复现了以绰号为“一团烈焰”的末代勇士奥贡喀沃的家庭为中心的万花筒一般的伊博族日常生活,从如何食用柯拉果到如何种植木薯,从玛瑙贝的使用到“琵琶鬼”的祛除,从婚礼、葬礼到由“祖先幽灵”主持的氏族法庭……套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书名《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瓦解》的第一部分完全可以叫做《英伦入侵前夜的伊博日常生活》。
然而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单纯的民族志样本,是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情感纠结和耐人寻味的意义指向。在记叙基督教的渗透导致的文化冲突、奥贡喀沃像飞蛾扑火一般反抗入侵以致身亡的过程中,阿契贝的笔端被一种复杂的态度所笼罩:一方面,他写出了奥贡喀沃的悲壮,这种被平静所抑制的悲壮及其所包含的宿命感,颇似梅尔•吉布森描述西班牙人到来前印第安土著英雄的电影《启示》和山田洋次挽留幕府终结时期最后一代武士们平凡中的操守的“武士三部曲”糅合在一起的加强版;另一方面,在奥贡喀沃的强力与其他氏族成员的软弱、顺应所形成的反差中,阿契贝也多少暗示了在他的视野里,传统的伊博族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瓦解,和本土社会结构内部的虚弱也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瓦解》的书名来自叶芝的名篇《基督重临》中的诗句:“一切都瓦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叶芝原本在里面嵌入的是他个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末世论预感,阿契贝借用来喟叹传统的黑非洲土著社会形态的瓦解。时过境迁,在《瓦解》出版50年后再重新审视这部已经成为英语世界至高经典的作品,我们可以说,这书名中的“瓦解”亦是一种预言,预言了康拉德《黑暗的心》所维系的那个“恐黑症”观念体系在今日的瓦解。
两天里面看完了这本薄薄的小说……老实说这书写的有点闷闷的...My primary motivation was just because it's on a list of recommended reading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觉得写得挺一般 不过表现出那种生活中所有的事情 what the main character holds most valuable, gradually fall apart 读完有点挺凄凉的感觉 恩 语言描写什么的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作品~
在多大的小书店里,看见一个女孩子胳膊弯里夹着《THINGS FALL APART》,我心里对她顿生好感。女孩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十分苗条,脸色是瓷器的白,黑发象瀑布一样光滑润泽,松松地挽了搭在肩上。对于这样天生细致窈窕的女子,我心中不知道有多少艳羡。看她袅袅婷婷地在书架前浏览,不禁上前用中文招呼:“你也选殖民与后殖民写作吗?”她惊了下:“什么?”我指指她手里的书,她恍然明白,“这是社会学要求读的。”原来这样。是我井底之蛙了。
《THINGS FALL APART》是尼日利亚人CHINUA ACHEBE的作品,成书于1959年,被认为是第一部非洲本土黑人用英语写作而引起世界范围关注的小说。
有时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白的,比如我们爱的那人究竟爱不爱我,比如是不是在哪里总有个人被他默默牵挂,在这里,是一个尼日利亚人,用陌生的英语写字,故事说的是黑非洲,题目却源于遥远大陆的叶芝。
整个故事没有提及年代,红楼梦一样开辟鸿蒙,又不知在哪世哪劫,唯旁观者迷惑,根据白人进入尼日利亚的年代非要推算明白:当是1900年前后的事。
黑人OKONKWO家境贫寒,父亲优柔寡断,不事生产,被村里的乡亲们嘲笑。OKONKWO发誓要做一真正男人,被人们尊敬。他身体力行,十八岁将最伶俐的摔交手摔倒,成为赫赫有名的勇士,他勤劳耕作,凭双手建立了坚实的家业,娶了三个妻子,成为村里决断是非的长老之一。
故事悠悠然开场,黑非洲的生活,鸡鸣既起,天黑而眠,男耕女织,村落里的秩序和神灵,仪式和庆典。时间缓缓而行,好象永远不会改变,没有人知道,在目力不及的世外,洋枪土炮,征服与被征服,一切都超越了想象。这样的生活如同天堂,和谐,有长幼规矩,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但作者晶莹透彻的眼睛也看到了种种自古存在的陋习:双生的孩子必须被抛弃,男人殴妻,医疗卫生极端落后,隐约的野蛮和愚昧。OKONKWO的形象在民俗的叙述中渐渐显露:暴躁,执拗,遵守每一件祖传的规矩,充满男子气息,却不会思考。大大小小的事件在河流般的叙述间涌现,如同星星点缀天空。
整本书二百页,排版稀疏,字大而距离遥远,纸质粗糙,人为制造出来的质朴感,是读书人最喜欢的奢侈。这正好象故事的编排,同样地质朴温和,岁月如同牛背上牧童的儿歌,我们在繁杂的生活里,在炉灶边,在沙滩上,在明媚的天光里,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昨天,偶然读上几页,缓缓地,不需要奋进,也没有紧张的情节令人窒息。
读过一百页以后,我想起了张艺谋,所有给异族人展示的故事都有这样的特色:一副民俗的画卷,阔大雍容,色彩的丰富,历史的古老令人震撼,对于吃惯西餐社会秩序健全思路简单的洋人来说,是最好的调剂。
OKONKWO的村子与邻村争执,邻村屈服,赔偿了一男一女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女孩子被送去给人当老婆,男孩子一时没有处置方法,暂时寄放在OKONKWO家。OKONKWO的家庭生活气氛不算和谐,主人公太刚硬沟通有障碍,三个女人瑟缩不敢多言,孩子懦弱。邻村男孩的出现使一切都改变了,他成为三个女人的好帮手,女孩子的朋友,男孩子的哥哥,OKONKWO的跟随者。他好象液态的胶水一样,使彼此互不相融的家人聚合在一起,喜悦涌现出来。连大石头一样的OKONKWO在又臭又硬的外表下,也流露出脉脉温情。
也许幸福能够称其为幸福恰恰因为不长久。三年以后,神告诉人们,必须处死邻村男孩。OKONKWO悲伤,OKONKWO无奈,他从未想过要违背神灵,可这一个活生生的男孩子,喊他做父亲的男孩子,他真心喜爱的孩子,又能怎么办?又该怎么办?作者是写字的老手,他创造了晴朗温和的一天,天空明艳,鸟儿雀跃,安宁温柔的时光,让每个人在行文里预期即将到来的血腥,是怎样的强烈对比?因为有情节,有铺陈,有反差,有OKONKWO出人意料的行为和外表强悍的懦弱愚顿,这一节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之一。
也许男孩子的死使OKONKWO心中有了更多一点温情。故事接下来叙述OKONKWO与二老婆母女的故事。二老婆曾是村子里最美的女人,她在OKONKWO十八岁那年的摔跤赛上看中了这个强壮男人,后来不惜私奔而来。她受的苦最多,生了十个孩子,只有最后一个女儿留下来。她最受OKONKWO喜爱,所以男人说话她偶尔也敢出言顶撞,而这一顶撞,使OKONKWO心头冒火,掏出猎枪来对着她射击,幸亏枪哑了火。二老婆唯一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美貌,性格则秉承父亲的决断,因此总能懂得父亲的心意。OKONKWO爱这个女儿,只恨她不是男孩子,不能为他扬名,不能在他死以后带领全家人祭祀他。女孩子身体羸弱,得了一场大病,死过九个孩子的母亲自然急得几乎疯掉,而那个做父亲的,维持着男人的尊严,好象毫不在乎的样子。临到章节结束,作者笔锋一转,偷偷告诉我们,OKONKWO于无人知晓时,急的热锅上蚂蚁一样,为了关心女儿的安危,竟做了好多徒劳无功的蠢事。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也是全书最温柔的亮点,让人一边笑一边为这个父亲感动。
但是,殖民和后殖民呢?
在全书的第125页,幸福的生活被打破了。一场葬礼上,人们为了纪念死者,装出各种神灵和死去祖先的样子疯疯癫癫地表演,OKONKWO当其时不慎枪支走火,杀死了一个同族人,根据习俗被流放到他故去母亲的村落。OKONKWO老了,他一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成为村中最受尊敬的拥有四个称号的长老,七年的流放将使他丧失了许多奋斗的时间。他郁郁寡欢,但是母亲家族的帮助和温暖,使他再一次在黑非洲的土地上凭借勤劳的双手富裕起来。他如此坚强,但是非洲的信仰和生产力并不足够坚强,第139页,白人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白人的出现是以屠杀为开场。第一个传教士来了,黑人们咨询神灵,神灵说,这是魔鬼,他将夺去你们的土地和信仰。于是黑人兄弟们就把他杀了。第二个来的白人带来了军队,将整个村子夷为平地。教堂建起来了,白人领导的政府也建起来了。失去双生子的母亲投奔了教堂,那些被村民们嘲笑和抛弃的弱者投奔了教堂,连OKONKWO的亲生儿子,一直屈服于父亲的淫威的,一直对邻村男孩儿的死耿耿于怀的懦弱儿子也感受到了上帝博大的爱,同情弱者的爱,和父亲画清了界限。
OKONKWO筹划了七年,想要风光显赫地回归故里,当他回归时,故里早已不是当初模样。他在针对白人的斗争里终于又一次寻回自己勇士的梦想。一次在饱受白人凌辱之后,他抽出刀杀死了一个白人的信使——他遥远的黑人兄弟。这时候他骄傲地回头,发现全族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他,责怪他的卤莽,害怕他会带来灾难,四散而逃。理想的大厦轰轰然倒塌。
206页,白人牧师带着军队来到村庄复仇,他们见到了OKONKWO自缢的尸体。在村落的信仰里,自杀是十恶不赦的,人们甚至不能用手去触摸他的尸体,还要等白人的军队来给他收尸。而且不会有人葬他。一个古老信仰的坚定拥护者,最后,根据古老的信仰,成为一具弃尸。
CHINUA ACHEBE是写字的好手,故事编排得十分精巧,没有漏洞,虽然与前半部的和缓庞大相比较,后半部稍显粗糙和急躁。整部书语言简单流畅,颇具美感,人物性格生动丰富。
有时候我真是想不明白人这种动物的感情,会如此复杂。CHINUA ACHEBE的父亲是当地最早的改变信仰者,他自己也是个基督徒,他用英文写字,他却对非洲的旧秩序旧信仰有如此多的爱。前一百四十页,生活的和美远多于陋习,后六十页,对白人的爱护远远不及对入侵的憎恨。
但是CHINUA ACHEBE毕竟是一个归顺基督的家伙,他在回顾天堂时不能不看到种种丑恶,他在憎恨入侵时不能不看到新信仰的某种博大,新秩序的某种先进。他在不前不后的地方,他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所以他的感触也许比每个极左或者极右的家伙都多。
所以他正好写小说。
too much focus on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writers. recommended by a professor in Alberta University.
seems low in speed and not as complecated as what i've read before. simple but moving, directly access to your heart.
brilliant one!
2007年6月13日,第二届国际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laine Showalter这样评价他:“In Things Fall Apart and his other fiction set in Nigeria, Chinua Achebe inaugurated the modern African novel. He also illuminated the path for writers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new words and forms for new realities and societies. We honour his literary example and achievements.”
而这一次华山论剑,出局的有Margaret Atwood、John Banville、Peter Carey、Don DeLillo、Carlos Fuentes、Ian McEwan、Harry Mulisch、Alice Munro、Michael Ondaatje、Amos Oz、Philip Roth、Salman Rushdie和Michel Tournier这些各类文学大奖的常客,也有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Doris Lessing。
他被称为非洲文学之父。南非前总统Nelson Mandela则称赞他是a writer "in whose company the prison walls fell down."
当我在飞机上读完他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Things Fall Apart 时,终于再一次震惊:和第一届的获奖者卡达莱一样的大师。一样地将巨大的绝望和悲哀化作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沉默的文字像静静流动的河水,同样地宣泄着他对那片神奇的土地无比的热爱。
对,那片神奇的土地。甚至那鼓声,也是他的同乡、另外一位文学大家索因卡绘声描述过的:历史、宗教与文化再次在鼓声中与死亡翩翩起舞,那些消逝已远的细节又泪水满面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不仅仅是非洲的黑人,还有美洲的印第安人,亚洲的土著。当更为宏大的背景在我的脑海中渐次展开时,窗外的黑夜是那么得黑,而且沉默,也沉重。
末路。
因此,当英雄Okonkwo结束流放回到自己的部族时,他“was deeply grieved. And it was just a personal grief. He mourned for the clan, which he saw breaking up and falling apart, and he mourned for the warlike men of Umuofia, who had so unaccountably become soft like women.” 他是英雄,他的死亡也是英雄的死亡。
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十月在敌人面前死去的格瓦拉,另外的一个英雄。
其实,小说的题目也是来自于叶芝的诗歌"The Second Coming",当年叶芝创作该诗的背景正是一战结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恰巧同时刚刚兴起,该诗被认为是对“即将诞生的非人性世界的一瞥”。因此,Achebe 对 Things Fall Apart 的借用,不仅仅是向叶芝的致敬,也是进一步深化对“非人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
1971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是曾经执导格拉斯《猫与鼠》和纪录片《爱与音乐》的德国导演Hans Jürgen Pohland。
事实上,除了写作,他一生致力于抵抗西方文化对非洲文化的边缘化,比如他著名的对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批判,便是对西方文化中假想的非洲的不满与抗争。饶有兴味的是,他成年后即在英国接受教育,现在又纽约州的巴德学院讲授文学。我想说的是,当养育了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文化在时间的冲洗下同时又要遭受西方文明的蚕食而变得百孔千疮时,个人命运的选择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路径?其实,他做得已经足够,他手中的笔和格瓦拉曾经紧握的枪一样,在面对所谓先进文明的冲击和殖民甚至奴役时,都成里刺向敌人的坚强利器。
不禁想:连布克奖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呵。当硝烟散尽,这样的认同与慈悲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些许的安慰呢。
2007年10月10日
奇奴阿·阿切比(Chinua Achebe),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毁誉不一的文学批评家,刚在上个月被授予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作为命运多舛的比拉夫政府外交官,他的主要兴趣范畴包括非洲政治、西方记叙中的非洲和非洲人、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文化与文明,以及殖民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1930年,奇奴阿·阿切比出生在具有深厚非洲乡土文学传统的尼日利亚,一个拥有丰富民俗想象和仪式文明的国家。父母皈依新教,他也因此自幼接受了教会英语教育。1953年,阿切比毕业于伊巴丹(Ibadan)大学,专业包括英语、历史及神学。在他加入伊巴丹前后,学校里还出过很多著名的作者和诗人,包括著名的诺贝尔得主握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约翰·佩柏·克拉克(John Pepper Clark), 还有克里斯托弗·奥基博(Christopher Okigbo)。
早在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非洲特派记者期间,阿切比就开始计划并创作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在三年内战中,阿切比支持比亚法拉独立运动,这导致他至今仍被敌对部落视为攻击对象。一九八二年开始阿切比流亡美国,并以非洲文学为题讲学于欧美各个大学。虽然成名于早年,但他的晚期作品《希望与困境》(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1990)、《家园和流放》(Home and Exile, 2000)更受到重视,被视为后殖民理论的经典之作。“尼日利亚四部曲”是以黑白文化冲突、本土族群内裂和自然宗教与一神论基督教的对立为主题的系列小说,既充满围炉听古的温热感,也具有激发民族斗志的内在张力。《崩溃》(Things Fall Apart)中的奥孔克沃,一个没落部落中的悲剧英雄的原型,实际上是阿切比这个文化斗士的自我写照。尽管他强调外来英语在民族叙事上的重要性,但对基督教民主总是保持一种抗拒疏离的姿态,他信奉一种称为“祈”(chi)的私神,意指爱与力的结合的传统智慧,认为一种以部落协商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才是最适合非洲人的生活体制。然而吊诡的是,“祈”是一种最易衍生为“强人政治”的思想元素,这或许意味着阿切比始终苦思于将“祈”转化为一种现代化的“部落社会主义”。
阿切比的《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发表于70年代,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史上一篇极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论著。在这篇文章中,他揭露西方批评家用所谓文学普遍性的观点来包裹自己文学的民族性,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批评。在《非洲作家和英语语言》(TheAfricanWriterandtheEnglishLanguage)6,以及《一个关于非洲的形象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An Image of African: Racism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文章中,阿切比谴责约瑟夫·康拉德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并宣称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的心》是对非洲人的丑化,把非洲描写成漠视人性的人间屠场,并籍此对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进行了尖锐批评。除了对诸如“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类,非洲小说不存在”之类的荒谬论调作出回应外,阿切比还从更高的层面审视了后殖民主义批评:“让每个人发挥他们的才能,为世界文化的盛大节日奉献礼物。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拥有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文化精品”。
坚持述说自己的民族故事,塑造非洲文化灵魂的悲剧人物,以混成式非洲英语书写非洲经验,是阿切比的创作理念。展现非洲的真实性,用西方人理解的语言来再现毋需恐惧的非洲,以民族寓言来沟通文化理解的落差,则是他多年锲而不舍的文学追求。他曾就母语写作之正当性的问题,与尼·瓦·西昂戈(Ngugi Wa Thiong'o)展开过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虽然最终屈居下风,但仍坚持非洲文学绝不能窄化为黑人非洲的文学,而是应该包括使用所有通行语言来写有关非洲事物的作品。这场最终没有结论且共识大于分歧的争论,说明了殖民与解殖这一文化圣战的复杂性与艰难性,同时也证明了边缘文学已跃居英语文学的议题中心。
将个人作品与民族命运联系起來,通过文学作为民族启蒙的精神载体,帮助族人摆脱殖民统治意识,是阿切比在当今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大陆已出版过他的小说《崩溃》,讲述一个部落英雄步步走向屈辱的死亡过程。主人公奥孔克沃的父亲是个善良而软弱的游手好闲者,一生穷困潦倒债台高筑,在村子里遭人耻笑。奥孔克沃通过辛勤劳作和摔跤,赢得了族人的尊重,也洗刷了父亲的耻辱。他在部落法庭上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面对着部落的衰退,力图保证自己的尊严。然而,在奥孔克沃表现出对“神”和规则的敬畏的同时,他也触犯了“神”和规则,这成为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不慎误杀同族中人,他被流放异乡七年,回来之后,发现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文化模式不再适合,古老的法则不再适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孔克沃没有对自己过去的社会经验进行反思,对自己的社会认知进行一次重组,寻找应付新世的新策略,而是与选择与新世界作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最终的结局是,为了维护“神”和自己的骄傲、拒绝白人的进入,奥孔克沃屈辱地将自己吊死在棕榈树上。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的力量,驱动奥孔克沃行为的情感核心与其说是对部落价值观的忠诚,毋宁说是出于对重蹈父亲覆辙的恐惧。在荒凉贫瘠的非洲大陆上,懒散与软弱意味着抗拒劳作,是与原始生存法则相抗的极大罪恶。由此可见,虽然悲剧肇始于内因,肇始于人的暴怒、内心的恐惧与骄傲,只是由不可抗的外力补上最后一击,才使得命运分崩离析,但构成命运的力量恰恰是种种历史的积存,种种历史的、社会的与政治的逻辑。
阿切比的文笔圆熟光洁,更令人叹服的是他出神入化的叙事结构和脉络,将小说构造成了一座精美的神殿。然而在神殿之中,我们遭遇到的却是被神的光辉细心遮蔽的耻辱,以及非洲民族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时接踵而至的苦难。(图书商报)
我对非洲文学总是满怀着期待,丰饶的神话、接踵而至的苦难、卓越的语言,足以诞生神奇的文学。在非洲各国中,尼日利亚尤其吸引我,一个遥远而且庞大的国家,位于非洲西部,在短短十余年间,相继涌现了图图奥拉、阿切比、索因卡三位大师级作家,后继者如本·奥克利,也是当前世界文坛的明星。相比起来,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就寥若晨星。
佛头着粪的“憎恨学派”
生活在一个粗鄙的文学时代,企图洁身自好、不被当下的中国文学所污染者,唯有把眼光放到窗外,堵上自己的耳朵,静心阅读其他语种的大师作品,以使自己保持对文学的绵薄敬意和微弱知觉,并且明了,当下的中国文学是如何寒酸以及如何自大。日前,阿切比的名著《崩溃》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对于爱读好文学的人,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的事情,尽管这个译本有着一个粗糙的序言。因而,如何避免受到这个序言的污染,就成为阅读这部小说的首要问题。
这个序言,合乎一句成语:佛头着粪,作者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后现代主义教授张颐武——江湖人称“张后主”。张教授长期浸淫于后现代的诸多理论,虽然不知道他的理论究竟为何,但是,作为“憎恨学派”的产物,其对文学的见解,却是可想而知。所谓“憎恨学派”,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一杆大旗下聚拢了各种花样翻新的理论,一言以蔽之,不谈文学,只谈意识形态和作家的国籍、种族、性倾向、衣服品牌、养不养狗等等问题。问题五花八门,言语花枝招展,三天一翻新五天一颠覆,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大脑之聪明和唾液之丰富。而这一切,都和文学无关。
譬如张教授这篇名为《〈崩溃〉的意义》的序言,闪烁于其间的关键词是以下几个:后殖民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对抗、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并将这部杰出的小说目之为“阿切比用自己的写作证明了,非洲的英语文学也具有经典意义,完全可以和欧洲文学的主流相抗衡”。然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解读,这部小说用英语而非阿切比的本族语言伊博语所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向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学的投降;更何况,这部小说的书名来源于英语文学的大师叶芝——阿切比引用了叶芝的话作为小说的题辞。
固然,阿切比在小说中写到了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崩溃,然而,这就是对殖民主义的控诉吗?阿切比所引的叶芝的话为:“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难再持守,世界到处弥漫着混乱。”作为欧洲文化的最后一代精英,身为白人的叶芝比黑人阿切比早三十年发出了哀叹:传统文化已经衰颓。而在阿切比之后的二十年,作为欧洲文化的非洲继承者,白人南非小说家库切,同样哀婉济慈和雪莱的文化全面崩溃。实际上,和阿切比大致同时,黄皮肤的陈寅恪等中国学者也有着类似的抱残守缺的文化理念。这一对传统的价值判断和认识,非关肤色、种族、文化。叶芝和库切,哀婉的是欧洲传统文化,阿切比哀婉的是黑非洲传统文化,陈寅恪哀婉的是中国传统文学,对象不同,心情一致,对于传统的伟大的同情和理解,而非浅薄的控诉、对抗或者其他后殖民主义的解读。
“憎恨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天花乱坠不知所云之外,最主要的流弊则是,混淆了文学的概念和标准——一方面把文学当成了棍子,挥向他们所谓的“西方”;另一方面,把文学当成了婊子,任意摆弄出各种姿势;再一方面,把文学当成了牛尿泡子,爱怎么吹怎么吹——他们人多嗓门大,占据着大学的课堂,自然响遏层云,一呼百应。
如此这般,中国之文学,怎能不面目可憎?
脉络清晰的文学主题
图图奥拉的《棕榈酒鬼以及他在死人镇的死酒保》出版于1952年(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8月初版);六年后的1958年,阿切比的《崩溃》出版(1959年获英国布克奖,英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再七年后的1965年,索因卡的《阐释者》出版(大陆译为《痴心与浊水》,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译名是怎么搞出来的?)——其间,尼日利亚于1960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三位作家,最年长的图图奥拉是约鲁巴族人,阿切比是伊博族人,而小弟索因卡的母亲是约鲁巴族、父亲是伊博族。这三部作品,如今都已成为20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这其中,索因卡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非洲作家;而阿切比也是多年被目为这一奖项的热门候选人。
纵向看这三部小说,不仅出版时间和作者年龄呈现顺延关系,在小说的主题和内容上,也呈现出清晰的递进形态。
严格地说,图图奥拉的《棕榈酒鬼以及他在死人镇的死酒保》尚且不能被称为“小说”,它只是“故事”,约鲁巴族的民间故事——“无所不能的众神之父”,因为他的仆人酒保酿制棕榈酒的时候在树上摔死,没有酒喝,从而前往死人镇寻找死酒保的漫游历程。这一历程由很多小故事组成,从篇名就可看出故事的奇异和炫目,比如“不要怪淑女跟化身为完整的绅士的骷髅头走”、“三个好生物接手我们的烫手山芋——他们是:鼓、歌和舞”、“前往无法回头的天堂镇”、“路上的死婴儿齐步走向死人镇”等等。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这个世界属于“那个年代”而不是“现在”,如图图奥拉在书中借“无所不能的众神之父”的嘴所说,“在那个年代,野生动物横行,许多地方都被浓密的矮树林和森林覆盖住,小镇和村子不像现在靠得那么近。”图图奥拉所叙述的故事,是尼日利亚——乃至于整个黑非洲遥远的从前,是原始的黑非洲,居民既不信奉伊斯兰教也不信奉基督教,而是信奉各种具有古怪性格、行为、面目的神。
到了阿切比的《崩溃》,小镇和村子已经紧紧挨着,部落之间的仇杀、联姻、经济和社会活动紧密相连,白人即将侵入。尽管“神”在人民的生活中居于主要地位,但部落对“神”的敬畏已经不再庄严,部落的规则遭到岁月的白蚁的侵蚀。而《崩溃》也从神话故事变成一本结构精巧、语言简洁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奥孔克沃,部落的上层人物,一个服膺“神”、武力和规则的英雄,在部落法庭上扮演着“神”的角色担任仲裁,面对着部落的衰退,力图保证自己的尊严。然而,在奥孔克沃表现出对“神”和规则的敬畏的同时,他也触犯了“神”和规则,这成为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奥孔克沃不是“无所不能的众神之父”,没有绚丽的漫游故事,他仅仅是触犯了“神”的凡人,有着平淡的生活的挣扎。其最终的结局,为了维护“神”和自己的骄傲,为了拒绝白人的进入,奥孔克沃屈辱地将自己吊死在棕榈树上。这一小说的结尾,几乎是对图图奥拉书写的“神话”的隐喻性继承——作为“神”的仆人和“神”的人间代言人,奥孔克沃同样死于棕榈树上。在小说形式上,《崩溃》同样讲述了很多民间传说和“神”的故事、歌谣。
而在索因卡的《阐释者》中,小说的背景由部落转移到了城市和当代,小说的语言由图图奥拉的明亮、阿切比的简洁变为沉郁,小说的主人公由图图奥拉的“众神之父”、阿切比的英雄变成了生活于城市的一群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无力年轻知识分子。但是,小说依旧在各处隐藏着黑非洲传统的残余:主人公之一画家科拉创作《众神像》,将古老的神话之“神”和自己朋友们画在同一张画布上;另一主人公艾格博放弃了部落的酋长身份,选择在城市里做一个处处吃瘪的小职员,对《众神像》非常愤怒,因为他想和有“神”的过去一刀两断(在部落,他就是“神”的代言人)——尽管部落的丛林让他宁静(“我喜欢精致和神秘的生活”);小说中的宗教狂热分子所用的“传教动作”,和《崩溃》所描述的女祭司的语言和动作如出一辙。更主要的是,《崩溃》所表达的部落的骄傲,同样在艾格博身上残存。尽管艾格博的外公老酋长迫于形势同意变革,但“艾格博一直在老头子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感到有一种大丈夫气质,一种残存的高贵风度。而他知道,这种气质正在被破坏”;尽管生活于城市而逃离酋长的身份,艾格博依旧说:“我还保有我的种族骄傲。”这一“骄傲”和“大丈夫气质”,就是《崩溃》中奥孔特沃的魅力所在。
不可逆转的英雄悲剧
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如同在“神”的面前,英雄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成立。在《崩溃》中,奥孔克沃以英雄的形象出场,生活在一个叫乌姆阿非亚的村庄,然后一步步走向屈辱的死亡。在这一过程中,白人的侵入完成最后一步,是压在英雄脊梁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这之前,悲剧早就拉开了帷幕。
在小说第四章,阿切比刚刚用三章篇幅叙述完奥孔克沃如何获得自己的名声、财富、头衔和尊严与骄傲,便叙述了奥孔克沃由于骄傲和英雄所具有的暴怒特性触犯了“神”:在祭祀土地神灵的平和节里,奥孔克沃结结实实地把不做饭的小老婆打了一顿,“他的两个老婆惊慌地跑了出来,恳求他在圣洁的日子里不能发怒。但奥孔克沃不是那种打老婆会半途而废的人,甚至他也不怕神灵的怪罪……多少年来,第一次有人打破了神圣的平和节。”而部落对于奥孔克沃的处罚,已经不是过去时候的“拖在地上,在村子里来回游行直到他断气”,而仅仅是向“神”奉献祭品以求宽恕。这一过程说明了,一方面,奥孔克沃作为一个暴怒的英雄,步上了他之前的所有文化里的英雄的必由之路——英雄的道路,由“不怕神”开始,由“神”的惩罚结束,尽管在这部小说里,奥孔克沃的命运并没有由神迹主导;另一方面,部落文化和部落规则,已经出现缝隙,文化的衰颓和规则的破坏的具体行为表现,恰恰是从部落的英雄,同时也是部落利益、文化和规则的忠诚守护者奥孔克沃开始。部落衰颓的命运和奥孔特沃的个人悲剧命运,纠缠在一起,彼此扶持,走向屈辱的终结。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奥孔特沃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和骄傲,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养子。尽管部落中人已经告诉他不用动手而由其他人完成仪式,“恐惧使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奥孔特沃抽出砍刀,一刀将艾克梅夫纳劈倒了。他害怕被人认为自己软弱。”尽管在这一时刻,他的表现合乎英雄的模式——甚至合乎神话中的那些食子的“神”的模式,这一行为,既伤害了他的家人(他的亲生儿子最终叛离了父亲,信奉了白人的宗教),也使自己的心灵和身体虚弱(“他就像一个喝醉的巨人长了蚊子的腿脚,不时有股冷战从头顶传到全身)。而在小说中,有一段他和好友关于这一行为是否合乎“神”的旨意的争论。奥孔特沃坚持自己的行为是执行“神”的命令,而他的朋友奥别卡里则告诉他:“你所作的事情土地女神不喜欢。土地女神可能因为这个行为是一个家庭断子绝孙……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杀,我即使不反对他的命令,但也不会亲手去杀死他。”
在朋友的阐释下,奥孔特沃的这一血腥的英雄行为,不仅违背了“神”的意愿,而且违背了“人性”。霉运降临到他的头上,一波接一波:首先,他最心爱的女儿爱琴玛生病;紧接着,在部落首领的葬礼上,他的枪走火杀人,被迫离开部落七年。而使奥孔特沃犯下这一罪的,则是他的力量的象征:枪。这成为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奥孔特沃开始直接面对导致他和他的部落灭亡的白人。所有的“英雄之路”的铺垫已经在前半部分完成,剩下的,就是英雄挣扎的过程。
在放逐之地,他辛勤地种红薯,维持家庭的体面;而他的儿子纳沃菲则跟着白人走了,并非宗教教义吸引他,而是“赞美诗中有关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中的兄弟俩的歌词,似乎回答了长期困扰着他年轻心灵的那个模糊、固执、久远的问题——那在草棵子里哭叫的双胞胎的问题,以及惨遭杀害的艾克梅夫纳的问题。”导致纳沃菲的恐惧和艾克梅夫纳的惨死的,都是英雄奥孔特沃。
奥孔特沃回到了部落,准备建一座更大的粮仓,以恢复自己在部落的地位。然而,白人以及白人建立的政府接踵而至,给了他最后一击。在一次宗教仪式上,一个新皈依的黑人教徒挑衅地破坏了仪式,“杀死了一个祖先精灵,乌姆阿非亚陷入了一片混乱”,部落的上层人士,包括奥孔特沃(“这么多年来奥孔特沃第一次有了快乐的感觉……从前对他不闻不问、冷淡消息的部落似乎在做着补偿”),在与白人理论的时候继而又受到白人政府的监禁和羞辱,最终不得不用钱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在部落的最后一次集会上,奥孔特沃获得了英雄的地位,他的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灵都在哭泣……因为他们遭受了可耻的亵渎……我们必须彻底根除入侵我们家园的邪恶。”在白人的信使来到集会现场宣布白人的权威的时候,“奥孔特沃闪电般地抽出了砍刀……头目的脑袋骨碌碌地滚到了穿着军装的身体一边”,紧接着他发现,部落里的人只是看着他,没有和他一起行动,“乌姆阿非亚人害怕了。”
小说的最后,骄傲的英雄奥孔特沃完成了自己的命运:吊死了一棵棕榈树上。而在部落里,自杀是令人鄙视的,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土地神灵的旨意,“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他的好友奥别卡里“恶狠狠”告诉传教士:“这个人一度是乌姆阿非亚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你们把它比上了绝路。如今他却要像一条狗一样下葬。”
这一屈辱的、违背神灵旨意的死亡,将英雄奥孔特沃塑造定型。悲剧肇始于内因,肇始于人的暴怒、内心的恐惧、骄傲,而由不可抗的外力给与最后的致命一击。由于此,奥孔特沃的命运具备了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更多来自于古希腊,而非来自于热闹的莎士比亚风格(相比来说,索因卡的小说和戏剧,则因太过喧嚣和丰富的形式感,而接近于莎士比亚风格)。白人在奥孔特沃的悲剧命运中的角色,既是尼日利亚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也是悲剧完成的不可缺因素,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部落、民族、文化的命运,衰颓总是从自身与内部开始,而由外力完成。阿切比对白人这一“野蛮人侵入”的描述,固然有着对本族文化的哀婉与对外来暴力的愤怒,但并没有使这部作品成为简单化的阶级斗争文学,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神”愤怒同样,承受而非控诉。《崩溃》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也不是因为它反映了白人入侵的暴力,而是因为它呈现了黑非洲文化衰颓的悲剧命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英雄的悲剧命运,小说中不时讲述的黑非洲民间传说和神话,则是这一悲剧的灿烂的副歌。
让人有所期待的开场白。请继续
啊?开场白?我写完了……
不是 是世界历史的鸟东西 惨不忍睹 老子都不想看第二遍...
你能体会一个半调子法语他痛苦的万一吗
就这鸟东西A-哦亲~
除了第一条与第十条外,用剩下的十二条来衡量这些原则本身,卡尔维诺的这十四条原则也堪称“经典”了
楼主是否认为作家应让主人公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领导非洲人民开展反帝反殖民斗争?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判断所谓的经典,那么我国的“革命”作家都成了世界级作家了。
我觉得阿切比在写作时确实存在困惑,一方面,与欧洲文明相比,他从心里不认同貌似我国尧舜时代的非洲落后部落生活,但另一方面,非洲人身份的他又不能背弃血缘所在的立场,以免遭到“左愤”们的围攻。他在全盘西化与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中徘徊,抓不准出路,弄得里外不是人。
这也是阿切比自身的崩溃。
尧舜时代只能说是生产力落后,但其民主程度是很高的(参见钱穆的《黄帝》)。作为一个民族中的一员,从本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长处与软肋才是正确的方法,一个自身都崩溃的作家更加称不上所谓“经典作家”。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宏大体系,或仅窥其某些短篇,就可见经典作家内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至于我国的“革命”作家,我不是很了解,没有发言权。但下午看到草婴译的波列伏依的《胜利》,尽管我们对苏联的体制可能存在不满,但那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称道的。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丝毫民族精神的作家,很难让我欣赏,这也是我对阿切比这部作品评价不高的原因。
读这本书,起初的感觉跟lz完全一样:太不耐读,仅是一个包上一层让西方人觉得新鲜的非洲原始部落外衣的故事,一个关于前现代秩序如何在外来冲击下瓦解的故事,一个基本属于炒卖民族题材的故事。
不过后来有了些新的认识,阿切比本人就悬在半空,他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正面发声的突破口,抑或非洲的思想文化根基就注定了他无法像陀翁一样能从民族文化与宗教中汲取到这么多资源。非洲本身的情况即如此,作家选择纵向截一个切片下来,将一个部落英雄简单、明晰而毫不带有被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荒诞意味的一生呈现一遍,也无可厚非。在故事里有时也能看到他对某种精神的称道,只是不那么明晰,且很快就被另一些现实抵消了。作者在讴歌原始文化、塑造非洲英雄和抨击白人殖民行为之间游移,最后把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剧叙述完整,阿切比一点也不复杂的路数,会让习惯“黑暗之心”主题或对传统不复之哀声的读者感到不满足。
所以原作在英文上狠下了功夫,词句虽简练通俗,但节奏感十足,氛围经营得非常到位,让人能结合句子的节拍想象画面,中译本则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腻的运思,只把一个句子的基本意思给传达了出来就算了事。我想其所以“不耐读”,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翻译。
十分赞赏楼上的观点,你把我想表达的意思说了出来。
我觉得这本小说写得还算不错的原因就在于阿切比写出了其自身思想体系的崩溃。
他自身的民族文化难以容忍主人公的父亲这样的艺术家生存,也可以毫无理由地残杀质押在主人公家的那个孩子,甚至更无逻辑地放逐了坚决捍卫传统的主人公。可是举着人道、理性、文明的旗子而来的西方文明,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手段又证明了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包藏祸心。
这何尝不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崩溃。
什么思想体系,什么革命立场,小说与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现代小说的美是与道德审判政治审判绝缘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欣赏现代西方小说之美
不知道按照LZ的革命立场,怎样评判俄罗斯众多被征服流放的作家呢,还有波兰、捷克、古巴、智利的流亡作家呢
先读了《神箭》再读《崩溃》,觉得后者远不如前者。但全世界来说,前者也更出名。翻译的关系吧,确实译得很平庸,不痛不痒。
LZ在文中引用了艾伦·布鲁姆,而在布鲁姆《西方正典》附录里,赫然写着阿契贝的三部作品
@Peano:对于西方正典的附录,不妨看看布鲁姆本人对此附录的看法。
你的意思是这些是他没把握的作品吗,这到是有可能
原帖地址我记不得了。其中的大意是,随书所附的书单不是布鲁姆的本意,乃书商所为,布鲁姆本人对列出书单和书单本身都不满意。
对于文学作品么,看法都是见仁见智:D
这是从哪里看到的
在附录里,布鲁姆说对二十世纪的不少作品,他并没有把握这些肯定就是经典,混乱时代作品太多了
库切在城市里混,阿契贝在部落里混。
有机会我也要看
没看过尘埃落定,瓦解看到70页,已经觉得物超所值。或许这正是我喜欢的叙事方式和结构。
《尘埃落定》跟这本书比?开玩笑!你以为中国作家真达到了世界水平?
为啥不能比呢?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客观一点吧!
直接无视+BS你
哥们书读太少了吧
别发火,先读了之后再发言吧,否则,我当你是放屁!
切,好像就只你读过……
当然是两本都读完才来的
《尘》读了一次,《瓦》读了三次
那你厉害,读了三遍!
尘埃落定跟本书毫无可比性啊兄弟,中国作家只会写垃圾,脑子全都智障
我看大家都有些厚此薄彼了,还是理性一些好。高尔基那么出名,是否高尔基的文学早已高过籍籍无名的布尔加科夫?
谁说高尔基比布尔加科夫出名了?
在俄罗斯,高尔基已经不再被当做一位作家看待了,当做什么呢,那个时代的文学物证罢了。
当然,什么事情在我们这里都是拧巴的,比如《钢铁是……》一书,典型的垃圾,俄罗斯已经将其清除出文学史,现在倒成了中国中学生的必读物。
> 删除
dfish兄说得有道理。钦努阿·阿契贝的《瓦解》,之前翻译叫《崩溃》,就其故事,不是很吸引人,就其深度,无非也是主流思想,不偏不倚,老老实实叙述了一个故事而已,因为是翻译作品,语言也没有什么特色,比较流畅而已,《崩溃》翻译糟糕得多。这部作品如此受追捧,有些拔高了。当然是好作品,但绝对算不上杰作。估计更多的是,我们的猎奇心理。
如果真的看懂仂这本书,就再推荐一本 decolonising the mind, 讲的都是同一个theme。。。colonizing one's thoughts is more powerful than colonizing the land.....
英文不懂也?咋个办?
才上架的书?
似乎我还没有看过非洲文学……以后补上
受益匪浅~~~~
很有参考价值,但不要把《瓦解》放到“恐黒”的对立面,那样无利于表明前者的独特价值。
《瓦解》的价值在我看来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从未消逝的一种人类尊严。也许古老的生活方式连同传说中的英雄都消逝了,但当我看到枯树丛中挂着主人公的尸体时,我觉得他赢了,以一种谁也无法战胜的方式巧妙地把一种东西永远的妥当的安放在了这个世界上,安放在我们心的一个角落,这是一种尊严一种荣誉一种智慧一种神旨一种永不会逝去的东西。
我坚信只要是人类的宝藏就永远不会逝去,而《瓦解》只是把这表现出来罢了。
这篇评论太浅薄了
我喜欢看评论的前半部分 信息量的堆叠加评论者自己的故事 后半部分的评论不敢妄加评断
同五猴。看了前半部分评论,我就迫不及待的关注了作者。但是真正进入评论以后,把《瓦解》的光芒剔除太多,弱化了,模式化了,简单化了。
同感。前半部分故事精彩,但评论我看到的是模式化的观点。“恐黑”还远远没有瓦解。约瑟夫 康拉德也不止“种族主义者”这么一点本事。
我喜欢作者借书中各人物的口讲述的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其中最喜欢的是那个乌龟的故事...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不过作为小说,读着还是蛮轻松的。
我没能看完,太长了,先做个记好吧。
我是这个学期上东方文学史才接触到阿契贝的。写得真好,确实是展示给异族人看的美丽画卷。看得时候觉得怎么安宁的生活和基督的入侵怎么转化得这么快。不过,正是这样的突兀才让我们看到了部落的温情和走向没落的江河日下。
挖!!!!名家专栏诶!
Orz...........
这本书会有中译本吗
有的,不过译得很差
我想说,为什么我们这学期要读这本书,还要写paper!!!!!!!!想死的心都有了...
“在荒凉贫瘠的非洲大陆上,懒散与软弱意味着抗拒劳作,是与原始生存法则相抗的极大罪恶。”这句话可以删掉吗?
写的太好了,差不多是我多年来看的最好的书评.
又看了一遍,书还没有看完.
在世界文学的森林里,我们没有拉丁美洲和非洲那样的带有原始神秘色彩的奇观可以奉献,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根联系我们和大地,同时又能给外族人以及后来人以启发的线索,实在太难了.
<崩溃>中简洁的语言流畅的叙述,绵绵的温情,叫我想到余华的<活着>,毫无疑问,目前为止,这是从接近大地这个角度来说,最好的描述我们这块"神奇"的大陆的作品.从语言和叙事策略上,我想阿切比和余华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一点在他的<兄弟>中更加明显,但是,我只看了上半部,我承认他写的很好,有一些片段完全可以成为经典,但是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看下半部的动力.
原因是什么?我想<活着>在追求对宏大叙事的自我实现的同时,文字背面是不由自主的对这片土地的人民的爱,这种爱非常强大,即便在余华经过零度叙事的过滤,依然能在那些破败的场景,无可奈何的人和事中间找到他的叹惋.
<兄弟>的境界无意更大,笔法更加老练成熟,唯一的问题是,目的太过明确.原先的余华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目的是宣泄情感,而在<兄弟>中,虽然也有这种冲动,但是无疑要让位于更加现实,更加明确的要"表现"时代\成为经典的"目的".
余华模糊而强烈的情感使<活着>充满了冷漠与温情,看客与戏中人的摇摆,这种混乱\模糊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浓烈,恰与书中所表现的时代及时代下的民族和个人的情感相和,从而在整体上,从情感角度实现了对历史\大地和民族之间关系的诠释.
<兄弟>中的余华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参与性或者要比以前强,但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明显要明朗的多.情感宣泄的需要让位于居高临下的评判,模糊而强烈的对这块土地的爱让位于成为上帝(重新叙述并建构大陆\民族\历史的关系)的欲望,简洁节制让位于狂妄自大式的喋喋不休.没有谦卑心态的他,在历史\大陆\民族\个人之间,俨然成为上帝,不是叙述,而是宣判.
而大陆是可以宣判的吗?历史\个人\民族,又有那一个可以被另外一个人宣判?余华对自己的小说的评价是"正面强攻",真是再形象不过,只是他不知道,即便马尔克斯也不能宣判拉丁美洲,他可以吗?
以自杀来结束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但是这样的结局也许最好的反映了在当时环境下的无奈……
好的书评总让人学到知识
受教!
对张颐武的批判酣畅淋漓。评论写得也不错,不过,亲,能告诉我为何用了那么多被你打倒的人的理论还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