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
200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胡廷楣
399
无
《生逢1966》是一部描写文革背景下的“老三届”少年艰难成长的长篇小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高一学生陈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父亲自杀、母亲病死的家庭变故。最后,亲近的女生又不得不离开。他为参加红卫兵同家庭决裂,但又不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定自己人生座标。他在迷茫中行走,几乎失去了一切,承受着心灵的巨大伤痛。最后终于在绝望中获得了来自同学和老师的亲情安慰。
谨以此书献给老三届和他们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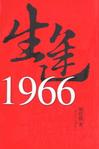
无
胡廷楣的长篇小说《生逢1966》以上海淮海路大同坊内石库门群落的几个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师长生活及他们所参加的、被称为“政治运动”的浩劫为背景,描写了以主人公陈瑞平和他的几位儿时朋友、同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文革”并进入丧失人性、理性的一段“疯狂”的人生历程。
红色、黑色;酸性、碱性,本是两组互相对立的词语却同时共存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激情与亢奋;失落与迷茫,到底哪个才是那个激情岁月的青年所拥有的心情。
《生逢1966》只是讲述了那个年代普通家庭中的一个普通青年的青春岁月。小说的主人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高一学生陈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父亲自杀、母亲病死的家庭变故。他为参加红卫兵同家庭决裂,但又不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定自己人生座标。
在陈瑞平的生命中,那段历史将永远会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孤独还有他19岁男孩的眼泪。他的青春就在这一片无所不在的红色中间走过。
历史事件的发生也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会让他在瞬间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喜或许只能是浩如烟海中的一粒浮尘而悲却注定是终生的。那个时代也许会让人得到他最渴望的也可能会让他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事件。它让所有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激情澎湃,燃烧梦想,却也能在瞬间打碎所有青年的梦想。
作品的特别之处不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多么新奇的故事,也不是在为我们讲述曾经的如火如荼的文革场景,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揭示了在那样一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矛盾与迷茫和他们那颗孤寂的灵魂。小说深刻而冷静,用冷到近乎残酷的清醒的笔墨写出了独属于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那段扭曲、压抑、晦涩的青春往事。
瑞平就是生活在一个“锣鼓不知为何而敲,但永远在喧天;红旗不知为何在飘,全部在飞扬”氛围之下的上海。他成绩优秀,打得一手好篮球,如果没有文革,他也许会很顺利地考入某所一流的大学和父母平静地过一辈子。然而,文革的到来让这一切都改变了。他的生活似乎失去了重心。资本家的父亲,地主阶级的母亲,这样的出身让他失去了成为团员的机会;当他终于站出来和地主出身的母亲划清界限时,他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红袖标,但却让他永远失去了与母亲之间的亲情。
红袖标的力量是摧毁性的,它让一个青年为它如痴如狂;它让一个青年四十三天没有叫过母亲一声妈妈;它更具有让一个青年在母亲身患胰头癌时都在矛盾着是否要叫母亲一声妈妈的力量。儿子反复地问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是啊,的确,“谁说过不能喊呢?她确实是你的妈妈。谁又批准你能喊呢?”就在这“喊”与“不喊”之间,母亲的气息渐渐衰弱,儿子也终于喊出了母亲再也听不到的那个最平常的称谓。就在母亲已经去世了,瑞平还是在矛盾着:“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妈妈死了,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了。然后又突然荡了上来,妈妈死了,我不用叫妈妈了。”
最平凡的感情竟会以这种方式走向终点,让人感到悲哀与凄凉。面对着这样的文字,胸口就像被千斤的石头压住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那样一个时代迷失的不仅是那失落的亲情,还有那青涩的爱情。
小说里关于陈瑞平与蓓蓓的初次灵肉“相遇”,也写得节制、含蓄,布满无奈、怅惘,而又满含着复杂的美感。
最初,陈瑞平并不喜欢蓓蓓,但却将自己的“初次”给了美丽的蓓蓓,这是两个饱尝了苦涩与挣扎的灵魂的相遇,充满了无奈、怅惘,却又满含着特殊的美感。
两个孤独的少年在各自人生的十字路口相遇,擦出炙热的火花,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深沉的爱意,只是两个孤寂漂泊的灵魂在颤栗的肉体拥抱中寻求着精神安慰。19岁的少年在彼此的拥抱中感受着彼此急促的呼吸,并在他们人生中的“大事件”温暖着彼此的心灵。也许他们还很稚嫩,但唯有如此,他们空虚而游离的灵魂才能暂时得到安放,那彷徨的内心才能得到暂时的抚慰。
看似荒诞的尝试,却饱含着当时青年的苦涩与挣扎。蓓蓓为了一枚小小的团徽付出了她全部的向往与盼望,付出了改变一生的代价。而瑞平付出了他生命的全部—他的爸爸、妈妈和他全部的青春,最后只留下19岁男孩的泪。
这样的“爱情”也许注定不会有结果,然而他们就这样彼此拥抱着,抚慰着彼此脆弱的心灵,互相赠与的只能是苦涩的青春的证明。
青春是什么,青春又给人留下了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与感悟。作者在小说中贯注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小说如此地真实与深刻,更加震撼人心,让每一页书页都散发着璀璨的光华。
胡廷楣的长篇小说《生逢1966》以上海淮海路大同坊内石库门群落的几个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师长生活及他们所参加的、被称为“政治运动”的浩劫为背景,描写了以主人公陈瑞平和他的几位儿时朋友、同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文革”并进入丧失人性、理性的一段“疯狂”的人生历程。
红色、黑色;酸性、碱性,本是两组互相对立的词语却同时共存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激情与亢奋;失落与迷茫,到底哪个才是那个激情岁月的青年所拥有的心情。
《生逢1966》只是讲述了那个年代普通家庭中的一个普通青年的青春岁月。小说的主人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高一学生陈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父亲自杀、母亲病死的家庭变故。他为参加红卫兵同家庭决裂,但又不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定自己人生座标。
在陈瑞平的生命中,那段历史将永远会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孤独还有他19岁男孩的眼泪。他的青春就在这一片无所不在的红色中间走过。
历史事件的发生也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会让他在瞬间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喜或许只能是浩如烟海中的一粒浮尘而悲却注定是终生的。那个时代也许会让人得到他最渴望的也可能会让他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事件。它让所有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激情澎湃,燃烧梦想,却也能在瞬间打碎所有青年的梦想。
作品的特别之处不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多么新奇的故事,也不是在为我们讲述曾经的如火如荼的文革场景,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揭示了在那样一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矛盾与迷茫和他们那颗孤寂的灵魂。小说深刻而冷静,用冷到近乎残酷的清醒的笔墨写出了独属于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那段扭曲、压抑、晦涩的青春往事。
瑞平就是生活在一个“锣鼓不知为何而敲,但永远在喧天;红旗不知为何在飘,全部在飞扬”氛围之下的上海。他成绩优秀,打得一手好篮球,如果没有文革,他也许会很顺利地考入某所一流的大学和父母平静地过一辈子。然而,文革的到来让这一切都改变了。他的生活似乎失去了重心。资本家的父亲,地主阶级的母亲,这样的出身让他失去了成为团员的机会;当他终于站出来和地主出身的母亲划清界限时,他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红袖标,但却让他永远失去了与母亲之间的亲情。
红袖标的力量是摧毁性的,它让一个青年为它如痴如狂;它让一个青年四十三天没有叫过母亲一声妈妈;它更具有让一个青年在母亲身患胰头癌时都在矛盾着是否要叫母亲一声妈妈的力量。儿子反复地问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是啊,的确,“谁说过不能喊呢?她确实是你的妈妈。谁又批准你能喊呢?”就在这“喊”与“不喊”之间,母亲的气息渐渐衰弱,儿子也终于喊出了母亲再也听不到的那个最平常的称谓。就在母亲已经去世了,瑞平还是在矛盾着:“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妈妈死了,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了。然后又突然荡了上来,妈妈死了,我不用叫妈妈了。”
最平凡的感情竟会以这种方式走向终点,让人感到悲哀与凄凉。面对着这样的文字,胸口就像被千斤的石头压住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那样一个时代迷失的不仅是那失落的亲情,还有那青涩的爱情。
小说里关于陈瑞平与蓓蓓的初次灵肉“相遇”,也写得节制、含蓄,布满无奈、怅惘,而又满含着复杂的美感。
最初,陈瑞平并不喜欢蓓蓓,但却将自己的“初次”给了美丽的蓓蓓,这是两个饱尝了苦涩与挣扎的灵魂的相遇,充满了无奈、怅惘,却又满含着特殊的美感。
两个孤独的少年在各自人生的十字路口相遇,擦出炙热的火花,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深沉的爱意,只是两个孤寂漂泊的灵魂在颤栗的肉体拥抱中寻求着精神安慰。19岁的少年在彼此的拥抱中感受着彼此急促的呼吸,并在他们人生中的“大事件”温暖着彼此的心灵。也许他们还很稚嫩,但唯有如此,他们空虚而游离的灵魂才能暂时得到安放,那彷徨的内心才能得到暂时的抚慰。
看似荒诞的尝试,却饱含着当时青年的苦涩与挣扎。蓓蓓为了一枚小小的团徽付出了她全部的向往与盼望,付出了改变一生的代价。而瑞平付出了他生命的全部—他的爸爸、妈妈和他全部的青春,最后只留下19岁男孩的泪。
这样的“爱情”也许注定不会有结果,然而他们就这样彼此拥抱着,抚慰着彼此脆弱的心灵,互相赠与的只能是苦涩的青春的证明。
青春是什么,青春又给人留下了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与感悟。作者在小说中贯注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小说如此地真实与深刻,更加震撼人心,让每一页书页都散发着璀璨的光华。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偌大图书馆的书也不曾借阅几本。仿佛曾经爱看书的习惯一下子就忘记了。但是在我从图书馆借阅的寥寥几本书中这本《生逢1966》绝对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动荡年代中上海市井人家的人生百态,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个年代都是失去人性没有人的尊严的。我依然记得书中一开始写的沙沙的马桶声,还有那用来吊命的人参。如果你有时间坐在阳光照耀下的沙发上我推荐你一下午读完它吧。
一个没有辨别力的年代,成为毁灭自己家庭的帮凶,没有力量反驳的脆弱的人,留不住爱人,亦不敢追求爱人,这样的遗憾,也是一种凄美吧。
看到的悲剧太多,才知道不能错过什么;
幸好我们都还年轻,还有选择的机会;
也因为活着,该珍惜的就别吝啬;
你以为存在的,说不定哪天就不见了;
没有一摸一样的东西出现,他们都是唯一的;
那些记忆教会了我们,走好每一步,远离悲伤。
引用王小波引用过的小个子拿破仑皇帝的一句话:我尤其喜欢以血写就的书
就像这本书血红的封面给我们的暗示一样
我一直喜欢在车上看书,这不是个好习惯,可是没有办法——自从我不再是个学生,不再拥有大白天懒洋洋斜躺在床上合着阳光一起读书的权利之后,大部分的好时光都用来养活自己了,这美其名曰工作,实际是变相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跟上我购书的速度。
今天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天公依然不作美,淅淅沥沥横飘飞絮竖凿地。这样也好,上班的公交车上,我读完了《生逢1966》。车很挤,几乎没有空隙的人群里硬是夹了无数把滴水的雨伞,我用手拂去不小心落在大衣上的水珠,不敢抬头向对我说抱歉的乘客报以微笑,生怕让人看见有些泛红的眼圈。故事在到站前结束,我直愣愣地将书放进皮包,直愣愣地下了车,直愣愣地撑开伞,忘记戴上手套。
故事真的结束了么?书里说“大同坊”如今已经油漆一新,可我那么多次在淮海路上穿梭,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弄堂,更加不会去想,四十年前,弄堂里的人要怎样生活。
在那个说话小心翼翼都不一定能保证安全的年代里,没有隐私可言的弄堂生活长满了眼睛,像是蜈蚣精的后背,在特定时刻会一同发出灼人眼球的金光。不过,上海是个沿海城市,这注定了上海人是很温和的,那些金光不会致人于死地——只会叫人想躲避。于是脆弱得像瓷器一样的人就去棺材里寻找清静了,他们才不管他们的骨灰是用红布袋还是用黑布袋装的,至少他们是可以缺席一切叫他们坍台的情境了。通常选择躲避的都是男人,上海男人。要不怎么说上海是个阴盛阳衰的城市呢!留下来的女人也想躲避的呀,可是女人是水做的呀,她们舍不得小孩,舍不得她们羽翼底下的天使。如果没有把她们心头那块肉,翅膀底下那个小人安排好,她们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而那些放射着金光的眼睛也并不尽然全是恶毒,那种金光的主要成分是嫉妒。只要嫉妒的对象不再拥有令人嫉妒的光环,那些眼睛里就会混进一些同情,与之前的嫉妒交织成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情。这种温情的分子相当复杂,施者不好讲明,受者就更不想暴露这个复杂的化学方程式。上海人是喜欢“扎台应”咯,所以这个掺杂着一些些幸灾乐祸和一些些兔死狐悲的感情最好就是化作实际行动。这行动也许是一句“窝里萨宁萨宁么事体伐?要帮忙伐?吾撒地方认得宁哦,要帮忙讲一嗓,勿要客气的。”,也许是从对过窗口用竹竿悠悠渡过来的一篮小菜,也许是早上相帮倒一只马桶,也许只是一个摇头一声叹息。不好说这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对于弄堂里生活的人而言,这是本能反应。这是一群群居的刺猬,不好靠太近,又不能离太远。
如果不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瑞平大概真的会娶对过的汪蓓蓓,他大概永远都不会晓得萧山的小县城里的伯伯、伯母其实是自己亲生的爹娘。如果不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瑞平爸爸会和瑞平妈妈大概会一起体面地把三条小黄鱼放到汪蓓蓓手里,等着这个全弄堂最漂亮的女生养一个大胖儿子或是女儿出来。如果不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唉!这是个蛮无聊的幻想。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没有什么能改变的。那些淡去的标语压在最深的箱底,那些迷茫的目光换作日后的沉稳。如果只是如果,它比肥皂泡更虚幻。
只是,那毕竟不是我能亲历的历史。小说再细腻,再真实,终有一丝丝的隔膜。我努力地参与到里头去,然而总归是要回到现实里来的,现实是,我的同龄人们不再记得那段历史,他们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又自以为理解。我走在他们中间,和走在被孩子们尖锐取笑的包围圈里的瑞平一样,孤立无援到了麻木的顶点。
这是本什么书啊,说一说啊
是拿破仑说的还是尼采说的?
有人记得却要忘记
有人想记得却不知从何记起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记得的
所以不需要觉得孤立
麻木这两个字似乎和你扯不上关系
好吧,那就算扯不上吧,反正已经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