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结束的地方
2008-1
浙江文艺出版社
[美] 保罗·奥斯特
175
韦玮
无
着泳装的漂亮小妞、冰淇淋的包装纸、一管管的防晒乳液、红色的飞盘在空中咻来咻去。这是梦里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景象,他闻得到它的奇和美,彷佛他的一部分已经知道自己超越了现实界限之外。一开始静默无声,是无语的静默,只有拍岸的浪和扑打着旗帜与遮阳伞的风。哪里的收音机放送起流行歌曲,一个女声在唱:“做我的宝贝,做我的宝贝,做我的宝贝吧!”…… 游走在生命边缘的潦倒诗人威利,身边只剩一只忠心耿耿的狗先生。 虽然他只能靠四条腿走路,不会说话,但他可以思想。这一对人与狗就像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一般,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经历了一场最后的大冒险,一起走向地图的那一方,迎接最终时刻的来临,并且期待在那个被称为“汀泊渡”的另一个世界相会……
(美国)保罗·奥斯特 译者:韦玮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1947年生于新泽西州的纽渥克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英文暨比较文学系,并获同校硕士学位。年轻时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不断尝试各种工作,甚至曾参加舞团的排练,只为了“观看男男女女在空间中移动让他充满了陶醉感”。 他早年的创作一直深受一些法国诗人及剧作家的影响,而《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则是他重新回美国文学传统的转折点。1990年他获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所颁发“莫顿?道文?萨伯奖”;1991年以《机缘乐章》获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提名;1993年以《巨兽》获法国麦迪西文学大奖。他的诗作与散文并均获得“艺术基金”的奖助。作品除《瓦提哥先生》、《月宫》、《没落之乡》等小说外,还包括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评论集《饥渴的艺术》及诗集《烟灭》。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语文。 90年代起,奥斯特并积极参与电影工作,除为华裔名导演王颖编写『烟』的剧本(《烟》于一九九五年的柏林影展中赢得银熊奖特别评审团大奖、国际影评人奖及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并与王颖合导了《面有忧色》(Blue In The Face)。1998年他更独立执导《桥上的露露》,他受蜜拉索维诺等演员的称许。他并且获选为97年戛纳影展的评审委员。目前与妻儿定居于纽约布鲁克林区。 2004年,《神谕之夜》(Oracle Night)在美国出版。 2006年10月20日,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奥维多获颁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1 骨头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长了。咳嗽在他体内潜伏了六个多月,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摆脱的机会了。缓慢,残酷,从来没有一次好转的迹象。从二月三日开始的肺部有气无力、充满黏液的咔哒声响,一直到盛夏时伴随着粗喘的痰液之舞和不规律的剧烈抽搐,这东西为自己构造了一个生命。这一切已经够糟糕了,但在过去的两周中,一种新的曲调慢慢出现在这首支气管乐曲当中——紧绷的、僵硬的、振动的——并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持续不断。每次发作,骨头先生都觉得有一些火箭从威利的肋骨里冲出来,他的身体要爆炸了。他猜下一步就是流血。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当最后关头终于到来时,好像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张开了嘴巴开始放声歌唱。骨头先生亲眼看到了。他站在那条连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马路边,看到威利在手帕上咳出一些可悲的血块。就在那时那刻那个地方,他立刻意识到,连一丁点希望都没了。死亡的气息已经降临到威利·基·圣诞身上。就像太阳是云中的一盏灯,每天都必然会熄灭再燃起那样,大限将至了。 一条可怜的狗又能做什么呢?从他还是一条小狗时起,骨头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现在,他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渗透在每一个思绪、每一个回忆、这地球上和空气里的每一个微粒里。习惯很难改变。毫无疑问,那个“狗改不了吃屎”的谚语确实有些道理。但让骨头先生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深感恐惧的并不只是出于爱或者迷恋。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把威利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可能这个世界也会随之消失。 这就是骨头先生在那个八月的早上所面临的窘境。当时他正跟着病恹恹的主人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闲逛。一条孤单的狗不比一条死狗好到哪里去。一旦威利呼出最后一口气,骨头先生除了死,也没有别的期望了。威利已经就这个问题教育了他好多天,骨头先生对整个操练过程谙熟于心:怎么躲开捕狗人和治安官,警车和没标记的车,还有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社会来的伪君子。不管他们对你说什么甜言蜜语,“收容所”这个词都代表着麻烦。一开始是网和麻醉枪,接下来就是笼子和荧光灯构成的噩梦,最后用毒针或者毒气结束这一切。如果骨头先生是什么名贵品种也就罢了,也许还能参加选美比赛,最后被另一个主人买走。但是威利的这个老伙计却是好多品种生出的杂种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猎狗,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更糟糕的是,他那身脏兮兮的破毛皮上突起许多带刺的毛球,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眼睛里永远布满忧伤和绝望的血丝。不会有人想救他的。正如这个无家可归的吟游诗人喜欢说的那样,结局早已注定。除非骨头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个新主人,否则,他注定会成为一条被遗忘的杂种狗。 “即使那吓人的枪没有干掉你,”在那个雾蒙蒙的巴尔的摩的早上,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灯杆上接着说,“还有成千上万的东西能干掉你。我警告你啊,独行侠,你得给自己找点新本事,不然你没几天可活了。看看这个无趣的小城吧,每条大街上都有中餐馆,你别以为你在他们门口晃荡的时候不会有人流口水,那是你太不了解东方的烹调风格了。他们把狗肉当成美味,伙计。那些大厨围捕流浪狗,然后就在厨房后面的小巷里把狗宰掉——每星期杀上十只、二十只、三十只。他们会把狗肉在菜单里写成鸭肉猪肉什么的,但圈里人知道什么是什么,那些美食家都不傻。所以当你在哪个中餐馆前摇头摆尾的时候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变成一个大盘子里的蘑菇鸡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骨头先生?要清楚谁是你的敌人——然后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骨头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对他说的话。从他记事起他就能听懂,到现在,他已经和任何其他在美国大陆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一样,很好地掌握了“英古利希”。当然,这是他的第二语言,和他的母语完全不同。尽管在发音方面还得多加练习,但他已经基本掌握了句型和语法的每一个细节。对于一个有骨头先生这样智商的动物来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许多狗都能掌握使用人类语言的实用知识,而骨头先生的优势就在于他有一个不把他当成低智商动物的主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好伙计,再加上骨头先生不仅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况,威利是那种沉迷于自己声音的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恋语狂,从早上一睁眼开始,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几乎一直都在不停地说话。所以骨头先生对这种“方言”这样应对自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到最后,最应该奇怪的是他自己没学会怎么说话。这并不是他不努力,而是造化弄人。天生那副嘴巴、牙齿和舌头的构造,骨头先生注定最多只能发出一些狂吠、哈欠、号叫,讲一些口齿不清意义不明的言论。骨头先生为这些完全不成句的噪音感到苦恼,但威利总让他说完,而且到了最后,“说”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头先生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他说的时候,主人总会洗耳恭听,看着他的伙计努力成为人类的一员。那个时候如果你看着威利的脸,你就会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听懂了。 但是,在那个阴沉的巴尔的摩的星期天,骨头先生却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们正度过在一起最后的几天,或许是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没工夫去长篇大论和拐弯抹角了,没时间去搞往日的那些恶作剧了。有些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目前的这种处境需要他看好自己的舌头,并且表现得像一条忠诚的好狗那样。威利猛地拉紧他的项圈时他没有反抗,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他没有抱怨,他没有到处去闻母狗的味道,他没有停下来在每一个路灯杆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紧紧跟在威利身边,跟着主人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找那条叫做卡尔佛特的街道。 骨头先生本质上也不讨厌巴尔的摩。这个城市不比他们这些年流浪过的其他地方味道差。即使他明白这次旅行的意义,他想到一个人会选择在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度过残余不多的生命,他仍然会很感伤。狗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会跟这个世界讲和,然后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死去。在死前,威利还有两件事要办,而他固执的天性让他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那个人的名字是比·斯万森。他们最后得知的关于比·斯万森的消息是她住在巴尔的摩,所以他们就到巴尔的摩来找她了。可万一威利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骨头先生就要在这个充满蟹肉饼和大理石台阶的城市里独自闯荡了,到那时候他该怎么办呢?其实打一个电话,半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但在威利的哲学里有一种偏见:非常重要的问题决不能靠打电话解决。和拿起那个小东西跟一个没法见面的人讲话相比,他宁肯不停地走上几天。所以他们现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来到这儿,手里连个地图也没有,只能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寻找一个可能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在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两件事情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极其重要。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分开解决它们了,所以威利只能采用一种切萨皮克策略——一种一石二鸟的终极策略。第一件事情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他那裹着毛皮的朋友找到一个新主人。第二件事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他的手稿交给可靠的人。刚才,他把一生所有的作品都塞进费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终点站的一个储存柜里,离他和骨头先生现在站着的地方往北有两条半街区。钥匙就装在他的口袋里。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值得完全信任的人来接收这把钥匙,否则,他所写过的每一个字句都会被毁掉,像那些无人认领的行李一样被当做垃圾扔掉。 在改姓圣诞之后的二十三年里,威利写满了七十四个笔记本。这些作品包括诗、故事、散文、日记、诙谐短句、自传体冥思,还有一篇未完成的史诗《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妈妈那间布鲁克林公寓的厨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从四年前妈妈去世之后,他不得不露天写作,经常是一边拼命把思绪集中到纸上,一边跟公园和暗巷里的恶劣环境作斗争。在心中最隐秘的角落里,威利对自己并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个怪人,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同时,他也知道许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这堆笔记本当中,就凭这一点他就可以昂首挺胸。也许如果他吃药的时候更小心一点,或者如果他的身体稍微强壮一点点,或者如果他对啤酒、烈酒和酒吧里的吵闹声不那么迷恋,他也许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这种可能性太大了,但现在已经没时间去懊恼后悔。威利已经写下了他所能写的最后一个句子,写到了分秒不剩。储存柜里的文字是他所能展示给自己的一切。如果那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比·斯万森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威利知道希望很渺茫,但他确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很久以前,当威利的世界还很年轻时,斯万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师。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勇气想要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他还叫威廉·古尔维治,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六岁男孩,喜欢看书,迷恋比波普爵士乐。她曾把他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给他早期的作品以极大的赞赏,大大超出了那些作品本身的价值,以至于他真以为是美国文坛的明日之星。她这样做是对是错都不是问题,因为在那个阶段,希望永远比结果重要。斯万森夫人发现了他的才能,在他稚嫩的灵魂中看到了灵性。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成不了大器,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米德伍德高中的其他低年级学生都把斯万森夫人看成一个矮墩墩的四十多岁妇女,当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她胳膊上的肥肉来回弹跳颤抖着。威利却认为她很美。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只不过披着人类的外衣。 但是,当学校秋季开学的时候,斯万森夫人却离开了。她丈夫在巴尔的摩找了个新工作,而她不光是个老师,也是个妻子。她除了跟随斯万森先生离开布鲁克林以外,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这对威利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也不是太糟,因为尽管他的导师远在天边,却并没有忘记他。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斯万森夫人和她年轻的朋友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联系,不断地阅读他寄来的手稿并给他评论,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查理·帕克的老唱片,还给他介绍一些杂志让他开始发表他的作品。在威利毕业那年,她的一封充满感情、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让威利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斯万森夫人就是他的缪斯女神,是他的保护者,是所有的幸运迷咒,这一点在威利的生命里具有无限的意义。但接下来却是那个精神分裂的疯狂的一九六八年,可能是走火入魔或者精神过于紧张,他被关进医院,接受了六个月的休克疗法和精神病药理学疗法之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威利了。他变得失魂落魄。尽管他仍然在痛苦中坚持写诗和故事,不管生病还是健康都继续他的写作,却很少给斯万森夫人回信了。理由并不重要。也许再和她联系,威利会感到尴尬。也许他有点心烦意乱,脑子里装满了其他的事。也许他不再信任美国邮政服务了,不再相信邮递员从不偷看他们的信。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的原因,他和斯万森夫人曾经长篇大论的书信来往渐渐停止了。接下来的一两年,他们偶尔互相寄几张明信片,然后变成那种商店里出售的圣诞卡,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同时停止了写信。从那时起,在他们之间,连一个音节都没有交流过。 骨头先生知道这一切,这些正是他担心的事情。十七年过去了。杰拉尔德·福特那个时候已经当上了总统。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出生也快十年了。威利是在跟谁开玩笑呢?想想在这些时间里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吧。想想在十七个小时或者十七分钟里发生的变化吧——更不要说十七年了。至少,斯万森夫人可能搬到了别的地方。这个老女孩现在应该快七十岁了,如果不是老态龙钟,或者住在佛罗里达州哪个活动房车停车场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她已经死了。那天早上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游逛的时候,威利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妈的,他说,这是他们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机会,既然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啊,威利。他曾经讲过那么多故事,他曾经用那么多种声音说话,他忽东忽西随口乱诌,骨头先生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句。面对威利·基·圣诞这样复杂又古怪的人,很难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骨头先生能肯定他亲眼所见的事情和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但他和威利只在一起待了七年的时间,这之前三十八年的事情他只知道个大概。如果骨头先生小时候没有和威利的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整个故事就会被蒙在鼓里了。听古尔维治太太讲那些关于她儿子的话,把她的说辞和威利的说辞相权衡,骨头先生已经能够拼凑出一幅合理的图画,了解到在他到来之前,威利的世界是怎样一番景象。有许多细节都丢失了,也有许多细节混淆不清。但是骨头先生能把握这一切,他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样、不是什么样。 比如说,那段日子并不富裕,也不令人欢欣鼓舞。更多的时候,这所房子里弥漫着酸楚和绝望的气息。想想这个家庭来到美国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事情,首先,大卫·古尔维治和艾尔·珀尔马特能有一个儿子已经是奇迹了。威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住在华沙和罗兹,从一九一0年到一九二一年,他们共养育过七个子女,威利的父母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对。只有他们两个的前臂上没有被文上数字,也只有他们两个最终幸运脱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往后的一切一帆风顺。骨头先生曾经听过许多让他毛骨悚然的故事。
一只小狗,一个落魄诗人,一次世界尽头之旅……本书是村上春树最推崇的美国小说家,也是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的保罗·奥斯特的首部畅销小说。 游走在生命边缘的潦倒诗人威利,身边只剩一只忠心耿耿的狗先生。虽然他只能靠四条腿走路,不会说话,但他可以思想。这一对人与狗就像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一般,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经历了一场最后的大冒险,一起走向地图的那一方,迎接最终时刻的来临,并且期待在那个被称为“汀泊渡”的另一个世界相会…… 这本小说让我们在自己悠然的世界中猛然觉醒,感获另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保罗·奥斯特小说的魔力,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水远存在着一个纯净而清明的角落供我们停歇。保罗·奥斯特的确是美国当代少见而且最具创作力的作家。 ——《波士顿环球报》 除了吸引人的故事之外,保罗?奥斯特在这部小说中,对于文字的掌控技巧,实在完美得令人惊叹!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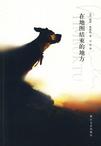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