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苏珊娜
1970-1
合肥九歌(原安徽文艺
阿罗娜·基米
291
邹红云,顾慧琤
无
《哭泣的苏珊娜》作者阿罗娜·基米毕业于以色列拉马甘市的BeitZvi表演艺术学院(BeitZviAcademyforPerformingArts),当过话剧和电影演员。1993年,她开始写剧本、散文,担任过记者和戏剧导演。1996年以来,她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儿童书。 《哭泣的苏珊娜》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9年,当年就在以色列获得了该年度的“伯恩斯坦最佳长篇小说奖”。“伯恩斯坦奖”的宗旨就是奖给当年最具独创性的希伯来文小说。之后,该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还荣获了法国2002年度WIZO奖。至2006年为止,该书已被译成了12种语言,分别是丹麦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葡萄牙语、芬兰语、希腊语、德语、西班牙语、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作者因此成为扬名国际的新锐作家。 初读此书,是在2003年上半年。当时我们并不知晓有关作者的这些情况,纯粹是为此书本身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所吸引。少女时期丧父的女主人公苏珊娜一直生活在母亲的羽翼之下,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她颇具艺术才能,敏感而多虑。堂弟尼奥的到来,使她在心灵上产生了什么变化?她是否能一点点走出母亲给她设下的爱的牢笼?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以第一人称对苏珊娜所进行的大段大段细腻的心理描写,让读者很容易进入她的内心,以她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真切地感受她的心路历程。作者语言生动诙谐,比喻形象别致,让人经常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尼奥在谈话中形容苏珊娜“生活在自己的壳里,像颗没成熟的珍珠”。作者在描写人物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书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和鲜活的个性。作者描写场景细致,这大概跟她学过戏剧当过剧作家有关,读起来仿佛历历在目,犹如观看电影一般。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心理的小说,但它涉及了许多方面,如美术、音乐、文学、电影,以色列政治文化风俗以及希伯来语等等。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功课,想办法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阅读量之大远远超过《哭泣的苏珊娜》篇幅,虽然辛苦但受益匪浅。另外,书中有一些地方很难实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如由谐音引起的误会,及多处的押韵等,在翻译中让我们推敲很久,我们尽自己所能,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风味。必须一提的是,我们有幸得到了加拿大籍犹太裔朋友LouiseMiller和其儿子MichaelMiller热情而耐心的帮助,他们使译者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更为透彻,书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希伯来语则完全依赖他们的相助才得以完成,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以色列姑娘苏珊娜从小失去父爱,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对她的一切几乎包揽,又由于她和当时的总理(拉宾)同姓,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渐渐不愿和别人打交道,仿佛筑起了一道围墙。可当她那长得帅气、充满才气的堂弟尼奥来到她的身边后,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俩人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这时,苏珊娜的母亲对此又进行了干预,并对他们的友谊提出了质疑,使得苏珊娜陷入了更加痛苦之中。
作者:(以色列)阿罗娜·基米译者:邹红云顾慧琤 阿罗娜基米(AlonaKimhi)于1966年出生在前苏联,1972年随她的家人来到以色列。现居住在特拉维夫。她在贝特兹夫学院攻读了表演学艺术后,开始在剧院里表演并开始演电影。1993年,她开始专注于写剧本,抒情诗和文章。1996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我,阿纳斯塔西娅》,被ACUM图书奖授予年度奖励。她的第一本小说《哭泣的苏珊娜》,出版于1999年,收到以色列伯恩斯坦年度最佳小说奖和2002年法国WIZO奖励。
译者序并非沾亲蓝花瓶葛兰菲迪希?韦奇伍德诗人和圣母卡秋莎男人们的神秘并非情人滴血肚脐海的女儿,大地的女儿八月的热浪气味
并非沾亲 大家对我的名字苏珊娜·拉宾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再问我与那位大人物是否沾亲带故。好在我的生活并不真像是从石缝中进将出来的那样,一下子有许多的人要结识,也就几乎无须做这方面的澄清。自然有时会有些例外情况,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起关于我的姓氏变迁兴衰和演化形成的故事,及其后者的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解释的这个担子落到了我母亲坚实的肩上,她担待着,内心充满着履行职责的自豪。我必须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过程,在这种时刻我对母亲的钦佩真是无以言表。有些情况下她往往会夸大其词,造成戏剧般的紧张以及细节上的堆砌,引得其听众直后悔自己最初颇带礼貌的好奇。因此,总体来讲,我的姓氏尽管有着民族的荣耀,却可以说主要是没完没了地造成误解和尴尬的源泉。 当然也会有些例外,虽然到头来只是使得总的法则更加突出,却可以产生某些好处。比方说,前些时候,钢琴家拉杜·鲁普来到我国,预定要在曼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尼哈玛建议我们仨一起去。自然,我们也邀请了阿曼德一同前往,可他说不喜欢肖邦那些波兰伤感音乐。阿曼德也是母亲的好友,通常有文化活动他们都一起参加,可阿曼德——让他听萨第、德彪西,甚至勋伯格这些造诣极深的作曲家的音乐才会愿意,否则——哈哈——就别浪费时间了。 不管怎样,阿曼德拒绝后,我们便乘61路去了特拉维夫,前往“再看一回”售票处,到了那儿母亲开始伸手到包里摸钱夹,此时却发现演奏会的票已经售空。卖票的妇女建议我们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如有人退票她会通知我们,虽然她自己并不相信会有此等事,因为以色列人对拉杜很是着迷。于是,母亲给了她的姓名,艾达·拉宾,那位妇女马上问她与总理拉宾有否亲戚关系,还没等母亲开始她惯常的解释,尼哈玛插进去说:那并不重要吧,是亲戚又怎么样?票子会突然从树上长出来?这个全凭关系的国度!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她把我们拽了出来。 而真是奇之又奇,就在第二天早上,售票处打来电话通知我们有三张座位在第三排中间的票。三,三。我自己正好是三十三岁。因此,一定意味着什么。 我老是关注于这样的巧合,尽管尼哈玛和母亲都说只有愚昧的原始人才这样做,除此之外,还有的那就更糟糕了,是那些妄想狂们,他们认为是外空或什么地方在向他们发信号。然而我并不就此打住,即使我想打住也办不到,因为我渴望懂得事物背后的规律,即便是用奇特的方法。 顺便说一声,母亲竭力与尼哈玛争辩,认为我们是靠诈骗得到的票子,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本家,可尼哈玛撅起嘴巴说:艾达,行行好吧,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母亲当然就朝她吼起来,像她一贯那样:尼哈玛!那是纳粹的口号!可尼哈玛说你可以向任何人学习,更何况德国人,他们毕竟是有文化有文明的民族。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母亲无法赞同这个同样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尼哈玛这番很成问题的主张,对她狠讲了一通有关邪恶的大道理,弄到最后尼哈玛快哭了,说母亲从不理解她,不然就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她,这都是因为母亲是大屠杀后的妄想狂,要愿意的话就去把票退了,我们不去听肖邦,就待在电视机前算了。她这样说母亲真是蠢,因为被临床诊断为大屠杀后妄想狂的实际上恰恰是尼哈玛自己,她疑心所有人都怀有谋杀、犯罪和邪恶的意图。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她们援引每个朋友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妄想狂的例子,证明自己针锋相对的看法,直到最后因为时候不早了只得和好。她们从不彼此交恶着上床睡觉,这样就不至于做噩梦,第二天早上醒来也不至于心情不好。尽管被迫和解,这件事却大大地破坏了气氛。而当我们打扮齐整、芳香四溢地去听音乐会时,心里还是非常欢喜。至于如何得到票子,则真的并没什么关系,特别是像与尼哈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究竟也只是巧言夺理,没什么可烦恼的。 最近几个星期,关于我们姓氏的问题出现过两次,让我感受到了变化和多事。有时候,几个月里也不会有这档事,我那奇特的姓名——苏珊娜·拉宾——静静地存在着,毫不令人吃惊,被我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以及显然连掌管姓名的神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事情还是来了。头一次是我们收到通知说有封挂号信。和母亲一起赶到当地的邮局,发现在那儿工作的是位新职员。纵然长着张讨厌的胖圆脸,我还是喜欢她的表情,因为她张嘴吐掉灰兮兮的小块口香糖时,歉疚地朝我们笑了笑,露出上下门牙间宽宽的缝。这立马显出了她的可爱,使得我和母亲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对这个有趣的发现都很欣赏,好像用我们秘密的语言在说:她是不是很可爱?这位新职员看了看我们的通知就到那些挂号邮包和信件中去搜寻,吃力地摆动着她宽阔而低悬的臀部。当她回过身来将信交给母亲时又可爱地咧了咧嘴:给,拉宾,请签名。紧接着,她突然闪现出一丝怀疑,皱起了眉头,带着新的兴趣打量着我们:你们和总理是不是亲戚?母亲历来视澄清真相为人生中一大使命,马上开始解释说我们这个拉宾并不是像任何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某个普通的拉宾诺维兹的希伯来语形式,而是一个外国姓氏拉宾尼安的缩写,这是我父亲的姓氏。他于三十年代出生在敖得萨一个有着不寻常历史的犹太家庭:他的祖父从波斯去那儿出差,与祖母坠入爱河就留在了俄罗斯,那儿立刻因他那不寻常的姓氏引起了骚动。 母亲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准备好讲述那段有趣的经历——复述我们的生活史,这样的事随着一年年的过去越来越稀少了。她用下巴示意我从包里把香烟拿出来给她,没等抽完第一口烟,就已开讲起故事来了,同时像龙一样把烟从鼻孔中喷出来:当阿弗兰穆,也就是我父亲移居以色列参军时,拉宾是他的指挥官。他便把姓缩短成拉宾,一则出于对他长官的崇敬,二则不会带有太重的离散犹太人的味儿,这在当时是时尚。数年过去,父亲加入了玛派党,即以色列工党,一次他甚至去拉宾的宅邸拜访了他,而他自己从未立志从事政治生涯,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太温和,性格软弱。这时,那位新职员打了个哈欠,看看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可以把她从余下的故事里解救出来,然而邮局里空空荡荡。母亲并不把这粗鲁的举动放在眼里,继续往下讲。她的——也就是指我的——父亲,她说,总是蛮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那可对他没好处。当艺术家可并不只是过得快活,喝酒,还有——原谅我用这字眼,搞女人。这可不容易。你还要有那样的性格。结果他成了室内剧院(ChamberTheater)的书记员,塞了这孩子——也就是我——满脑子的希腊神话和诗歌。我自己——也就是我母亲——在本一西门(Ben-Shemen)基布兹长大,接受的是很像样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农艺的教育,却并没让各种蜜蜂叮在我帽子上。即使可以说我的——也就是她,我母亲的——生活并非一片美好,父母还是把我送上了离开德国的最后一班火车,而他们自己、我的大弟弟特奥,还有小弟弟阿哈隆,那个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都在布痕瓦尔德遭到了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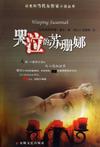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