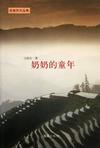奶奶的童年/高新民作品集
2011-12
文汇出版社
高新民
146
《奶奶的童年》主要内容包括:《老姑》、《祝万昌麻饼》、《佐藤先生》、《奶奶的童年》、《足浴》、《复婚》、《律师》、《厨娘》、《月嫂》、《退休》、《空巢老人》、《富人的银行》、《租房》、《吃馄饨》、《蚁族》、等。
高新民,1947年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毕业于皖南医学院,进修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曾作为访问学者赴俄罗斯、新加坡研修眼科。所著《葡萄膜病》、《糖尿病性眼病》等眼科专著均已出版。业余爱好文学,在报刊杂志发表数百篇诗文,其诗集《启明集》已在香港出版发行。随笔《医林漫步》由中国当代出版社出版。游记《西欧旅痕》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凡人旧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系中华医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老姑祝万昌麻饼佐藤先生奶奶的童年足浴复婚律师厨娘月嫂退休空巢老人富人的银行租房吃馄饨蚁族香菊动车组C2C伴读一对小鸟拆迁哈佛学子肖老师
奶奶的童年 小强活泼天真也很可爱,快上三年级了,每天吵着要吃冰激凌、巧克力和布丁。他的奶奶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看着孙子这么高的生活要求,每每摇头叹息“现在的孩子都惯坏了,生活条件这么好,还是不知足,唉,我们小时候……”,这句话实际上成了小强奶奶的口头禅。这天是星期天,小强的爸爸、妈妈开着自驾车,到乡村去度周末,是到乡下的葡萄园采摘。奶奶又叹气了“现在的孩子真是在天堂里生活,唉,我们小时候……”,小强对奶奶的口头禅都听烦了,星期天的下午,小强特意拉着奶奶要她讲小时候的事情,奶奶说: 那是1946年,山城的江滩上传来了一阵阵婴儿的哭声,循着哭声走去,河边有一个被旧衣包裹的婴儿在啼哭,那声音嘶哑而凄凉。围观的人们有的轻声叹息,有的无奈地咂嘴,“多么可怜的孩子”。有的老婆婆还偷偷地抹泪,“这孩子的父母真心狠,亲生的孩子也忍心扔掉。”有人这样说。“哪个父母不心痛自己孩子。也是没有办法啊!”有人无奈的说。但那时这些人都穷,没有人能领养这孩子,那时小山城也没有儿童福利院,这弃婴除了生活稍微好一点的人愿意抱养外,只有当时的基督教育婴堂收养了。山城的育婴堂由基督教堂办,这里已收养了几十个遗弃的儿童和残障儿童,由教堂请的保育员抚养,这个河滩边的弃婴就被育婴堂收下。因婴儿身上没有任何标记和文字东西,也没有姓名,育婴堂只能登记收养的时间,估计婴儿三个月大小,没有残疾,估计这孩子的父母并不想以后再认这孩子,也许他们是真正无力养活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没有姓名,皮肤也较黄,育婴堂临时给取了名字,叫“黄皮”。这孩子是女婴,黄皮这个名字实在难听,但在育婴堂谁还管这些,只要好叫就行,谁还管好听不好昕。 黄皮在育婴堂一天天长大,开始过上了生活有保障的集体生活,无忧无虑;在嬉笑与哭泣、打闹与玩耍中长大。从小认识的是育婴堂的“妈妈们”,这些孤儿从小就叫保育员为妈妈。那么多的小朋友,都是兄弟姐妹。 1953年,小黄皮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督教育婴堂要解散了,残障的孩子转入政府的福利院收养,健康的儿童则由无子女的社会人士领养,开始小黄皮不知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力。她终于被乡下一对没有子女的父母领养走了,领到一个叫溪头的小山村。当小黄皮被乡下养母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向山里走去时,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她从小没有离开过育婴堂的妈妈们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一对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生活。小黄皮越想越伤心,从育婴堂到溪头三十几里路,是在养母的背上背去的,也是在养母的背上一刻也不停地哭去的。恐惧、无奈、陌生的生活就要从头开始了。养父养母拿糖饼哄她,又买新衣服给她穿,小黄皮渐渐地不哭了,但乡下的土语,打赤脚的小孩,慢慢地成了小黄皮的朋友和现实需学习的语言。没有多久,小黄皮就有了平生第一次的正式名字:许圆珍,因为养父姓许。小圆珍背上书包和农村的小朋友一起到祠堂里的村小上小学了,现在有了自己出生的时间,1946年3月6日。1946年是被遗弃后被人收养的那年,月、日则是被许家收养的日子,小黄皮从此有了一个被拼凑出的出生年月,和一个被许家取的正式的名字。 许家无儿无女,生活在农村也算一般中等人家。拾柴、烧火、洗碗、放牛,这就成了圆珍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早晨,父母下地干活,圆珍的早读是在灶门口烧火开始的,一边烧火,一边读书,她很用功,也很爱读书。养母是没有一点文化的农村妇女,早工回来,看见圆珍在灶前念书,就大声地斥责:“清早起来就在灶前念经,嘟嘟噜噜念什么经?”养父是有些文化的人,年青时也在外面闯荡过,有些见识,此时转转弯子,“孩子喜欢读书不是什么坏事。”父亲开口了,母亲也住口了。小圆珍的读书就是这么开始的,圆珍还很小,皖南农村的锅台比较高,洗碗够不着,只好站一个凳子上将饭后的碗筷洗涮干净,再站在凳子上将这些碗筷放进碗橱。放了学或星期天就是小圆珍要做的另一个“功课”——放牛。因为那时牛还没有人合作社,自家的牛要自家放,小圆珍牵着头牛到后面的山上放,一边放牧,一边拾柴。天快黑了小圆珍将拾来的两小捆柴放在牛背上,骑着牛带着柴回家。放牛和拾柴也是小圆珍快乐的时候,这时听不到妈妈的唠叨,也看不到爸爸那冷峻的眼神,可以和其他放牛的小朋友一起打闹,自由自在地玩耍和无拘无束地哼唱山歌。后来合作化了,牛都人社了,放牛的事才不用做。 圆珍也有十分开心的事情,她会自己扎辫子了,因为妈妈从来不帮她梳头,更不要说扎辫子,她是学着别的女孩子样子自己学会扎辫子的,这辫子是编在两个耳朵边。虽然是没式没样,但毕竟自己会扎辫子了。圆珍在小学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又不太顽皮,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她的同学中有一个叫腊八,一人叫迎秋。同学开心的叫“腊八日圆珍吃泥鳅。”实际上是取一个同学的名字为时间,一个同学的名字取谐音改为“泥鳅”这道菜,让圆珍享用,无形中圆珍的地位成了美食的享用者。她在同学眼里还是被看得很高的。 农村的扫盲活动开展起来了,学校教师布置任务,回家要教不识字的爸爸妈妈读书。圆珍非常认真地用粉笔在房门上写上“门”字,在窗户写上“窗”字,在灶上写上“灶”字。虽然妈妈不愿意或没有时间学写字,但没有责骂圆珍,只是笑笑罢了,因为她知道识字的好处和孩子的一片好心。 圆珍也有自己的理想,想要两个橡皮筋的圈扎辫子,橡皮筋扎辫子,既好看又方便,可是她只能用细绳扎辫,她很羡慕有橡皮筋扎辫子的女孩。这农村的橡皮筋也不那么方便容易买到,只有货郎担进村才可以。常来溪头的有两个货郎。一个外号叫“伤脑筋”,一个外号叫“烦死人”。因为这两个货郎各有这么一个口头禅,所以分别得了这两个雅号。有一天“伤脑筋”又摇着拨浪鼓进村了,大人和孩子们高兴地叫起来,“伤脑筋”来了。圆珍因为和母亲讲好才拿着鸡蛋向“伤脑筋”换了“牙粉、牙刷”,顺便也给自己换回了几个橡皮筋,这时圆珍也有扎小辫的橡皮筋了。 村小只读到四年级,五年级要到十里外的大村子去读。一年级到四年级叫初小,五年级六年级叫高小,圆珍升人高小每天上学要走十里路,放学回来也要走十里路,十里是山间小路,有石板路,也有鹅卵石路,杂草丛生。小孩子有时有鞋,有时打赤脚,赤脚走石板路,夏天烫脚板,孩子们有时只好在石板路上一跳一跳走。鹅卵石硌脚,一边走,一边选择下脚的地方,孩子们的脚都咯出厚厚的老茧,就这每天二十里路,圆珍完成了高小教育。 ……
至此阿仙夫妻子女一家四口,分散四地打工,一年相聚的只有过春节,春节是团圆的节日。春节一过一家人又各奔东西,挣钱谋生,家中就剩下阿牛的父母两个老人种那仅有的一亩多责任田了,这是大多中国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写照。 ——《厨娘》 这个屯本来就是北京城郊的村,这几年改革开放,农民致富,自家的房子也越盖越大,越漂亮。这多余的房拿出来出租,开始还是一间一间的租,后来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现在人口比过去一个村的人口增加了十来倍,每天早上出去的都是上班的毕业生,每天晚上回来的是下班的大学毕业生,村里晚上可以听到吉它的弹唱声和流行歌曲的传唱声,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是一个群住的部落,这就是时常调侃的“蚁族群住的部落”或者叫“蚁族”。 ——《蚁族》
圆珍升入高小每天上学要走十里路,放学回来也要走十里路,十里是山间小路,有石板路,也有鹅卵石路,杂草丛生。小孩子有时有鞋,有时打赤脚,赤脚走石板路,夏天烫脚板,孩子们有时只好在石板路上一跳一跳走。鹅卵石硌脚,一边走,一边选择下脚的地方,孩子们的脚都咯出厚厚的老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