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стория Уродства
2007
Слово
Умберто Эк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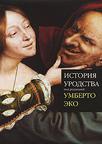
一种情色与哲学的结合。
普通人生儿育女,而培养高贵精神的人则生产了美与智慧。
后世幻想那是美善的时代,其实从但丁直到现代,都受这些恐怖情绪的影响。
圣奥古斯丁:我们在论述时选择方便的节骨眼上沉默,使这些沉默像标点一般突出我们的论点。我们既然能够如此,上帝不是更善于选择方便的方式使某些事物有所欠缺吗?……因此,没有任何自然是恶的,只要它是自然……
后来的传统称之为”敌基督“。
7—8世纪的犹太密宗说,她是后来后来变魔鬼的亚当的第一个妻子。
这个世界的王。
公元520年的马赛克,上面把魔鬼表现成红色天使。
马丁·路德:吻我屁眼吧。
巨大和无节制。
曼陀罗。
库克罗普斯。
每下愈况。
贺拉斯:普利阿姆斯的哀歌。
耶稣和大笑成为争论好几百年的问题。
吕特伯夫(13世纪):俗话说得好:”逼过猛,得到屎“!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各位一清二楚了吧。
罗森克兰茨《丑的美学》:浮夸。
吊诡。
丑在某个意义上得到救赎。
拉伯雷:括约肌(也就是说,班努赫鸠的屁眼)……而且这也是约翰·邓斯·司各托的见解。
同时,连傻瓜也已经从嘉年华角色变成一种哲学象征。
克罗齐《极为机敏害羞的贝尔托多》:总而言之,他彻头彻尾是那耳喀索斯的反面。
拉伯雷有个同时代人,是老布鲁盖尔,拜他所赐,农民的世界,连带农民的节庆活动,其粗俗与畸形成为伟大艺术的题材。
莎士比亚《亨利三世》:除了切鸡吃鸡,他还会什么干净利落的勾当?他会耍什么聪明,除了装巧逞能?他有什么巧妙能耐,除了作奸为恶?他做什么恶,除了恶事做尽?他值什么,除了一文不值?
到文艺复兴时代,猥亵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表现人体的时候,生殖器外露不会再令任何人难堪,而是被视为美的要素。作家,如阿列提诺( Aretino ),则颂扬先前认为不堪启齿的事(时至今日,我们这本书还不宜摘录那些文字)。
在17和18世纪的放纵文学里,萨德……Well you know...
在19世纪晚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及20世纪前卫运动产生的许多文学里,猥亵成为主角,目标则是拆毁自以为是者建立的禁忌,鼓励人接受肉体的一切层面。
罗森克兰茨:漫画是丑在美学上的救赎(斯威夫特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形式)。
泽德麦尔《失去的中心》(1948):反对讽刺漫画:在现代艺术里,被扭曲者不再戴着人的面具。有识者认为这些意象是可怕的讽刺,其实这些意象是在艺术家心里最深的黑暗深渊里产生的。
德尔图良:依照《圣经》,美貌的吸引力和出卖身体每每是同一回事。”
马拉提斯(1世纪)《格言集》:维杜丝提拉,唯一有办法插入你那阴道的,是丧礼里的蜡烛。
德尔图良《论女人的衣着》。
有时候,这种反女性的谩骂是对13世纪意大利“甜美的新风格”(dolce stil novo)的反动。
薄伽丘《科巴丘》:女人的本性:(还是不要这个也许吧)她会风姿优雅地以法国作风把奶子甩过肩膀)。
杜·贝莱(16世纪)《懊悔》:还有那里,为了庄重,我不可形诸言语的!
龙萨(16世纪)《给艾伦娜的十四行诗》:叶芝《当你老了》
门多萨(16世纪)《自以为美丽的老女人》:阿东扎太太,你三乘以三十岁了,你头发不过三根,牙齿单单一颗,胸脯如蝉,至多只像蜘蛛网做的。你穿的衣服里,藏着我在你额头上看得到的皱纹;你的嘴颤摇如一座桥,而且宽似两扇门。你唱歌像青蛙,又像山鹬,你的指爪如尸体,你看来挺像一只仓号鸟,你发臭如等着腌渍的鱼,以你那佝屈的山羊背,你在我看来像拔了毛的鸡。
反彼特拉克主义。
在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再次看到一些省思质疑对丑的谴责。以男人之丑来盛赞女人之美。
克维多《世界主日》(1612)使我终于对女人恶心到了。2013年9月14日凌晨……
到了墨菲斯特菲利斯,我才醒悟过来,这本书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翻译的。
话说回来,几乎可以说是浮士德要见魔鬼,而不是魔鬼来引诱他。因此靡菲斯特是魔鬼的第三个变体的先声。
到20世纪,他彻底变成“世俗的”。这一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帕皮尼(Papini)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便知。
无名氏《世界的运行者》,22.391-22.398(14世纪):基督降临的时候,光辉万丈,以至于面对主的强大的光的时候,敌基督将会满怀惧怖,他害怕基督,吓得五分之一脏腑从他屁眼倾泻而出,不胜羞耻,浑身恐惧和痛苦交加,就这样死掉,全身沾满自己的大便。
朱斯蒂《圣安布洛斯》(1846)对敌人的敬意已是美而非丑了,大将之风啊。
隆布罗索《白人与黑人:人类种族之起源与变化》(1871):欧洲人的头颅与众不同之处是其和谐令人叹为观止……他有中国人的扁脸,而兼有黑人的凸脸。
白人的文明使命中最常见的就是对非洲人的无情刻画。
弗莱明《来自俄国的爱情》(1957):苏联的女同性恋:关了灯,过来,坐到我身边。我们两个得好好认识认识。
阿普列尤斯(125-180)《金驴》:我那一根变太大了!
第206页15世纪《莫林的故事》这幅画魔鬼摸着……
卡尔达诺(Cardano)其说成为现代精神病学诠释的先声。
有个伪撒旦信仰的案子值得深思,就是德莱斯(Gilles de Rais)。是魔鬼驱使人残忍,还是一股天生的残酷倾向使人想象和魔鬼有交道,用以自圆其说,用以自我亢奋。我想是主客一体,主体间性吧,红宝书。
爱伦·坡有一个把猫折磨至死的故事,想起了“海边的卡夫卡”,艾柯便自己跳了出来。才刚227页,过了一半多点点,沉不住气了。
萨德《尤丝蒂娜》(1791):我童贞的裂伤只是我在这场攻击里遭受的最小痛苦。
不过艾柯的《昨日之岛》(1996)确实不错,以虐待狗的实验来测试经纬度。
爱伦·坡《黑猫》(1839):哲学不曾讨论这股邪门的精神。要纯粹为做坏事而做坏事。这股渴望促使我继续彻底完成我对这只无害动物的伤害。有个上午,在冷血之中,我用一个绳圈套上它脖子,把它吊在树干上;——我泪流满面,怀着心中最痛苦的悔意吊它;——我吊它,因为我知道它爱过我,也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给我害死它的理由;——我吊它,因为我知道这么做事罪孽……
巴雷《论怪物和异象》(1573):怪物有各种各样的起因。第一个起因是上帝的荣耀。第二个是他的愤怒。第三,是镜子超常充裕。第四,是精子数量不足。第五,是想象。第六,是子宫肥大或子宫缩小。第七,是母亲的坐姿不正确,例如她怀孕期间太过经常两腿交叉而坐,或太经常盘腿而坐。第八个原因是由于怀孕的妇人摔倒或肚子受到打击的结果。第九个原因是遗传而来的疾病,或偶然罹患的疾病。第十个原因是精子腐败。第十一个原因是精子混杂。第十二个原因是邪恶的无赖欺骗。第十三个原因是精怪或魔鬼作祟。
在其《论希腊诗的研究》里,施莱格尔(Schlegel)认为这种对人体令人比较不愉快层面的新兴趣有点类似莎士比亚风格:“就像大自然,莎士比亚创造美的和丑的,没有将之一分为二,而且同样丰富洋溢;他没有让任何一出戏完全美丽,美也从来不是决定整体结构的标准。就像大自然,绝少有美能免于杂质而成为纯美……莎士比亚剥掉角色的肉,以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探索道德尸体令人作呕的腐烂。”
第十章浪漫主义以及对丑的拯救对西方丑、崇高等范畴进行了甚详的历史论述。当留意一脚……
第十一章阴森,安吉拉·卡特提醒我们:童话可能有些令人恐怖的方面。
无法解释的极致、阴森的极致是出现幽灵般的第二个我:二重身。果戈理、戈蒂耶、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写过,弗洛伊德指出……
卡夫卡《变形记》使读者疑心这故事的真正主题是我们默认我们周围的罪恶。
斯托克《德拉库拉》(1897)。
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1871)(阿尔布莱特画的很抽象):有人说,激情使人循环式思考。
波德莱尔《艺术在巴黎》(1861):男人厌倦了写作,女人厌倦了做爱。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是布隆姆(Leopold Bloom)的地狱兼天国。
“大众文化”的种子。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维利耶(Villers de I'Isle-Adam):“生活?我们的仆人可以代劳。”唯美宗教出现。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于斯曼的逆理而行,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家那边,兰波给德米尼的信,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还有马里内蒂自由的文字,帕拉采斯基的反痛苦,达达达达达达,杜尚的蒙娜丽莎……你们会不会跟着陆钓雪说:上帝为了他的利益也会引用尼采?
巴塔耶《花的语言》把花与叶的不同真正阐释了,一塌糊涂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如是如实。
第393页审稿人的报告和批评:有人说这些作品真丑,给了我最大的乐趣,啊,这就是互文,就是艺术,就是剩余的全是文学,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第393页!
堕落吧,ART,还有媚俗,有趣(叔本华),坎普(苏珊·桑塔格)——昨日之丑变成今日之美,莫扎特,雌雄同体,17世纪中晚期欧洲开始想象中国艺术而做得不伦不类的中国风。苏珊·桑塔格提到博斯、萨德、兰波、贾利(Jarry)、卡夫卡、阿尔托(谁啊?),他们的目标不在于创造和谐,而是处理愈来愈暴力且无解的主题。
挑衅,艺术家还以自己的身体来承受血淋淋的折磨,神奇宝贝,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群众之上—>为了感觉像别人,因为大家都这样(cosi fan tutti),卡尔维诺的监票员,更好完。
美有标准,但丑的形式却是无穷无尽。继《美的历史》后,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大师又一部震惊全球的巨作,《丑的历史》谈的丑不再是美的附属品,而是恢弘地呈现“全面的丑”。
人们对于“美”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倾慕,并提出了许多理论替美下意义,对于丑的事物,却由心中发出厌恶。同时,人也在逃避“丑”的存在,忽视丑形式的存在,尤其是,当丑在我们自己心中的时候。Eco将丑的本身、形式上的丑、以及艺术对这两者的刻画区分开来,并在首章做了预告,丑不只是视觉上的丑,也是心里的丑,恶心、慌外、可憎、血腥、可怕、畸形、难看的、发臭的、腐败、肮脏......等等,都是丑!当你准备好要认识丑的时候,得先知道,“丑”,它无所不在。
艾柯大致以时间为脉络,从古典希腊时期(甚至提及更早)到现代,将各种丑的特色呈现出来,全书皆有图为佐证,更节录引用大量的文献为例,赤裸裸地将丑晾着,视觉及感受上都无所遗漏。古典世界里,社会对无于形下的难看、未知的恐惧、及不符合道德的,产生出来的想象及厌恶是最古老的丑的刻画。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产生了宗教的思想,甚至是体验各种痛苦的酷刑和殉道行为,进而刻画出地狱和恶魔,人们在逃避“丑”的同时,也创造出各种形式的“丑”。对于厌恶的东西也刻画出高度的丑陋刻画,如女人、妖异之物、犹太人...等等。在美所主宰的世界,丑也在近代作了反扑,各种前卫艺术及主义和传统的美激起鏖战,除了开始正视存在性的“丑”之外,对于矫饰的美发起的反动,有人追求至丑,并想尽办法呈现最真实的丑。
此书对我的思想有极大的启发,如艾柯所述,美与丑再一线之间,他举例非洲土著所刻凶恶的木雕脸孔,西方人觉得恐怖而吓人,当地土著却觉得是慈爱的形象。人们总是以自身的观点出发,主观的去定义外界的事物。而这其中,对于丑的概念常源自于“异己”,如民族歧视、同性恋歧视、厌恶畸形之人、文化歧视的厌恶...等等。其次,对于自身丑陋之处的逃避心理,在此书前却无所遁形,厌恶、嫉妒、怠惰、投机、自私、矫作,甚至嗜血、凶残等等的心理,在许多艺术家的手下、作家的笔锋下也都真实的呈现着,并非闭目不见便不存在了。事实上,在看似和谐美好的世界,掩饰多少丑陋的恶习及思想,各种矫情的假象,人们刻意地掩饰却益发明显,看似美丽的东西其实是刻意伪装的丑。因此,最后,人们刻意追求丑之道,也是对于世界的反动。
此书关于艺术,也关于文学,更贴切地说,是文化的的研究,若要譬喻的话,我说此书是一个拓展心灵视野的窗棂,是开启心灵枷锁的钥匙,但更贴切的说,是摆在花瓶里的排泄物。
“《丑的历史》为休闲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也为那些希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的人指引了门径。” 书的封底用到了《选择》杂志的一句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中肯的。
这本书从古典时期谈起,一直讲到了现当代。书中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一些谈到丑的文艺或者美学批评。
在书的导论的第一段里,艾柯就说到,“每个世纪都有哲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美’的定义,借助于他们的作品,我们能够建构一部审美观念史。‘丑’却不是这样。大多时候,丑被界定为美的反面,但几乎不曾有谁针对丑写一部专论。丑沦落为边缘作品顺带一提的东西。因此,美的历史可以援引范围很广的理论文献(我们由此推导出一个特定时代的品味),丑的历史则必须在关于人或事物的视觉图像与文字材料里穷搜线索”。(p8)
此言不假。就我的在写作我的论文的这一年时间里,我能够找到的18世纪到19世纪的直接谈论丑的问题的英文论著几乎为零。而事实上,就我所知,在英美文学界的整个历史上,专门谈论丑本身(而不是将其作为附属物,比如美的对立),并且将其上升到一定高度的论著都寥寥无几。因此艾柯的这本书当然只能“在关于人或事物的视觉图像与文字材料里穷搜线索”。于是这就导致这本书更像是本艺术史(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不是理论性的著作--后者本是我的期待。
在追溯完丑的历史之后,艾柯在本书的末尾这样写道:“日常生活中,恐怖的景象包围我们……我们再深知审美价值是相对的都改不了一个事实:在这些情况里,我们看见丑事,都毫不犹豫地明白那是丑事,我们无法将之化成喜悦快感的对象。你可以说艺术的声音是边缘性的,但艺术提醒我们:尽管一些形而上学家满怀乐观,但有个无法改变的令人难过的事实--这个世界里有个恶意的东西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里的很多文字和影像都在引导我们将畸形理解为人类悲剧……本书长篇讨论丑的各种化身,到处尾声,诚愿借此悲悯的胸怀寄诸读者”(p436-37)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给人安慰的结语--毕竟在看了那么多丑的形象和文字之后,心里是不舒服的。可是无论怎样,那些个光怪陆离的画面、恶心污秽的文字都在提醒,丑一直存在,甚至,丑才是生命本身的质料。
在《美的历史》之后,艾柯再推新书,剖析世人对“丑”之成见,颠覆传统的审美观。《丑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图像集合,而是会聚了艾柯的美学思索。《丑的历史》举凡恐怖、受难、死亡、魔鬼、启示录、怪物、凶兆、诙谐、猥亵、巫术、撒旦主义、虐待狂、媚俗……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他雄辩地证明了,美固然仪态万方,丑一样博大精深。
丑是什么?只是美的反面吗?丑的范畴有多宽?在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眼里,“丑名昭著”的苏格拉底,长鼻男匹诺曹,毕加索画笔下的《哭泣的女人》都可能是迷人的。艾柯说,“美乃寻常物,可能令人乏味,而丑却有无限可能。尤其在艺术领域,丑往往战胜美。”
读《丑的历史》,应该与他更为有名的《美的历史》对照着看。《美的历史》赏心悦目,《丑的历史》刺激震撼。美,引人入胜,丑,更加有趣。美,欲拒还迎的,林妹妹式的,含蓄地等待你的亲近;丑,那一定是压倒一切,剽悍直接,你拼命反抗都不灵。美,直指人心,丑,直指人胃。
西施自是有人爱,东施何尝没人爱。
在著名的意大利小说家和学者翁贝托·艾柯的眼里,蒜头鼻、麻子脸和大肥腿都可以变得美丽而迷人。
艾柯上周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推出了自己的新作《丑的历史》(Storia dellabruttezza,英译书名为“OnUgliness”)。
他出版于2005年的《美的历史》(Storiadellabellezza)已经以27种语言在全世界卖出了50余万本。彭淮栋译中文版《美的历史》2007年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近200元的定价,美得十分昂贵。
现在,艾柯决定深入探讨丑的魔力。他说,丑的身体比美的身体更有魅力,因为丑的定义没有边界。
“我们发现,寻找丑是件多么大的乐事,因为丑比美更有趣。美往往是乏味的,因为人人知道美是什么。”他说,“丑却有无限的形态可能———你可以弄出个巨人、侏儒,也可以弄出个长鼻男,就像匹诺曹那样。”
前往法兰克福之前,他对安莎社说:“要想像理解美那样理解丑,得聚焦于少数历史时刻,以及审美规则的演进。”
到了法兰克福,他说:“基督教总是与对肉体的贬斥连在一起……有些画作明显对丑充满了欣赏。”
16世纪的佛兰德画家昆廷·马西斯画过一个旷世丑女,丑得一塌糊涂,丑得像个穿了胸衣的老男人。艾柯觉得她怎么样?喜欢吗?
“也许我会说———Non e il mio tipo———她不合我的口味!”他答道。
他还举当今两大男女大鼻子明星为例,说明美丑之间有着巨大的灰色地带,须臾即可转换。
“芭芭拉·史翠珊和热拉尔·德帕迪约都给人以优雅的感觉———他们并不美———但优雅是什么?”满脸胡子、胖墩墩的艾柯说。他总是叼着一载从不点燃的香烟,“世界不能被分成美丑两界———例如,我就在两界之间。”
继让全球惊艳的《美的历史》之后,博学大师安柏托·艾可写出“丑”,而且他亲自保证,一定比“美”更精彩。
每个世纪,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提出“美”的定义,藉他们述作之助,我们能够建构一部审美观念史。“丑”则异于是。大多时候,丑被界定为美的相反,但几乎不曾有谁针对丑写一部专论,丑沦落为边缘作品顺带一提的东西。因此,美的历史可以援引范围很广的理论文献(我们由此推出一个特定时代的品味),丑的历史则必须在关于人或事物的视觉、文字刻画里穷搜数据。
不过,丑的历史和美的历史还是有些共同特征。首先,我们只能假定一般人的品味在某些方面和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家相同。假设一位来自外层空间的访客走进一所当代艺术的画廊,又设使他看见毕加索画的女子脸孔,并且听到其它观赏者形容其为“美丽”,他可能误以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这时代的人认为毕加索画的那些女子脸孔美丽,秀色可餐。
但是,这位访客看一场时装秀或环球小姐选美,目睹那里赞美其它类型的美,可能就要修正他的见解。很不幸,我们回顾久远以前的时代,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谈美还是谈丑,我们都无此参考,因为那些时代留给我们的只有艺术品。
丑的历史和美的历史另外一项共同特征是,我们讨论这两种价值的故事,势必得局限于西方文明。在上古文明和所谓原始民族方面,我们有出土艺术品,但我们没有理论文字来告诉我这些艺术品本来的用意是要引起审美的喜悦、对神圣事物的畏怖,还是欢欣。
作者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生于1932年,意大利人。他是享誉国际的知名作家,也是记号语言学权威、知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现居米兰,执教于波隆纳大学。著名的4部著作为《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昨日之岛》(L'isola del giorno prima)、《波多里诺》(Baudolino)、《美的历史》(Storia della bellezza)等。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原题《丑比美更美》)
“媚俗也一直被用来形容希特勒、墨索里尼政权下那些歌功颂德,要全民欢迎的艺术。”
美的对立为丑,然而审美与审丑皆有共性,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翁贝托・艾柯写《美的历史》后,再作《丑的历史》,在书前《导论》里说:“每个世纪都有哲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美’的定义……但几乎不曾有谁针对丑写一部专论。因此,美的历史可以援引范围很广的理论文献(我们由此推导出一个特定时代的品味),丑的历史则必须在关于人或事物的视觉图像与文字材料里穷搜线索。”罗森克兰茨在1853年写过《丑的美学》,艾柯称其为“第一部也是最完备的”丑著。
艾柯在《丑的历史》认为美与丑的审视标准随历史时期或文化之不同而变化,说:“一个时代认为合乎比例的东西,另一个时代却不认为它合乎比例。在比例这件事上,一位中世纪哲学家会想到哥特大教堂的层次和形式,一位文艺复兴理论家会想到依照黄金分割来建构的16世纪殿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认为大教堂的比例是野蛮的,他们以‘哥特式’一词来形容,就说明了一切。”这意思是美与丑并无定论,观念亦会随时代或社会发展而起变化。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巴黎埃菲尔铁塔,“埃菲尔1889年为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完成铁塔之前,1887年的《时代报》(Le Temps)刊出一封署名者包括作家小仲马和莫泊桑等的信:‘我等作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珍爱巴黎仍然完好之美者,在此尽我等全副力量与满腔义愤,为法国人民被低估的品味、为受威胁的法国艺术与历史请命,抗议在我国首都的心脏兴建无用且丑怪的埃菲尔塔,富于常识与正义精神的不满的大众早已为此塔取一诨名:巴别塔。’抗议信怒斥这巨大的‘工厂烟囱’将会像一块墨渍渲染开来,‘可恨的铁柱子’的可恨阴影将笼罩巴黎。”这段话里最有趣的是信的措辞,写这封信的人皆是知识贤达和社会名流,倘若我们的知识分子有这般勇气敢于大声疾呼直抒己见,大概老北京城不至损毁到今天这副模样。
关于丑有许多可谈的话题,书中第十四章《媚俗》一节曰:“丑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上层’阶级的人向来认为‘下层’阶级的品味讨厌或可笑。我们当然可以说,经济因素在这类歧视里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就是说,雅致常常和昂贵的布料、颜色及珠宝相连。”大多艺术品虽出自工匠之手,却由上流社会所推动,皇室和贵族成为艺术品最好的维护者,而每当有底层暴动和骚乱,都会使艺术品受到损毁。然而艺术常被政治和宗教所支配,使其成为时代政治的符号,艾柯称此为“媚俗”,比我们狭义的媚俗更多出政治因素。“媚俗也一直被用来形容希特勒、墨索里尼政权下那些歌功颂德,要全民欢迎的艺术。”另有一些称作“好东西,坏品味”的,如古镇开发成旅游景点,将旧时代的东西拆除掉再建设新古董,倒是符合“坏品味”的标准了。
谈美易令人愉快,但要把丑说得不让人反感,实非易事。《前卫运动与丑的胜利》一章里说:“心理学家荣格在1932年撰文讨论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认为今天的丑是即将到来的巨变的征兆和症候。意思是说,明天被当作伟大艺术来欣赏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认为倒人胃口:新事物来临时,品味往往还跟不上。”这为我们当代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当代艺术展上经常见到以丑为美的作品,或怪诞、亵渎的自我表现,很是有点赌明天的心理,似乎天才也要靠运气,古今皆然。
(来源:广州日报)
刚收到书的时候自然会感觉质量是和价格相对的,而书的封面是裹在纯白纸板封面的并非粘在纸板(对于我有点费解)。说实话书买到手也有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还是没看完,最开始翻看也是被书中的图片所吸引,先是把图片都大致看完才开始重头看内容的,其实书中一挺多图片我都从别的各种渠道看到过,比如书中有提到《粉红火烈鸟》《一条安鲁达狗》等cule电影 短片,但真要知道由来历史什么的还是要从本书来深入了解,书中有很多对丑在不同历史时代环境的看法分析,就是一些摘录的故事文献我不太有耐性看~挺不错的一本书~
作者: [意]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原作名: Storia della bruttezza
isbn: 7511702023
页数: 448
译者: 彭淮栋
定价: 198.00元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10-04
又名: Storia della bruttezza, History of Ugliness
书名: 丑的历史
http://www.hkzhltdzy.com
看完挺震撼,除去政治因素,整个东方文化也总是露美遮丑,像我这样的85后接触到的历史文化其实是剥去了很多原汁原味的进化细节,被新的审美观重包过的。确实需要从内心把丑作为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接纳。
我第一次见到此书是在机场候机厅,很吸引我,但价格太贵。然后回家查了很多书评,发现很多学意大利语的人指出本书是另有主要合著者,觉得挺疑惑。译者不能为了利用艾柯的名气就把创作者精简掉吧?我不懂意语,还是感到中译本其中的一些涉及到希腊神话的情节翻译跟之前接触到的都有出入。内容丰富,版本精美,就是觉得著者和翻译细节不太如意。
非常值得稱讚的是,質量很不錯!
很喜歡這本書的質地,手感很好,因為有一定的重量所以拿在手上的感覺很像在捧著一本百科全書,
裏面的插圖也有些出乎我的意外,
關於【醜的歷史】這本書裏面所講訴的有關資料與歷史,
我之前已閱讀過不少,
不過裏面的有些插圖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讓我非常驚喜,
此書我認為最大的亮點也是書內的那上百幅插圖,
至於對作者的描述,我認為有點偏向作者的個人主義風格,
例如在講訴“傳染病所散發出的腐爛臭味”一節,
作者明顯的以自己個人的偏見角度去描寫,
還有對於朋克的不削等。。
作者以個人中心來複述那些故事,可以借鑒,
不過建議最好以客觀主義的思想去讀這本書,
最後還是要提一句:裏面的插圖真的很不錯!
《丑的历史》有网友说老早收到了,讲收到的书品相交关好。我5月24日在卓越下的这笔订单,31日中午收到,与第二次调换的《时间的故事》一起送来。精装书品相出人意料的漂亮——快递员说,这两本精装都从苏州库房调拨而来呢,他不知道的是这两本书都是Viking兄编辑滴。
对于这两本书,虽然印张、开本大小都一样,用纸都是铜版纸,不过《时间的故事》用有光纸,《丑的历史》用哑光纸,前者明显薄了近1/4。对艺术类书籍的用纸,我觉得还是哑光铜版纸更好吧。
6月3日晚失眠,4日凌晨1点多爬起来翻《丑的历史》,一口气翻到5点结束,尽管有希特勒、斯大林的图片,依然怀疑删除过一小撮局部的段落,虽然事实并没有删节过——书是好书,装帧极佳!
附上书的护封与纯白布面精装封面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01482295/
美是有情人眼里的西施——必提福(beautiful),丑是无情人眼里的东施——阿哥累(ugly)。本来,妍媸百态,燕瘦环肥,各有所爱,但是立场、偏好、经验、所有权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人们对于美丑高下的主观性划分标准。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里说,“问蛤蟆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美,他一定会说,他的雌蛤蟆就是美,她有两只秀美的圆眼睛,从小小的头上凸出,她有宽宽平平的喉咙、黄黄的肚皮、褐色的背。问几内亚的黑人,他认为美是黑油油的皮肤、深陷的眼睛和扁平的鼻子。询之于魔鬼,他会告诉你,美是一对角、四只爪子和一条尾巴。”所以说,他人之西施,或许是你的东施。前世之东施,亦可能是今日之西施。千言万语归根结底,还是《麦克白》里的巫婆们精通辩证法,她们高呼:“美就是丑,丑就是美”!
艾柯大师编著的这本《丑的历史》,应该与他更为有名的《美的历史》对照着看。《美的历史》是天上人间夜总会,赏心悦目,《丑的历史》则是JJ迪厅,刺激震撼。美,可能吸引人,但是丑,更加有趣。我的经验告诉我,大多数时候,美是忸怩作态的,欲拒还迎的,林妹妹式的,含蓄地等待你的亲近;可是丑,那一定是芙蓉姐姐和凤姐那般的,压倒一切,剽悍直接,你拼命反抗都不灵。美,直指人心,丑,直指人胃。我乖乖研究了第10页尼日利亚的舞蹈面具、第42页格吕内瓦尔德的《耶稣受难》、第168页阿尔钦博多尔的《冬》、第232页的摄影《世界最丑的狗比赛冠军》——实话说,有鉴于本人见多识广,能震到我的,委实不多,可是仅仅这四页,就足以让我阵阵恶心。
《细节》杂志的评论说:“大多数艺术书值得看看,或许,在咖啡桌边即可。这部无法言喻、令人发狂的书却是要读的。”的确,此书不是简单的图像集合,而是汇聚了艾柯的美学思索,一旦想起他是从研究亚里士多德起步一路疾奔到后现代,就很容易领会《丑的历史》必定如他本人一样巧舌如簧、喋喋不休,举凡恐怖、受难、死亡、殉道、地狱、魔鬼、启示录、怪物、凶兆、诙谐、猥亵、巫术、撒旦主义、虐待狂、阴森、放纵、媚俗、坎普……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他雄辩地证明了,美固然仪态万方,丑一样博大精深。
在书中,艾柯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范畴:丑的本身、形式上的丑、艺术对前两者的刻画。也就是说,本书既是丑的观念史、也是丑的形态史、还是丑的表现史。 最具颠覆性的是,当丑的题材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往往模糊了美丑之间的界限。啊,那些塞壬女妖,何其美丽,让人联想起中文里“魅力”的“魅”字,那是鬼字旁的。
在书中,艾柯式幽默亦时有体现,比如第一章《古典世界里的丑》,一本正经地介绍《会饮篇》,苏格拉底的恋童癖和柏拉图式的恋爱,那个pederasty到底如何理解呢?英俊的阿席比亚德斯醉闯飨宴,表达他如何为了分享苏格拉底的智慧,多次向苏格拉底献身,但苏格拉底从不愿屈就肉欲,只是纯洁地躺在他旁边——艾柯以为读者们都像他一样清楚,苏格拉底有个悍妻,怎敢不“纯洁”。 从苏格拉底开始,本书中援引的大师名家,个个都是一时翘楚、百代之才,通过他们的审丑史当能发现,人类对于丑是越来越宽容了。这其中,艾柯没有明说,许多大师名家其实正是丑的缔造者和辩护者。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深深处,一直活跃着“小众趣味”、“不良趣味”、甚至“恶趣味”。呜呼,西施自是有人爱,东施何尝没人爱。
PS: 我毫不奇怪,博斯的画作,既出现在《美的历史》中,也出现在《丑的历史》里。
万圣8折。这种铜版纸画册——尤其是它的画儿如此引人注目——想要没被人翻烂的新书,估计也就8折了,昊海楼的野草预计不会少于这个折扣,所以,就买了。
至于评论,看完再说。
或有疏漏,绝无删节。
以藏 哈哈哈
你这个上传的照片仅本人可见啊!!
仅本人可见啊!!
刚开个了头,还有续篇吧!
啊,我觉得我跟马老师的审美差别太大了,那4张我倒没啥感觉(是我想象力不够吧),但是书里让我恶心的图片、文字实在太多了,特别是那种直接的丑陋、暴力。
《丑的历史》里面的有些图片,确实丑的名副其实啊……
可惜前年上海书展上买的英文版不在手边,不然可以说说我最厌恶哪几张图片。
对了,这回彭淮栋翻得如何?
如果把书的图片作为艺术来欣赏, 恐怕基本达不到目的,而且会失望。 如果是想获取一种心理体验,洞悉一些艺术的原素,倒不失为一种选择. 但还能找出几张供欣赏的.
翻得还好。我发现我对翻译越来越不挑剔了。
即便是丑的题裁,一旦加以艺术表现,有时还是比较美的。我对书中图片很满意啊。
一早起床发现所有功能都不能用了,难道又发生了地震,今天是全国默哀日?
丑的好让人期待哦。。。。
终于明白为啥凤姐都红了我还没红呢
哎 很想很想看看啊~~
买了,坐等寄到哈哈哈
刚买了原版,拜读中..
原版岂不是意大利文,我膜拜你~~哈哈哈哈
楼主只注重定义不注重差异。
艾科让我们关注的恰恰是差异。
LS 所言何来?
楼主原来是老师,失敬失敬。
楼主老师应该去看看所谓的十大禁片,老师您所提到的那四张图片与之相比,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绘画方面,楼主老师如果去查查中世纪的绘画,有些真是很恐怖,看了绝对做噩梦。
禁片看过,也专门研究过中世纪,还是“艾柯研究专家”(呵呵,别人封的)……
只是觉得你对我的小文有误读,我何时注重定义不关注啊差异来着?是以有此一问。
艾克研究专家••••真不知道你说出来干什么,让人家觉得你牛逼,你权威以阻止别人对你的观点的质疑?
LS真过敏。
我与果果那段对话,是针对他提醒我十大禁片和中世纪艺术,十大禁片我真的看过,中世纪和艾柯都是我的研究领域,因此说明一下,有何错处?
再向前,我问他“所言何来”?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不重差异”,是为了辩论,不是阻止质疑。可惜这个对话没有进行下去,也许果果只是“那么一说”,而已。
在艾柯研究方面,我是个很认真的人,如果LS有见解,欢迎讨论。如果只是一口没来由的恶气,悉听尊便。
我没质疑你看没看过,我也没质疑你俩讨论的,我就不明白你说个专家干嘛,说明你是专家?
你是专家跟讨论有关系?
有关系,如果你懂得艾柯本人关于普通读者和经验读者的区分的话 :)
看完美的历史,看了这文章想读丑了……
普通读者和经验读者的区分是?弱问马老师是艾克哪本书里的?
这两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艾柯谈过多次,译名稍有不同,比较通俗的解释,请见《悠游小说林》。
丑也是有有点的。
窃以为《会饮篇》里苏格拉底的“纯洁”和悍妻没有关系。前一个是作品里的苏格拉底,后一个是现实生活(姑且相信的话)中的苏格拉底--当然,这和艾柯这本书没什么关系就是了。
普通读者和经验读者作何区分?读过所有作品的是经验的否则是普通的?普通读者不可能有洞见?了解其前前后后的历史但没有思想共鸣的算普通还是经验?可以自封为普通的或经验的吗?不否认读者的知识存量文化内涵有高下之分,但在一本书面前人人平等。
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样通俗的评论观点对于经验读者来说确实过于浅显了
我也预定了,期待中。。。
为何不在Amazon买?6.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