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通论
2000-1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家范
453
无
《中国历史通论》讨论的范围应覆盖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全书分为前编、绪言、后编。前编是通论专题研究,后编是回顾与反思。该书理论丰富,史料翔实,观点新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作为高校历史系的教材。
绪言:对《中国历史通论》的考虑
前编:通论专题研究
一、部族时代
二、封建时代
三、大一统帝国时代
四、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
五、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
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
七、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
八、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
后编: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
二、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
三、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
四、对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
《中国历史通论》是对中国历史的讨论,主要包括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等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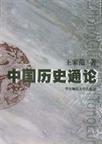
无
王家范爷爷一再说,六十以前写不出好书。(当年章门高弟黄侃就说五十之前不著书,结果:黄季刚,1886-1935。可见这类话,是要窥得几许天命之人才敢说的。)到六十二岁上,王爷爷拿出了这本《中国历史通论》,果然是出手不凡。
揭示中国历史特性,大抵不离两大板块,一是文化,一是制度。而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这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做制度史、经济史的学者常常有一种印象,觉得搞文化史的大包大揽,什么都是它们排第一。其实这正体现出理念和制度运作之间微妙的关系。理念要变为现实,必须不断地化为实践上的操作。“中国历史上不缺思想与文化的高度,但实践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制度史自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制度改革常常作为事后补救的手段出现,而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一进程,是难以估量的。道德政治化的结果,到头来往往损伤自身的纯洁性。王爷爷很少提及文化史,这种观点是渗透在他对经济史的论述中的。可能因为我比较关注文化史方面,读王爷爷的书反倒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理念的高度”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并非混融一炉,二者间的紧张之处或许更值得注意。
农业产权的界定模糊而富有弹性。产权的形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使用权,或称经营权;二是占有权,即“收益权”;三是所有权,即“处置权”。就中国传统社会总体状况而言,产权“国有”性质表现地根深蒂固,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自然,不能凭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训,就认定中国自来便奉行土地公有制;但也不能忽视这句话深深植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策略之中。在王家范爷爷看来,中国农村在面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所出现的反抗远不如苏联激烈,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正因为私有制发展的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律保障,中国商人和市民未能形成一股独立的、可以与官方相抗衡的力量,中国进入现代才如此之艰难。
“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能不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王爷爷对此给出了篇幅不短的论述。现代经济变革产生需要的那一部分乡村土壤——个体小农经济在中国早就好端端地存在着,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农工商虞”四业哪一个都不能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环境。农业负担过重是致命的问题。每王朝履变赋税之法,不是减法,而是连加法,政府不吃亏这一条铁律是不变的。自耕农占有的耕地,越来越畸零分散,小农经济被滞留在维持人口自然在生产的经济水准线上,无力发展出外延性的扩大再生产。大一统帝国征收赋税,以“劫富”、“分肥”为倒向,江南富庶,苏松常嘉湖的赋税又畸重,略有积累,便被不合理的高赋税所吞食。北宋以来,富户地主最苦于各种职役,一充粮头、解头,即赔累衰落——小民谋生之艰,在书中处处皆是。在“地主经济”中,政治身份性的官僚仕宦居绝对优势,而“地主”转化为“异己”的社会力量,要到近代以后才稀稀落落地在东南沿海出现。明清以降,江南棉布产销盛极一时,“资本主义萌芽”话题由此衍生,王爷爷却指出,王朝政府充当了一个特殊的、长期被忽略的棉花、棉布消费的“大主顾”(宫廷、军队所需、实物征调、“折边”迫使农民出售棉花),在棉业市场繁荣的背后,其实是国家财政赋税的特殊怪胎——这正是斌斌课上提到过的,程念祺所说的“财政市场”。传统社会手工业技术,多服务于皇宫官僚系统的大一统需求(“大一统性”),许多中大工艺系个人即兴创造,既无理论总结,也无重复试验,经验高度保密,甚至为朝廷独占(“工艺封闭性”),劳动密集型的手工部门始终产生不出技术改造的刺激机制,甚至有些节省劳力的技术也宁愿弃之不用(“劳动密集性”)。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商业,在“抑商”的口号下,与商人争利,防止任何有可能构成对帝国集权统治具有威胁的集团性社会势力形成,商业行会异化为政府代理人
王家范爷爷治明清江南史有年,一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并不新鲜——比如“封建”的定义与中欧“封建社会”对比,比如何为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萌芽”争论,比如中国“冯建经济长期停滞论”争论,比如君主作为国家主权即土地最高所有权的代表,比如高赋税阻碍农业生产的变革——但王爷爷是是这些学术热点的亲历者,而且常常不是领头者便是终结者。到了退休返聘的年纪,把自己学术盛年研究成果和思考轨迹发表出来,又是另一番味道。
除了社会经济史,王爷爷的书中还涉及一些关于社会结构和通史写作的论述。王爷爷讲社会史实在是不带劲儿,我就不说了。通史方面,王爷爷写了三个人。第一位是张荫麟。王爷爷把张荫麟是做梁任公“新史学”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张的学术以考据起家,很见功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传承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张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也引出了一个时代大话题:考据与义理的关系。张荫麟的独树一帜,还在于他兼治哲学。史学的改造创新,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的“营养不足”。第二位是吕思勉先生。王爷爷同样把他视为梁启超的继承者,认为《吕著中国通史》是“梁启超构建新式中国通史理想的实现”。梁启超要改造原为统治者“资治通鉴”用的旧国史,用新文化、新方法编写国史,所拟《中国通史》目录,可看出他摆脱旧史叙述独重政治史和道德评判的努力,与吕著目录相较,自可看出传承脉络。王爷爷说吕先生极具平民意识,且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吕先生深受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而今文经学“经世”转轨为“新史学”,是学理内在的自然脉络。另一方面,吕先生也是较早意识到“新史学”“不重根本、急于作用的隐患”的学者。梁是国家主义者,用“国家”取代“朝廷”,也就极容易滑向新的“资治通鉴”,政权意识盖过社会意识,将当下政见、方略的不同硬与历史认识纠缠在一起,不重疏通知远——可谓切中弊病。第三位便是王爷爷自己。基于史学通感,王爷爷提出了颇多独创之论。如《总起》中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八点特质(早熟;农业产权模糊和富有弹性;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个人崇拜根深蒂固;“政治一体化”;知识精英是社会主流力量;“大一统”的成功;变易观)。
王爷爷用了四五十页的篇幅,来讨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王爷爷看来,这本原本为反驳“欧洲中心论”而作的书,反而落入了“中国中心论”的圈套。弗兰克的结论是,明中后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白银贸易圈,而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在中国,每年有320万两白银流入内地。王爷爷则算了一笔账,这320万的白银,流入帝国财政的大窟窿,瞬间化为乌有,明中期以来,“内库空虚,无以为继”的呼声不断,绝没有弗兰克想像的白银多得满地流淌不尽之感。他提醒研究者,切不可因为弗兰克对中国传统社会史无前例地高评价,便欣欣然自得。想起斌斌以前说的,对传统社会倾向否定才是大多数中国史研究者的一般态度,像钱宾四那样的乐观实属凤毛麟角。对研究对象“亲妈感”或“后妈感”笔触,除了影响读者的心态,势必也会影响作者的结论。不管“亲妈”也好,“后妈”也罢,王爷爷说了,历史是要教人冷峻的。
篇幅太大
给个链接
http://tieba.baidu.com/f?kz=121466482
王家范教师常年在教学的第一线积累了无数的劳动成果当然更多的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不断思考大概都集结在了这一本子了其中不乏精辟之见解我其实更喜欢他流畅的文笔比其他的前半部分的论证来说更喜欢他对于中国历史如何走入现代的看法另外王家范教授的著作《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是我大学的启蒙读物
呵呵,你写的真多
你提那个是要黑黄侃么?哈哈哈哈哈~~
@巴撒 啊哈哈,我爱章疯子他全家~~~~~包括弟子、基友
哈哈哈,那你追随他门搞基去吧
当当11周年店庆降价啦 呵呵